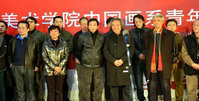从《辞海》“写生”释义不完整说起
——中国画写生观之要旨
卢炘(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画名家馆联会秘书长、潘天寿纪念馆原馆长)
画家张伟民严肃批评《辞海》对于“写生”这一绘画术语的释义,认为解释不完整,“不甚了解中国画本质的诠释,混淆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带有明显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张伟民《会心的体悟与漫游的思绪——中国画写生观》)其论观点鲜明,颇具学术性,读之甚有所得。
《辞海》述“写生”词条:“专指绘画艺术的专业术语。动词,对着实物或风景绘画。例:静物写生。”作为“写生”一词,《辞海》作如此解释,笔者认为也是就事论事,并不存在什么大问题。西洋画讲“写生”,中国五代画家也有“工画而无师,唯写生物的腾昌祐”,宋代有自号“写生赵昌”者,但中西写生的意义还是有区别的。20世纪以来西画写生观念传入,西画成了近现代美术教育的普及内容,“写生”一词也产生了带有偏向的共识,纠正《辞海》“写生”条的释义似乎没有多大必要。要把张先生的意思用简要的文字补进《辞海》“写生”条也不易,难以选择准确简要的语言来表述。
诚然,张伟民的观点强调中国画的写生观很有意义,从专业角度来看,“写生”并不是“对着实物或风景绘画”那么简单。笔者也谈一些浅见,以求方家指正。

潘天寿 记写雁荡山花图 1962年
写生与临摹的关系
谈中国画“写生”势必谈到临摹与写生的关系,学习中国画理解这种关系非常重要。正如潘天寿先生所说的,由于传统的独特性,学习中国画要以中国的方法为基础,而临摹结合中国式写生乃为正道。
临摹、写生孰先孰后,至关重要。
上世纪40年代国立艺专在重庆璧山时期,导致潘天寿离校回浙的几个原因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临摹写生孰先孰后的问题,潘天寿与当时的校长观点有分歧。透过现象看实质,此事反映了对传统的不同理解。
理解潘先生的意思是:临摹为学习的第一步,写生是随后发展创作的第二步。通常说的“第一口奶影响一辈子”;“三岁到老”,“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己”,初期的教育非常要紧。师傅领进门,“门”不要走错很重要,就像高速公路上开汽车,一个岔道错过就不知道要多走多少冤枉路。
临摹也要多方研究。临摹实际上是一辈子的事情,它与写生的关系交织在一起,临摹虽然在先,但是写生到一定时候需要再临摹,所以临摹是一辈子的事。
潘先生练字,每天中午练张字,这是从小一直坚持下来的,晚年还临黄道周的帖。书法家陆维钊先生,他临兰亭,其中有一幅说自己临到第150张,才感觉到有体会,他就在边上写“稍有所会”4个字,你们看陆老要到70多岁才能够稍有所会,正说明了临摹的重要性。而他临摹的《兰亭序》到后来只保留了一种意,形体运笔都是他自己的“陆体”了。书法如是,中国画亦同样,临摹并非摹得一模一样便好。
写生须把握“四重一求”
实际上,写生应该含在创作的范围里,可以把它看成是创作的初级阶段。故此我觉得写生须把握“四重一求”:重本质,重特色,重默写,重活写,求变化。
一重“本质”:捉形、捉色、捉神情骨气
古人捉神好——这是因为长期的练习,所以他们作品的艺术性很高。
古代的精英,他们的眼光很高,即审美情趣高,又从小拿毛笔,对毛笔的运用技法都可以做到很熟练。中国的笔墨,它既是表现形的手段,又是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笔墨本身有独立价值,也就是在临摹的时候,已经把本质的东西先抓住了。
一味摹古——形象弱了——所以要加强写生,写生必须捉形、捉色、捉神情骨气。(潘天寿语)视对象为活的生命体,写生的过程是这种自然生命与作者主观感受的结合,因此不再是纯客观的物体,而是加进了作者的文化性。
二重“特色”:明确中国画特色,然后再有个人的特色
1.中国画用笔线写形,用笔来捉形,用线来概括,追求空灵的效果,从形的力度来强调,越简笔线要求越高。
2.进而研究姿态、动作神情、动态布局。
中国画写生就要明确中国画特色,通过写生渐渐进入创作状态。画人物我们知道,每个人的面孔不一样,又有不同情景的不同表情。山水画也像人物有不同的面孔,不同地方的山都是不一样的,又有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和朝夕之别;花鸟也是这样,各有不同的面貌,即使是两片树叶都是不同的。要避免概念化,如何避免?靠写生得来。
从技法上来讲,中国画传统的白描等技法,实际上都是要再发展、再开拓的,包括山水画的很多技法。就宏观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要耐看,要经得起审美衡量;二是要有整体性,这个整体性包括它的精神含量。
三重“默写” :重默写就是重神情和特色的具体做法
默写一样东西,你的记忆不可能面面俱到,你必须要抓特点,所以留在脑子里的是特点。所以事后默写与临场写生不同,默写出来的是强化了的东西,因此非常重要。
四重“活写”:需要看和思结合
“看”就是观察,观察自然界事物,也要看前人作品,前人作品要看大名头之作,取法乎上,即所谓“练眼”,要多看大、厚、重、拙;避免小、薄、轻、巧。潘先生曾经和学生讲,看展览你要挑选的,有些东西不可多看,多看眼睛看坏了。对自然界事物的写生既要注意观察,又要多思。
“思”是如何结合传统技法,多思多悟,这是一个强化感受的过程,也是浓缩感受的一个过程。随后就是思变。
一求“变化”:先求形似的复杂变化,后求简略的神似变化
“变”其实是创作的阶段,写生的求变化要不断检验,在不同的临摹和写生中,要清楚处于哪个阶段,应该求什么?先求形似的复杂变化,后求简略的神似变化。最后要“变”出笔墨的个性化语言和笔墨结构来,以前不太敢讲形式结构,怕批为形式主义。其实大家都画一样的东西,当内容确定以后,你怎样把它生动起来?活起来?使人得到深刻的精神享受和美感,关键是个提炼表现的问题,形式、笔墨、语言、结构的问题不可回避。
历代名家有许多关于写生和创作的经验,可他们并不都一模一样,值得我们去分别研究:譬如黄公望与《富春山图》,是写生模记山水画家创造的绝代佳作;石涛写生打草稿而八大山人却写意不写生;吴昌硕画气不画形,但也有《蕉窗写生》,而书法却并不从写生来;齐白石重实写,黄宾虹重默写,潘天寿写诗代写生;傅抱石的“动起来”,陆俨少写生“多思善变”,李可染善写生,他的学生贾友福画太行山却不写生而照样出名作……
深入生活 跨越生活
我们既然把写生当作创作的初步,对其同样可以提出深入生活,跨越生活的要求。虽然我们每天生活在现实中,但如果不去深入思考,就谈不上深入生活。写生所寻找的对象,那种生存状态尽管是客观存在,但必须与写生者主体产生互动,有了共同的契合点,即情动于中产生共鸣,方为真正有意义的写生活动。此时自然状态带上了人文色彩,自然美才有可能演变为艺术美。境界格调越高的人便能发现和提炼越高的审美意境和思想意义,技法作为基础不可或缺,加上勤奋不懈的努力,写生终于跨越生活,遂能如愿以偿,完成自己的阶段性任务。
艺术家是对生活十分敏感的人,没有感动哪来创作,同样没有感动作为创作的初步阶段——写生,也同样会走过场。所以有画家把那种以生动传神的笔墨语汇物化对象,称之为“进得去”又“出得来”。“进得去:体察入微(观),潜移默化(浸),物我两忘(化),此为入门之道。出得来:人性为主导(认识)形存实亡(文而化之),转体为形,化物为态(实入虚出)。……此时,正是‘人文化天工’生命本质向社会文化方式的转变。”(同上,张伟民《中国画写生观》)我非常赞成这种“会心体悟与漫游思绪是跨越生活创造艺术的桥梁”的说法,写生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