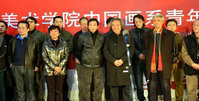法国巴黎市立当代美术馆开幕了曾梵志大型回顾展,其中就包括了《最后的晚餐》
吕澎(艺术史家)
编者按:10月5日的香港苏富比拍场上,曾梵志的《最后的晚餐》以1.8亿港元成交,刷新了亚洲当代艺术品纪录。不久之后,在法国巴黎市立当代美术馆开幕了曾梵志大型回顾展,其中就包括了《最后的晚餐》。
巴黎,在展览方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会上,绝大多数法国记者没有提及“1.8亿”(以下皆为港元)的问题,只有一位女记者的提问中出现了“钱”这个单词,但她的脸很快就红了,有些不好意思——毕竟这是一次关于艺术的展览,尽管展览的是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我接到了不少媒体的电话,询问如何看待曾梵志的作品卖到“1.8”亿这个数字?又如何看待人们对艺术家或者相关人士天价做局的继续质疑?的确,所有询问以及问题的焦点都是钱。事实上,在中国的今天,在不少艺术活动与展览现场,人们谈到最多的就是钱、钱、钱。
猜测没有止境,日常生活中,人们需要谈资,尽管每个人的角度不同,相信在未来新的数字出现的时候,所讨论所怀疑的问题还是这类老问题,总之就是钱的问题。这意味着,在中国,只有钱是个问题,其他都不是问题。
我在展厅里待了不到一个小时,作品非常熟悉,中国艺术家能够在巴黎市立现代美术馆做个展,我想不出有什么副作用足以抵消其积极的作用。展览完整地呈现了曾梵志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不同时期的作品,能够让观众充分了解这位艺术家的艺术变化的过程。相信这对于巴黎的观众来说,是一次很好机会了解他们不太熟悉的艺术家的艺术。如果有人要深究艺术家的艺术问题,也许那些展示在展览入口的文献材料以及涉及其他关于中国艺术的评论和历史著作会有所帮助,如果有机会组织研究与学术领域的更加深入的讨论会,就更能够增加人们对大量的涉及历史、政治、社会、技术、风格以及手法问题的理解。展览、呈现、出版、推广、会议、交谈以及作品流通,这些由人类自己设计出来的文明游戏构成了文明史的一部分,其规则与变化也是根据人类生活的需要而调整的。针对展览我要说的是:这不仅仅是一个叫做“曾梵志”的中国艺术家的一次展览,更是为巴黎和欧洲的观众提供一次观看一个具有特殊性的艺术的机会,实际上,重要的不是曾梵志,而是曾梵志的艺术。站在一个法国观众的角度上讲,不过是欣赏到了他(或者她)在卢浮宫、奥赛和蓬皮杜看不到的一种绘画艺术,就此,展览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目的。如果从展览本身的安排与设计来看,也许“面具”系列的作品多了些,展墙的作品还可以松动而不要放得那么满,同时,倘若作品旁边有更为充分的文字,也许更能够帮助观众对作品的理解。
当然,人们有很多问题想问:为什么是曾梵志?为什么他的艺术就能够进入巴黎市立现代美术馆?为什么他的作品就能够拍到“1.8”的数字?这位艺术家经常服饰讲究地出现在媒体(尤其是时尚媒体)和不少场合上,他的面部经常带有些许傲慢和透露出野心,他似乎也表现出越来越不屑于与其他艺术家共同举办展览,他甚至就是一副过去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上流圈层才能够看到的派头:雪茄、雪白的衬衣、品质不错的背心、锃亮的皮鞋以及隐而微显的深算——所有这些,都与中国大多数人对一位卓越艺术家的想象和形象设计并不吻合。显然,那些特别关心曾梵志的人并不太关心他的艺术,而是关心这位艺术家的肉身表面,关心他在社会或者世界不同场合的语境,关心曾梵志的言行在自己大脑里激活的那些八卦无聊的话题,最终,关心曾的作品所引发出来的天价数字。
坦率地说,尽管我至今也不时遭遇捉襟见肘的困境,对不少人津津乐道的所谓“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还是没有兴趣,为了多给自己一些自由,我也没有参加当晚各色“上流”人物聚会的酒会,但这不意味着我对之感到嫉妒或恶心,仅仅是自己的一种选择,这完全不是我分析艺术家的艺术问题的依据。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几天里,除了完成一些必要的学术工作,我还是去了一些曾经去过的美术馆,在维米尔、伦布朗、凡·高作品面前驻足良久,我再一次凑近作品欣赏了解他们的艺术。在巴黎市立现代美术馆,我看到了那些早年大师们(毕加索、米罗、德劳奈等)设计的挂毯,也让我觉得新颖,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些艺术家专门设计的挂毯,在我过去的认识里,这些先锋派是不会去做那些实用性设计的,尽管他们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艺术。
在中国,曾梵志因为“1.8”亿而再一次成为人们的焦点。然而可悲的是,人们关注的真正焦点是“1.8”。人们不关心一种艺术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关心艺术家创作的艰辛历程,不关心艺术家究竟在想什么,不关心艺术家的艺术的基本特征,不关心一位艺术家的艺术给这个社会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精神财富和有什么意义;而是聚焦金钱,猜测“1.8”亿的做局,甚至期盼他人“泡沫破灭”最终失败。就此而言,“1.8”亿反射出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贫困的时代,一个关于精神溃败的戏剧继续演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