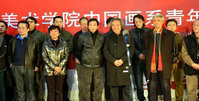李原原(深圳美术馆研究部)
最近关山月美术馆和中国美术馆相继举办“别有人间行路难:20世纪40年代庞薰琹、吴作人、关山月、孙宗慰西南西北写生作品展”和“走向西部:中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两个大展都将我们的视线聚焦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画家的边疆写生风潮上来。
从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现状来看,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40年代的边疆写生风潮作为大后方美术研究的重要范畴也被淡化。边疆写生风潮作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体写生潮流,其参与画家之多,写生地域之广,不仅对艺术家个人风格的转变和创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20世纪中国油画民族化和中国画改造两大重要课题都做出了坚实的探索,对后来西部美术、少数民族美术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回顾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艺术发展,在经历过文化保守主义、中西对垒与融合之后,逐渐向着开放、自由发展,民族解放的社会需要选择了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思潮和以写实主义为主流的创作方式成为了艺术家“救国”的武器。抗战爆发后,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战略价值凸现出来,边疆开发成为上至政府下至民众各阶层普遍关注的话题。在国民政府的倡导和社会舆论的呼声之下全国掀起了边疆开发的热潮。当“战地写生”、“救国画展”等活动在抗战地区大行其道之时,边疆旅行写生在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也成为了一种热潮。加之抗战时局的变化和艺术人才的西向迁移,当时很多重要的画家都参与了这股边疆写生热潮。如司徒乔的新疆写生、关山月的西北写生和漓江写生、叶浅予的川康写生、庞薰琹的西南苗区写生、赵望云的川西写生和西北写生、黄胄的西北写生等等。随着“敦煌热”的高涨,前往敦煌写生临画的画家越来越多,张大千、常书鸿、董希文、韩乐然、吕斯百、关良、孙宗慰、潘洁兹等等都是敦煌艺术的倾慕者。他们抒写西部空旷辽远、清新明亮的自然风光;描绘草原、高原上的风土人情、牛羊禽鸟;摹写、研究古代壁画和石窟造像,并汲取其中的艺术精髓融入到自身的艺术创作中。
如果说以延安鲁艺为代表的木刻艺术是以贴近民众、反映社会现状的写实风格顺应了革命斗争的需要,那么相比而言,边疆写生艺术活动更加注重对于中国绘画艺术本体语言的探索和发展。
从油画创作方面来看,在以“写生”作为中西艺术纽带的边疆旅行过程中,油画家通过表现西部高原清新明朗的地理特征和雄健质朴的少数民族风情,从中国传统绘画、石窟艺术、民间艺术从中吸收的技法,以往模仿西方油画阴郁沉重的调子和注重人物细节刻画的中国油画,开始呈现出造型概括简练,笔触轻松自如,色彩明朗、亮丽的整体面貌,形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油画民族化的典型风格。同样,这一时期的中国画改造也受到古代壁画和西方写实技法的影响,线条苍劲粗犷,用笔朴质豪放,嬴弱纤秀的文人气息转变为大气磅礴的民族豪情,也因此获得了传统中国画的现代转换。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油画民族化大讨论中提及的笔触韵味、平面造型、轮廓用线、装饰性色彩、构图安排等主题,其实在吴作人、孙宗慰、董希文等画家40年代边疆写生中早已经开始实践。边疆写生中对国画刚劲硬朗的线条探索在后来的新中国画运动中,顺理成章地服务于表现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生活新场面。而边疆写生中油画明快亮丽的调子和国画雄壮、豪迈的画风在这时也正好用于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政治表达,并且在其后的很长时间里继续保持着强大的活力。
在20世纪40年代的边疆写生之后,潘世勋、朱乃正、詹健俊、吴冠中、靳尚谊、方增先、李焕民、徐匡、周思聪等等一批又一批重要的艺术家通过西部写生创作走上中国美术的大舞台,谱写了中国西部美术创作的宏伟篇章,也愈发凸显出西部美术在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回溯西部美术的源头——20世纪边疆写生风潮,一代中国艺术家在烽火燃烧、社会大变革的年代,跋山涉水,历经磨难,怀着一颗向民族传统艺术学习的纯朴之心,用画笔发出时代最强音,其精神态度与艺术热情值得我们当下艺术工作者崇敬和学习。而这一写生风潮中所呈现出的极具承启性、开拓性的艺术史价值也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