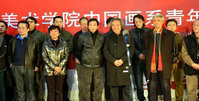文/孙琳琳
“我们时代最优秀的书法家的基础训练,超过了明清时期的许多知名书法家。新的任务是用书法做当代艺术,让所有人看见以后都说:哇!书法还能做到这个样子。”
时隔三年,邱振中又做了一次书法展,这次是在北京,恭王府嘉乐堂,47件书法作品、32方印章,绝大多数书法作品是这两年的新作。本来他是不愿意在一线城市做传统风格书法展的,因为这么一来,就显得太“书法家”了,他始终定位自己是一个当代艺术家。
开幕那天来了300多人,官方的、当代的、学院的、时尚的,都是冲着他的书法来的。邱振中有些感动,该他讲两句时,他说:“当一个人有幸成为一个专业工作者,他就知道有多难。我做了30多年,2007年才开始获得一些想要的东西。但当这个展览筹备完的时候,我已经对它不满意了,因为这里面没有反映我真正的理想。”
1994年,范景中为邱振中编了一本书法、绘画、诗歌作品集,取名为《当代的希绪福斯》,序言里,范景中将邱振中对自己的这股挑剔劲儿称为“神圣的不满”,这个提法深得邱振中平日思行的神韵。恭王府书法展开幕的次日上午,邱振中甚至专门组织了一个研讨会,他要宣泄他“神圣的不满”。
“对自己的作品我老觉得不满意,我设想的书法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既有自己的东西,又要让人震撼。”邱振中想了想,补充道:“要做到那样我起码还要两三个阶段。”
观众可能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是没关系,线条的抑扬顿挫你一定感知得到。
落日时分,恭王府的游客渐渐散去,绿瓦的大宅放松身心,露出它两百年前的样子,大风和金黄的夕阳降落在银杏庭院,走过10米宽的青砖箭道时,你很容易就被王爷与子弟们在箭道上跑马骑射的想象迷住了。
嘉乐堂的三个厅挂满邱振中典雅的书法,站在这里,即使没有学习过书法的人也能感受到,这样的草书跟前人的草书是很不一样的,不一样又一样高质量,跟中国传统有一种血缘性的、自然的联系,充满了优美的节奏感,力度与控制力又那样惊人。
这种推进是很艰难的。写草书最困难的地方在于迅捷流动的同时保持线条的分量和变化的丰富性,还要处理好空间的关系——每一个空间都有表现力,所有的空间都是一个整体。观看一幅这样的书法作品与观看抽象绘画的方式是类似的,观众可能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是没关系,线条的抑扬顿挫你一定感知得到。
看着邱振中的书写,你感觉站在了1908年写就《大地之歌》的马勒面前,站在了1911年指挥《大地之歌》首演的瓦尔特面前,他们神采飞扬,挥舞着指挥棒与唐诗唱和。
人人都说邱振中字写得好,好在哪里?“特别关键的是我有了一种信心,我们能够跟古人比。”他说。
对于一个在当代研习书法的人来说,古人是最重要的参照系吗?书法界一般这样认为。但是邱振中不,他关心的是:书法和当代艺术有什么关系?
“我们时代最优秀的书法家的基础训练,超过了明清时期的许多知名书法家,但我们不可能用古人的书法做当代艺术。”然而更重要的、难度更高的正是这一点,“那么多刻苦的训练和体会,在做当代艺术时就基本没用了,令人遗憾又震惊。”
“我们已经有颜真卿、王羲之了,难道一个年轻人写一辈子就做这个?”
一谈到书法创作,大多数人就会想到基本功,基本功是书法家的及格线,然而邱振中的希望是,未来能培养出两三位非形式主义者,除了写得一手好字,还关心文化修养,善于读书。
当学生向他倾诉迷惘时,邱振中总是淡淡地问:“你希望写到什么样子?”他期待听到一个清晰的理想,因为他相信,在谈到想做什么的时候,没有一点理想是不行的。
“不少人说,我要写到王羲之、颜真卿那样。我心里想,见鬼,谁要你写到那个样子!我们已经有颜真卿、王羲之了,难道一个年轻人写一辈子就做这个?你不觉得这一生不值吗?”
一个专业工作者一生一定要找到一个为书法而真正值得去干的理想,这个理想,实际上就是建立书法与当代文化的关系。做出那种作品,它既有古典作品的一切优美之处,又有视觉上的新颖感,让所有人看见以后都说:哇!书法还能做到这个样子。
要实现这个理想困难吗?听听邱振中“神圣的不满”就知道难度有多大了。但他知道努力的方向在哪儿。
“阅读和思考改变的是你这个人的综合状态,被改变了状态的人再去做某种创作,肯定跟原来不一样。”
这是邱振中的经验之谈,他平时做很多与书法无关的事,画画、写诗,阅读大量现代小说,也关注一切领域的讯息,比如去读关于世界舞蹈比赛的文章。
在研讨会的最后,邱振中引用了D.H。劳伦斯1913年说的话:
我知道这有多难。人要深刻地真诚起来,是需要一点东西的。琐碎的烦心乱神之事太多,搅得我们往往抓不到想象的真正本质。这听起来像胡扯,不是吗?我常常想,人在工作前,应该能够祈祷一下——然后就把事情交给上帝去。真正同想象较上劲——把一切统统抛弃,真是很难,很难的事。我总感到像是赤裸裸地站在那里,让全能的上帝之火穿过我的身体——这种感觉是相当可怕的。人要有虔敬之心,才能成为艺术家。我常常想到的是我亲爱的圣劳伦斯躺在烤架上说:“兄弟们,给我翻翻身吧,我这边已经熟了。”
做书法也要有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