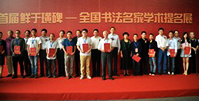-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吕澎:不要用光荣榜式的词怀念85新潮
吕澎没有直接参与’85美术运动,但也是和’85新潮站得很近的人。当提到“今天我们为什么怀念’85新潮”时,吕澎表示:“每一段历史都是承上启下的,过去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今天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昨天的基础之上。”与其说是怀念过去,倒不如说那是我们永远都脱离不了的根。尽管今天我们距离它越来越远,但历史永远伫立,为我们指明方向的同时,依然等待着我们发掘。

1992年任戬、吕澎、舒群、王广义在武汉大学(摄影:肖全)
85时期是一段承上启下的历史
记者:如今距离85时期已经过去了30年,再谈起为什么要怀念’85新潮,你有什么新体会?
吕澎: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肯定一点都不关心,我到过多个艺术圈,有些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不喜欢听到“85”两个字。实际上这个词只是象征性的标记,让我们说话更方便。它无非就是说80年代现代主义艺术的兴起和这场运动以及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今天的艺术是从那时走过来的,所以不可能脱离“上文”谈问题,今天无论是纪念、批评还是反感,都离不开那个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要讨论今天,很大程度上讲就要了解昨天。我们讨论85历史的目的不是说那段时间有怎样的辉煌——我觉得这些类似光荣榜式的用词都没有必要;唯一必要的是,我们要了解今天的艺术的时候,恰恰应该了解那个时期——因为那个时期正好是和1978年之前的艺术状况截然不同的时期,所以我们应该了解这段历史。
记者:所以’85新潮最实际的意义就是对今天的参考、对艺术史上的承上启下。
吕澎:对,其实我们就是在谈历史而已。’85新潮就是提示我们是80年代中期非常强烈的、明显的、各地都发生的现代主义艺术现象和潮流,无非就是讨论这件事。
写85时期的历史时已脱离了’85新潮
记者:在你的《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一书写作过程中,’85新潮的历史是否直接影响了你对整本书的写作思路和判断?
吕澎:写那本书有一个具体原因是,当时正值1989年,宣布了之前向西方学习的现代主义运动潮流,这其中的某种不合法性。因为都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艺术所产生的影响,所以从意识形态的标准上来讲,它是被压制的甚至是被否定的。但问题在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和那段时期很有关系——那段时期正是我们朝气勃勃的思想的时候、考虑问题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回头一想,如果过去十年的生活与工作都被否定的话,那么我们人生的意义都在哪呢?所以基于这一点,我通过写作艺术史来思考过去的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也是写这本书的前提。
记者:写那本书的时候,当时的社会背景与’85新潮时期的差异大吗?
吕澎:那段时间没什么太大的差异,虽然有一些新的现象,总的说来1988年、1989年跟1985年、1986年没有多大区别。但是有的批评家喜欢将1988年、1989年看作是现代主义差不多告一段落的时候,这种说法也可以,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太大差异。其实1989年之后,尤其是1990-1993年倒是有明显的变化,但那时候已经脱离了’85新潮,所以表面上来讲与85时期已经没有直接的关系了。
记者:85时期的艺术家基本都经历过“文革”,那时的作品和社会风气免不了受到影响。对你那时搜集资料、写作历史是否有影响?
吕澎:那时总的资料来源有三个:第一个是通过我们的经历和经验来做一个历史性的基本判断;第二个来源是艺术家提供的资料;第三个来源就是各类出版物。资料的来源现在还在挖掘,比如艺术家的书信集,或是他人的通信、艺术笔记,这些东西在陆陆续续地出版之后才能帮助我们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
研究’85新潮必须深入个案研究
记者:有人认为《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的书中,对’85新潮以关注群体为主,对个案研究不足,是否真的是这样?
吕澎:可能他们没有认真看书,个案不少。但是作为历史来说,它并不是艺术家的个案研究,所以不可能把他们放大到完全破坏体例的程度,这涉及到写作的体例问题,但是对艺术家的个案研究还是挺多的。
记者:今天我们再研究’85新潮时,参考不外乎是高名潞和你的书,似乎当下对此的专著还比较有限。
吕澎:其实两本书从充分性来说,不等于代表了所有的研究,所以以后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重写。从使用的文字量来说并不少,但是版本少;还有更多丰富的资料还比较少。这个问题的解决,一是可以通过不同的版本、不同角度的人书写来完成,再就是个案研究——对时代的研究有时要进入到个案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地深入下去。
记者:如果今天让你再重新写《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关于’85新潮这段是否会和当时不一样?
吕澎:也许会——资料、文风可能会有变化,但是说实话,基本价值观和基本判断不会有太大变化,只是写作的具体材料会有差异。
我呼吸了整个85时期的空气
记者:你不算是’85新潮的参与者,那么85时期对你最直接的影响是哪方面?
吕澎:我第一没有参加,第二我认为不是哪一个活动或者运动、团体对我有影响,而是整个时代的风气导致的影响。各地都有团体、有展览、有新的艺术、有活动,这种风气对我的影响很大,或者说我也参与了这种“风气”。但是具体的活动我是没有参加的,那时候我主要的经历是在翻译西方的美术史。
记者:1992年你策划广州双年展、发现艺术市场趋势的时候,是否受到’85新潮的启发与影响?
吕澎:这倒没有。那时主要是关注在新时期如何寻找突破口,从寻求方法和生存可能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种价值观对于我们来说无可评议,问题是这种价值观的生成和发展很困难——你得去寻找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在市场。所以那时候先办的艺术市场的杂志,然后才是广州双年展。很大程度上讲,是假设一个市场方向再去寻找可能性,但事实上是没有市场的。
当下对于’85新潮的认识仍有误区
记者:曾有批评家认为85时期基本就是西方现代艺术的模仿史,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吕澎:当时学习西方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从思想观念还是表现方法。但是当我们进入到艺术家个案的具体分析时,你会发现,就像文字有误读一样,当时我们的艺术家对西方艺术家的风格、手法的学习也有错位和差异。实际上他们是看到印刷品之后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去创作,在这个层面上讲,只是说国外的艺术家对当时我们的艺术家有方向性的提示,但是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却有很明显的差异。
记者:曾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后89时期”摘取了85时期的果实,你怎么看?
吕澎:这种表述是不准确的,90年代的艺术根本离不开80年代,就像今天的艺术离不开90年代的艺术一样。它就是一个承上启下、产生影响并不断变化的过程。“摘取果实”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我们今天的工作总是在昨天工作的基础上发生、发展,这个是无可评议的。但是它是如何影响的、之间有什么关系,需要具体来看。
历史的价值是永恒的
记者:85时期的很多作品至今依然受到资本群体的热烈关注与收藏,还有人将2007年尤伦斯举办的“85新潮回顾展”称作“有钱人的聚会”,甚至质疑为什么不在中国人的美术馆举办。
吕澎:作为艺术史上的艺术现象或是艺术品,收藏肯定是被资本收藏,但是与艺术本身并不是直接的关系。这只能说明85时期艺术的价值观是被资本所认可。反而是官方并没有收藏,所有的中国美术馆没有收藏,官方不认可这些东西。
记者:你认为’85新潮的参考价值与实际价值,在今天看来其意义依然重要吗?
吕澎:无所谓指导不指导、有用没用,它就是思想不断打开的过程中的一个表现。不存在什么“过时不过时”,当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它依然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怀念历史最重要的是正确认识历史
记者:无论是学术角度还是商业角度,你认为今天再提起’85新潮,最需要注意什么?
吕澎:每个人的历史观不一致,所处的位置不一致,因此对历史的判断也存在差异。最应该注意的,还是好好去思考那段时间的历史。
记者:你觉得’85新潮对现在的年轻艺术家是否还存在影响?
吕澎:无所谓影响不影响。柏拉图、苏格拉底、笛卡尔、罗素这些过去的人的著作,如果读过,那就一直有影响。但是不能说“我今天受到了柏拉图、苏格拉底、笛卡尔或罗素的影响”,话不能这么说——你只是通过从头到尾阅读后得到了很多知识,增强了思考的能力,这些东西都是无形中帮助你、在不断地判断新的事物。现在的年轻艺术家应该正确地了解’85新潮的历史——至于深入了解与否,还很难说;但如果他们没有基本的知识的话,应该算作是一种缺失。

- • 当代实验艺术巡回展在意庄美术馆开幕
- • 崔晓东山水画精品展将于11月15日在荣宝斋天津开展
- • 纪念刘奎龄诞辰130周年书画提名展在津开展
- • 德行是灵魂的力量-中国艺研院首届艺术硕士杨国欣
- • 当代实验艺术巡展2将于10日下午在意庄美术馆开幕
- • 韩国龙仁市市长郑粲闵接见姬俊尧等天津书画家
- • 组图:周祖达书画艺术展开展 70余幅精品力作亮相
- • 天津书画家朱毅赴昌都讲学 为法门寺送《心经》
- • 汲古得新·郭书仁、张大功师生作品展11月8日举行
- • 尹沧海师生书画作品展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哲学院举行
- • “天津第二届小幅水彩画作品展”将于11月9日举行
- • 墨韵禅心·张佩钢佛像展在东莞饶宗颐美术馆开幕
- • 书法家李德海、花鸟画家李伯增联袂在津办展
- • 记《弘一大师李叔同篆刻集》新编增补本编辑出版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