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曾焱:我们为什么要看当代艺术
我们为什么要看当代艺术?我为供职的杂志写了好几年当代艺术,好像还没有正经思考过这么形而上的问题。
我试图把难题转嫁给当代艺术的制造者——当代艺术家,比如张晓刚老师。张老师正在工作室里埋头准备他最近刚刚在北京佩斯画廊开幕的新作个展,无心于纠缠问题和主义。他简单而迅速地回复说:当代人必须要看“当代艺术”。
是啊,为什么不呢?答案就这么简单。我被艺术家这种完全下意识的“不负责任”的回答说服了。不过这让我想起了几个月前的一次采访,张晓刚讲述的一段经历,当时他是为了回答我,为什么他会像现在这样画画,为什么会有《大家庭》。

试图恰到好处地表达生活
张晓刚1992年得到一个机会到德国呆了三个月。那个年代出国不易,于是就像所有第一次出国的中国艺术家一样,他虔诚地扑进博物馆,日日去拜谒那些只在艺术史中读过的大师名作。当时欧洲还没有申根,为了看梵高、伦勃朗、维米尔、德拉克洛瓦,他从德国非法过境到了荷兰和法国,跑了十几个城市,看了几十个美术馆和画廊。在卡塞尔他混迹了将近一个月,因为1992年正好是五年一度的卡塞尔文献展,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最当代的最牛的艺术都集合去了那里——从录像大师比尔。·维奥拉到大画家图伊曼斯的作品,他都见识到了。
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张晓刚说,他悲伤地觉得自己几乎要成为一个完全不懂艺术的人了。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确定是不是还要继续从事艺术:自己崇拜的西方艺术已经将所有能够想到的概念都表达得如此好,还需要一个中国人来献身它吗?他记得在阿姆斯特丹,坐在梵高博物馆台阶上的那一刻,深感绝望和无助。
然而那三个月经历的狂喜和茫然,终究还是帮他在思考后得到自己的结论,并折转了艺术方向:“……过去,我们总认为艺术就是我们从书本中学习艺术的一个结果,我们忘了将我们的历史和生活的环境加入其中。特别是当我回顾我所钟爱的大师作品时,我才发现他们实际上只是在试图恰到好处地表达他们感受到的生活。所以,突然之间,这一结论点醒了我,似乎让我悟到了属于我的那条路在哪里。”回国后,他画出了《大家庭》。


重叙这个采访故事,是因为我突然觉得,它其实也回答了“为什么要看当代艺术”这个问题。也许它和“为什么要做当代艺术”有着同一个答案——不过是因为我们需要恰到好处地表达我们的正在发生、我们感受到的生活和处境。
是的,我们都热爱博物馆和美术馆,也从里面那些已经被时间和艺术史反复淘洗过的伟大作品中,得到最正当的价值确认,接受最美好的艺术熏陶和知识传递。但这些对于很多人来说还不足够,他们还需要另一种艺术,那种带来切肤之感的观看:可能泥沙俱下,面目混杂,令人狂喜也令人失望;而就在不确认的怀疑、失望和触动中,在艺术史和现实之间,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恰到好处。
中国当代艺术“后感性一代”的代表刘韡,对材料的选择就有严格的属于这个时代的美学边界:这个材料必须是日常生活中唾手可得的,必须是廉价的,完全不能用昂贵的材料,而且必须是传统意义上“不美”的。比如他使用军用帆布和废弃书籍等材料来指涉异化的城市概念,而对应艺术家自身处境的是,他的工作室正被拆迁,被瓦砾包围的门上写着大大的“拆”字。对刘韡来说,有创造力的表现,并不是创造出新的东西和使用新的媒介,而是有能力带给材料一种切身的当代性。
出身于1986年的更年轻的陈天灼,却认为最令人恐惧的是日常,因为在他看来,日常会带来朝向死亡的无形焦虑。他的设问是,艺术创作如果可以制造一种时间和空间,在其中人们忘却了日常,超脱了日常和死亡,真正“High”起来,这就是做艺术家比别的职业更幸运的地方。
当当代艺术更多成为身体、思想在空间中的“运动”和“相遇”,从前如神殿一般的美术馆也并非不为观众而改变。英国泰特美术馆前馆长克里斯·德尔康在接受我采访时就说过,现在很少有人还会像从前那样去完完全全地膜拜艺术品,当代艺术的观众对美术馆的需求更趋多向,他们不断提出问题,触及文化,也触及宗教、性别、民族、环境,并希望在这里寻找困扰自身的某些问题的答案。
每个人总会遇到一件打动自己的作品
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艺术史”,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同样是观看者。所以我喜欢在采访中问他们同一个问题:你被谁的作品打动过?
美国录像艺术大师比尔·维奥拉跟我说,他最喜欢的艺术家之一是俄罗斯人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Tarkovsky),尤其爱他的《潜行者》和《安德烈·卢布廖夫》,因为塔可夫斯基通过复杂且多层次的有力量的图像、非线性叙述以及对现场的持久观察,来描述内在和外在情境,这使得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英国当代雕塑家安东尼·葛姆雷最爱前辈贾科梅蒂,所以他自己在创作中更感兴趣的是找到一种途径,去感知贾科梅蒂所说的“对现实的追求”。
在大师之外,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年轻艺术家的“艺术史”:
梁远苇从纯粹观念绘画的困惑中回返到向古典传统视觉作品寻求解答。她从高居翰关于元代画家的历史论述中,认同了绘画可以作为知识分子思考自己当代性的媒介,而中国历史上的文人画运动通过绘画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前卫性。在2016年的新作中,她的学习对象变成了元代的画家王蒙和古罗马的庞贝壁画,她觉得王蒙的东西总是在翻滚,有一种靠线的运动获得的神奇的生命力,而庞贝则是用平面延展空间或拼贴空间的经典,是具有强烈现场性作品的代表。
这些都是艺术家所理解的艺术。那么,当代艺术需要公众理解吗?回答这个问题前,不妨再来讲两个当代艺术家的故事以及他们所理解的公众。
导演史蒂夫·麦奎因(SteveMcQueen)以《为奴十二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世界上最为人所知的电影奖项。而在这之前,他是一位当代影像艺术家,尽管非常着名,还不到30岁就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了个展,两年后又获得英国最负盛名的当代艺术奖项——特纳奖,他的作品也只是在美术馆和艺术双年展这样的场合看得到,名字仅仅在艺术圈传播。对于麦奎因来说,决定转向叙事电影,是因为他觉得当代艺术这个世界太小了,他希望为自己想要表达的某些特定的话题去寻找它自身的观众。


而我采访过的另一位德国当代影像大师法罗基(在采访之后半年,他不幸病逝),却正好做了与麦奎因相反的选择。
在50岁以前,法罗基是作家和着名电影人,他的作品主要是在电影院和电视里放映。而二十年之后,70岁的法罗基是德国最具关注度的当代影像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深度游戏》、《严肃游戏》由世界各地的着名美术馆或画廊空间来呈现,他参加了卡塞尔文献展和威尼斯双年展,并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了个展。他也主动选择了自己的受众人群:他拍过一部电影《关于一场革命的录像带》,1993年在柏林两家影院上映,总共只有两名观众买票入场。但当他在2011年将影片带到纽约MOMA时,每天都有数千人去排队。
法罗基和麦奎因都为自己认同的媒介选择了受众,而不同的是,麦奎因在叙事电影中获得表达空间,而法罗基认为自己从当代艺术中获得了表达的自由度——当代艺术和公众,其实是一种双向开放的关系。

前些天我去艺术家向京工作室,也聊到艺术家和公众之间的这种关系。她说了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那就是关于艺术家的“特权感”:因为艺术家是一群被天赋“赐予”了艺术语言能力的人,艺术家难免会感到自己掌握了某种点石成金的表达的特权,而他们又经常迷惑于这种特权。艺术家如何对待这种“特权”,最终也许就成了好艺术和垃圾艺术的那条“冯唐的金线”。
自从贡布里希在他的《艺术的故事》里写了这么一例金句,“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人们就喜欢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相信艺术,还是相信艺术家?其实,作为一个有幸可以脱离艺术市场语境的观看者,在当代艺术面前,相信自己就可以了。

“好的作品不提供答案,而是提出问题,观看者以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来回应,这样便构成一件完整的作品:它可以是一种情绪,一种心态,或者是观看者自己的问题。”作为创作者的录像大师比尔·维奥拉的自省,其实也给了观看者最好的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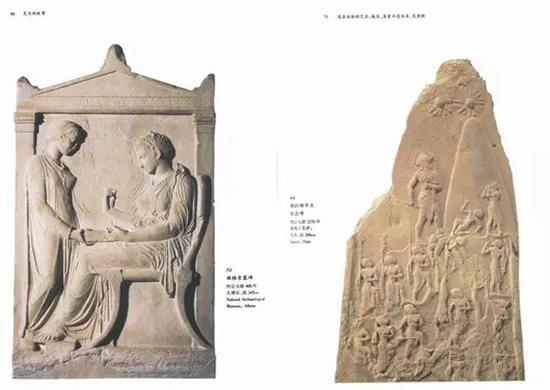
当代艺术没有什么了不起,观看当代艺术也不需要装模作样。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每个人都想要一点答案,不是吗?(作者 曾焱)

- • 齐治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书法篆刻展在天津文联举行
- • 马元:艺术侠客—忆我的先生张世范
- • “结对子、种文化”天津画院赴北辰区开展交流活动
- • “顾志新师生暨道友诗联书印合璧展”名家荟萃
- • 水·色·韵—王刚水彩展在乐天百货MVG画廊开幕
- • 组图:天津六画家赴宝岛台湾开展学术和文化交流
- • “李建平版画作品展”10月24日在泰达图书馆开幕
- • 诗情画意—高凤楼书画展在文登区博物馆开展
- • 组图:津门七位书画家雅集汲墨轩书画院
- • 《画畵》八岁了!政协书画艺术研究会办展为其庆生
- • 扬子晚报用整版篇幅介绍津门艺术家马孟杰书法展
- • 杨德树长征路写生展在天津图书大厦书天艺苑开展
- • 朱森林漫画展在津启动“坏老头”将巡游全国
- • 组图:天津画家陈钢在加拿大举办“长城中国画展”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