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篆刻艺术发展动力的史学诠释

我对2009年初夏公布的上海高考命题作文题记忆犹新,要求是以郑板桥的书法为材料写一篇议论文,对其“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后人评价发表看法。“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这个对当今高中生来说仍属生疏的名言,让我立即联想到了韩天衡先生,因为韩天衡先生有一篇在篆刻界非常出名的文章,用的就是这八个字作为标题,它后面还有个副题“论五百年篆刻流派艺术的出新”。但是这篇文章发表于1981年的《美术丛刊》上,离2009年高考相去已二十多年,显然那些莘莘学子是难有可能备先见之明,去受受韩先生这篇论文的滋养而获得加分机会的了。即使自感关注学界的出版人如我,也是因多人论文中常援引韩天衡先生的这篇文章,才在脑海里留下了印象,而并未去觅取原文来拜读一番,说起来这真是件惭愧的事。但老天终究是要命我在韩先生这篇文章中获取可贵教益的。2009年我们合作出版了韩天衡先生领衔主笔的《篆刻三百品》后,在与韩先生的交流中得知,他在将给我们的另一部重要书稿中,正是要以这篇文章为纲领,全面阐述五百年来的篆刻艺术发展史。这实在让我满怀期待,并下决心以审稿机会更多地了解韩天衡先生彼时此刻整整三十年来印学研究的学术思想。今天,这部从一万字扩展至十五万字,汇集四百多方钤印及众多印学史料,全面、系统地论述明清以来篆刻流派萌发演化的脉络,着重开掘、阐述五百年来印章艺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命名为《中国篆刻流派创新史》的著作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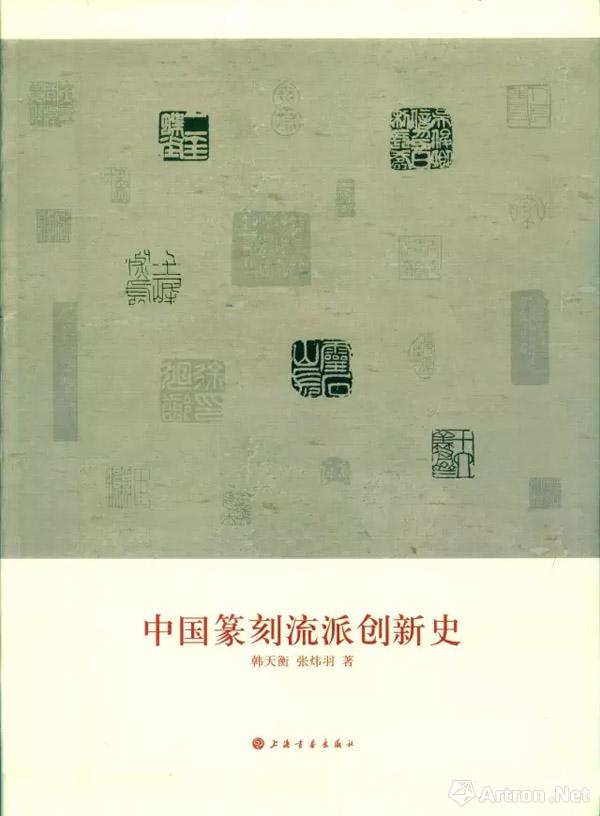
《中国篆刻流派创新史》
其实“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出处远早于郑板桥时代,《南齐书·张融传》载:“(太祖)见(张)融常笑曰:“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后人常以此典来比喻不可多得的异才。韩天衡先生将其冠之以论文篇名,又扩充了它的内涵,使之成为其篆刻艺术研究的基本史观。探查论文发表的当时背景,正处于“文革”后篆刻艺术复苏期。此时篆刻学习资料相当匮乏,广大青年篆刻爱好者对明清流派篆刻中错综、纷繁的发展脉络与艺术风格还是懵懂混沌,无从系统领略、学习到前人的艺术遗产。而韩天衡通过自己的刻苦勤奋,并借各种机缘的广泛涉猎,以二十余年艰苦的探索与锤炼,将自身的篆刻创作推进到成熟期。他不仅被明清流派篆刻艺术中开山巨匠们的创新奋进精神所折服,更清醒地认识到艺术创作如守旧恋古是完全没有出路的,只会是别人的附属品。《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论文的发表,对明清流派篆刻中创新家们成功的奥秘作了细致、深入的剖析,并鲜明地提出了他的篆刻艺术史观,以及自己艺术实践的主张。这一观念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还热衷于模仿吴昌硕、齐白石等为能事的篆刻作者来说,无疑是超越时代。
《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论文发表至今已整整三十年,而这三十年可以说也是当代篆刻艺术发展最为繁荣的阶段,这与韩天衡先生的身体力行,并有意识引领将创新视作为艺术家的普遍实践认知,是有重要关联的。但随着艺术面貌个性追求的多样性发展,传统和求新,这个永远争论不休、难以把握的一个难题,在当下新生代篆刻爱好者中,也出现了不少忽视传统,亟力模仿当代流行印风的倾向,韩天衡先生再次看到了与三十年前相反,但实为五十步与一百步的问题,因此认为有必要重提篆刻艺术创新的话题。《中国篆刻流派创新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韩先生的又一部研究型著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韩天衡先生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印学史料的爬梳整理和研究,由他执笔的《中国篆刻艺术》,以及《中国印学年表》、《明代流派印章初考》、《五百年印章边款艺术初探》、《九百年印谱史考略》等重要著作和论文的先后面世,都使得他的艺术视野更加开阔、学术根基更加深厚。《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论文的时代性与篇幅局限性,当时论及作者的下限仅至齐白石,特别是对建国以后篆刻艺术的创新作者无法作叙述。而此次《中国篆刻流派创新史》将下限也延伸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方去疾先生,采集更为丰富的史料,并以明清流派篆刻发展史观进行统筹,对各位创新家的代表作与时代背景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鉴赏与论述。
“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这一极具哲理意味的命题,基本概括了韩天衡先生的辩证艺术史观。“不可无一”,标刻着历史进程中传统承续的连接点;“不可有二”,则是傲视同道的霸气和流风后世的范式建立。这一命题中,韩天衡辩证地转换视角,在古人和自我之间,在传统和创新之间,给出了双向的选择,即让传统中有“我”,让“我”中有传统,用传统修正自己,用创新来激励自己。
在艺术学发展史上,创新是一个早就为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不断认识、开掘内涵的命题,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已专设《通变》一章,详细阐述“通”、“变”的内核,并辩证阐发了继承(通)与出新(变)的关系,变就是创新。在明代第一部印论专著、万历年问的周应愿《印说》中,亦专辟两章分别冠名《创新》《变化》,就文人篆刻渐为风尚,篆刻艺术实践有所积累,及时提出了探索印章艺术的审美标准和创作观念,指出“古法固须完,新意亦可参”,并以《周易》“与时消息”来阐发他的创新史观。“入古出新”、“通古变今”,后代篆刻大家正是高度重视了这个命题,并以个人与群体相融合的方式予以实践和认知,创造出了一个堪与秦汉印章相媲美的艺术高峰。

韩天衡先生在本书中正是总结前人的艺术理论,并将这一重要命题以史学的视角加以高屋建瓴的观照。他曾经将“推陈出新”改为了“推新出新”,虽一字之改,但却别具新意;并阐释“推”是推进、推动,而并非推翻、摒弃。他的理论是“艺术必须‘推陈出新’,别无它途,而其本质在于‘推新出新’。那些以往大师们经典传统的、我们无数次模仿的作家和作品,它们都是当时开创的新面孔,时空并不能遮盖它新的光芒。我们要学习往日之新,推出今天之新”。他的这个理论的依据来源,就是在书中援用的大量创作例证基础上,条分缕析后得出的艺术发展规律性的总结。传承是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创新则为之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这无疑是韩天衡先生对近五百年来篆刻流派发生发展的规律无比犀利的洞察。
除上述论述之外,《中国篆刻流派创新史》还有以下几项主要特色。
一、以篆刻发展史观和流派孳变视角遴选篆刻艺术家。
五百年来篆刻艺术史中的作者数不胜数,而真正能匠心独运、自创风格的也寥寥可数。本书选入的46位艺术家,均为流派的开创者和发展大家,或者是具有敏锐的创新意识、作品风格新颖的先进者。其中有像丁敬、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黄土陵、齐白石等开宗立派的大师,他们不论在篆法、章法还是刀法方面都作了前无古人的全面变革与创新。其他还有像曾衍东、赵穆、谢磊明、丁衍庸等长期被人忽视,或在某一技法方面能锐意创新的作者,都在该书中作了挖掘。而像在明末清初士大夫们以“不得一篆则心耻以为欠事”的胡正言,与吴昌硕等并称“江南三铁”的王大炘,吴昌硕得意弟子徐新周、王个簃等,虽生前印名颇盛,但以篆刻艺术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其创新元素甚罕,本书则摒弃未录,因此可见著作者之用心。
二、全书体例严谨,脉络梳理清晰,编排主次分明。
全书论述有主次、纲目之分,版面划分清晰,既突出了流派开创者的地位,也反映了群星璀璨的历史盛景,可以一览诸篆刻流派的谱系脉络,如:明代文彭、何震、苏宣、朱简、汪关及清代诸位开山大师,都放在重要的位置,而取法前人一翼加以发挥完善者,其艺术成就与历史地位是不能与开创者相提并论的,则置于从属的地位,虽如晚清杰出的篆刻家吴熙载,在现代印坛名气极盛的邓散木等人,也在所难免。这一论述和排序,充分体现了本书作者站在篆刻艺术历史发展的高度,所采取的辩证、客观、公正的论述方式。
三、通过对入选作者的代表作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来梳理流派篆刻的艺术价值和创新意义。
作者对数十位创新艺术家的作品不做虚空、浮泛的评论,而是通过对几百件代表作进行详细剖析,做到辨析入里,言之有物,并时时涉及到作品创作时的政治、社会、考古等历史背景。另外像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等创作数量或风格繁多的篆刻家,对他们作品的艺术形式进行了全面的分类、归纳,使读者在欣赏和创作时均便于对照,看清脉理。
四、全书引入大量新发掘的资料,体现了最新研究成果。
当代诸多篆刻书籍中的刊载资料往往局限于常见的几本,以致引用的图版翻来覆去,使读者易失去新鲜感。而本书作者大力挖掘新的资料,甚至不惜重值去购买原拓印谱。像苏宣的《苏氏印略》、赵穆的《小瑯环室藏印》和齐白石早年印谱等,均为传世无多的珍贵谱录。这些罕见印蜕资料的引用,使读者对他们篆刻创作的来龙去脉认识更为清晰。对他们风格的多样化愈加欣赏不已.更增添了本书的可读性和原始史料价值。另外像传世无多的文徵明、文彭父子篆书作品,赵之谦著名的“仁和魏锡曾稼孙之印”中倒立马戏阳文边款所参考的汉代画像原件,以及对一直盛传齐白石常以肘臂顶刀杆刻印的误解,都有作品或照片作了很直观的例证,这些也都是他人著录中所未见的。

我拜识韩天衡先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时我有意约他撰写一部有关历代印章艺术鉴赏方面的书稿,那时韩先生还在上海中国画院任副院长主持工作,非常地忙碌,结果是未能如愿。时光荏苒,十余年后,我有幸专门从事艺术领域的出版工作,再次拜谒了韩天衡先生,得到了他的极大支持,可谓是“再续前缘”、如愿以偿。在韩天衡先生的精心组织、主笔下,仅以半年多的时间便高品质地出版了《篆刻三百品》一书,获得极大成功。在编撰《篆刻三百品》时,我多次聆听韩天衡先生召集参与写作的弟子,讨论撰稿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深感其治学之严、学养之厚,尤其是对篆刻艺术发展、流变的轨迹和规律具有深刻的洞察,“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推新出新”,便是他艺术史观最形象最概括的语言,经常用来说明文人篆刻艺术发展的内在动力。今天这部《中国篆刻流派创新史》,以更为系统的架构、更加翔实的史料,辨析入里地阐述了篆刻艺术的复兴时代——明清以降的流派时代及其艺术精神,堪称是韩天衡先生数十年来学术思想的结晶。这不由得让我自然联想到,韩天衡先生自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成名以来,又经历多次嬗变突破,形成了奇中见平,动中见静,传统意韵深厚,又独标时代风貌的艺术风格,已卓然成为当代大家。毫无疑问,韩天衡先生正是以他从艺术史研究中获得的历史启迪,指导了他的创作,并以他的艺术实践诠释了他的创新史观。我为自己三年中见证和参与韩天衡先生两部重要著作的出版,感到无比的荣幸。
张炜羽君是韩先生的亲炙高足,长期在韩天衡先生身边接受熏陶,其性也恬淡,其思也缜密,治印近三十载,以楚简帛文字入印,气息古雅,已获褒赞,又深谙“印外求印”道理,孜孜浸淫,增进旧学素养,于篆刻史格外探究,筑起厚实基础,《篆刻三百品》已获见其功底和识见。今乃师再度相中于他作为新著助手,无疑是对他的最大肯定和信任。现观其文,颇感其刻苦不懈,史料收集详备,演绎丰富,且能将韩先生要义领悟融会,并贴切生发,应未负所望。放眼时下,能如此敏而勤奋、兼顾学艺与学术者,实属难能可贵。
人类美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美的探索的历史,而美的探索源自于人类对于审美理想的精神追求。真正的艺术家应排除名利,百折不挠,探索不止,因为创造美才是艺术家的使命,才是艺术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也应是衡量艺术家思想境界、艺术境界的重要标准。我们研读《中国篆刻流派创新史》,顺着书中所梳理的脉络,历数历史时空中一位位皓首穷“印”、耕耘方寸的篆刻家的身影,或许也能认同这种观点,并将这种启迪运用于当下的艺术创作和印学研究中去。
我学也晚,未探印学门径,本不敢在前辈著作前“大放厥词”,但因韩先生直命在前,难以不从,只得写下林林粗陋之见,惟祈天衡先生、炜羽君与广大读者勿责咎也。(作者 王立翔)

- • 《况瑞峰书八体千字文》捐赠暨签售活动在津举行
- • 天津书画名家追忆李克玉先生:德高望重 德艺双馨
- • 大象无形-唐洪勝个展4月25日在山东青州开展
- • 经典·求同—封俊虎书法展4月27日在北京开幕
- • 天津书法名家走进滨海新区为书法爱好者点评作品
- • 三晋名家名师名教协会走进朴墨心画院开展艺术交流
- • 津门书画名家“诗画秋浦 醉美池州”活动风采
- • 《马寒松古代人物作品精选》近日出版发行
- • 祖国颂-申世辉山水画创作及教学成果展4月29日开幕
- • 天津政协花鸟画研究院成立暨作品展4月26日举行
- • 凤舞祥语-陈之海中国画作品展在天津图书大厦开展
- • 美丽中国文化之旅张大功中国画作品展在青州开展
- • 南开大学秀山画会成立仪式暨首展4月29日举行
- • 天津市中国美协、中国书协会员专题研讨班圆满结束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