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临摹与创作是书法界的永恒话题,是每一个书法人都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只要你拿起毛笔写字,就绕不开它。
每一个人对临摹和创作都有自己的见解,可是如何把这个问题讲深讲透,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临摹的问题,创作的问题,从临摹如何过渡到创作的问题,每一个方面同时也包含着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技巧、方法的运用等。如何去学帖,如何去读帖,如何把它写准、写像,如何意临等等,都是技巧和方法的问题,同时又包括观念和见解的问题。
有道是“生命不息,临摹不止”。临摹是每一个书法家一生都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但临摹就是单纯地临吗?看作品的时候,点画的长短、粗细、枯润、方圆、锐顿等各个外在的方面都可以看到,但书法的点画背后往往还有很多的内涵。这就导致了表面上看书法虽然简单,但是深究起来,却能细细品味到非常多重要的因素。因此,临摹的时候既要敬畏古人,但也不能盲从,要带有批判的精神,不断地发问,挑战自己,还要善于比较。
临摹是为创作服务的,一个书法家如果只是个临摹高手,最后写不出具有个人风貌、个性强烈、被他人普遍认同的书法作品,那么他也是不成功的。如何在个人创作中体现自己的面貌?本期,我们整理了浙江省书协主席鲍贤伦和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上海市书协副主席刘一闻关于“临摹与创作”的谈话,在本报刊发,重温临摹与创作这个“老”话题。
鲍贤伦:临摹是学书的主要方法
临摹是与古人对话
临摹几乎是学习书法唯一一个可取的方法和路径。绘画可以临摹、写生,然后中得心源。学习书法,除了临摹,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取得进步。我认为临摹的根本意义在于获得书法技法的能力,强调的是一种能力的获得。很多人,包括我们这些从事书法的人,比较在乎临摹临得像不像,像就是好,不像就是不好,从某个方面来说也是对的。但又不那么简单,如果我们对技、对能(能力)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会停留在一般的模拟上。此外,临摹是一个持续性的行为,常临常新。可以武断地说,中年以后,临不临帖几乎决定这个书家晚年的成就高低。
临摹不仅是一个功利性的手段,还可以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生命方式。置身于书斋,面对古人的书迹,临写的过程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享受。临摹时我们似乎在和古人对话,在搭古人的脉搏,体会古人的笔是怎么落、怎么走、怎么结束,用心体会他的书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度脱离了先前的状态。这就已经不单纯是写字,还包含了一个人的修为,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实践。而创作,却需要稍作克制。因为创作是带有一定情绪的。这种情绪会使人兴奋、高昂,就是创作的活力,是一种生命的巅峰状态。但是人不能总是处于这种状态,还需要一种稳定、平和、可持续、可维持的状态,临摹恰恰可以满足人这种生命状态的需要。
在学书的初级阶段,有老师比没有老师好,有一个好老师更是万分幸运。所有人的学习都是在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老师把他的经验灌输给你,这是最快捷、最好的一个办法。但风险性也很大。真正的好老师确实是屈指可数,如果一开始没有一个高的基调,那就可能定下了你以后有限的前景。
关于临摹,不能把它简单化,临摹对每个人的作用是不完全一样的。在什么阶段临什么、怎么临?一般来说,我们会从正草隶篆里选择一个点开始做。我的老师徐伯清先生,他让我写隶书,开始就写隶书是写不好的,但他要达到一个目的,而且非常明确,就是“正手脚”。横平竖直,先把手脚调正,我觉得很有道理。几个月后,他说你写草书吧,怎么隶书还没写好,又让我写草书呢?他说你写吧。开始也不懂,就照着帖子去写。这样写草书能写得好么?也是写不好的,但是他却告诉我一条:笔画和笔画是连贯的,这一笔的开头是和上一笔的结尾紧密联系的,过程是动态连续的,这是写草书最直接了当的感受。有了上面两个感受,徐老师又让我写楷书,这个时候写楷书,理解结构、起收笔以及笔画之间的联系就不那么困难了。对学习过程的设置,不同的艺术家、老师都会有他从教育角度做出的考量。跟着老师学以后,我们还要很快确定下哪些东西是和自己最契合的,感觉契合的就容易写得好,看着不顺眼的,可能就很难写得好,或者要花特别大的劲才能写得好。
当你确定下一个点、一个方向以后,还要下“遍临”的功夫。比如写隶书,就要遍临隶书,写篆书,就遍临篆书。遍临是一种普查性质,如果不普查的话,就不知道自己所涉足的这个领域到底是何种状况。普查后才能认清差别,做到大致有数。然后再确定一个自己特别中意、特别有感觉、自己有较强解读能力的方向,锲而不舍地写下去。大家深入的程度不同就造成了一个金字塔的结构,谁深入的多,谁就到塔的上端去,大部分人都是在中间,甚至在底部。说某个书家真草隶篆皆能,遍临诸帖,这个“遍临”还要看它的作用在哪里。
临摹到了一定阶段,就不单单是你和某个古人之间的事情了,还要面对一个时代,面对整个书法史,面对一个更为庞大的架构。往往是越往下临,出现的问题就越多,自己的想法也越来越复杂:假如我们再深入一下,整个汉代就是这样的吗?那些碑都临过了,摩崖也临过了吗?简牍临过了没有?汉是从秦过来的,秦代的字到底怎么样?秦代没有隶书石刻,但有木简,秦代再往前又是什么样的?往后看,汉以后隶书出现了一个衰落的局面,一直到清代的异军突起才又有了起色。秦汉和清代首尾呼应,中间是一个断档。两者一比较,各自的长短在哪里,区别在哪里?学秦汉还是学清代是两个不同的取向,如果要学秦汉,那要想,和秦汉以后的书法——正草书的审美判断有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还要读一读秦汉的历史,看一看秦汉的其他艺术品。看了以后,我们还会发现一些问题,如秦汉之前基本上是没有个人书法家的概念,个体书法家意识是到了东汉才出现的。汉代几乎是一个分水岭,是古今文字、书法的自觉期和非自觉期的分水岭。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是我们理解秦汉隶书的一个重要线索。所谓的秦汉,它是一种大的气象,人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不仅在书法上,在其他艺术品的创作和生产制造上也是一样的。这种情况是随着汉末哲学的发展,个人意识的觉醒而改变的。个人意识觉醒以后,书法家就不再满足于整体气象的表现了,而是开始把个人的感受和更细腻的情感反映到书法当中去了。大家就开始出现了竞技的意识,我要和你写得不一样,我要比你写得好。整个东晋实际上就是文人之间的相互陶染,在不动声色的竞争和比拼。有人问我的字为什么这样写,你要追求什么?我就说既然写秦汉,我就觉得格局和气象是首当其冲的,站立在这个制高点上,就可以做得比较的特殊。因为一般人学隶书都是庙堂汉碑写得比较多,所以他不得不拘泥于起笔和收笔、蚕头燕尾等等。他没有把注意力辐射至一个时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风格是当代性命题最合适的选择
临摹是入古,是获得古人的技法能力。在这个入古的过程中,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主体性地入古,这不是对古代的不尊重,而是最积极、最高级的尊重。带有主体性的入古,实际上也是在培养自己的解读能力和转化能力,也是为进入创作构架桥梁。
创作依靠什么?一块基石是从临摹中不断获得的技术支撑,另一块就是你的性情。性情一半是先天的,一半是可以靠后天培养的,所以要多读书、多观察,养胸中的浩然之气,养温柔敦厚的书卷气等等,在临摹与创作中,有时还会起到导向性作用。法度是一个客体性的东西,作为主体能动地去学它,只有当技法变成能够为你所用,它才是有价值的。一个人不可能把所有的技法占为己有,也没有必要。人的审美都是有倾向性的,这一方面占了上风,另一方面就会弱一些,甚至是不需要的。技法也是这样,选择哪一种技法,就在于它们合不合你的性情,性情实际上是审美倾向的主导。
对技法的传承,我们每个书家都不要自作多情地以为这个事情须要由自己来完成,这么重大的历史课题靠一个人怎么可能完成?每个人只要完成一部分就可以了,最终的延续要靠我们整个集体来完成的。我们要面对的是传统书法和篆刻的当代性价值的问题,这些东西传承到了当代,应该用什么去承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去做?有那么多人,好不好呢?仅仅把古代的东西传承下来,仅仅是在这个传承过程中,得到一些熏陶吗?显然不是。传统的东西到了当代要有它当代的新东西。
我觉得当代性的命题最合适的选择就是风格。你可以写出全新的东西来表达自己的特性,也可以把古人的东西学得很到位,然后传承给下一个时代。但这两种方式都有毛病:新的东西必须是要和传统有逻辑发展关系的,是内在的自然发展;同时我们还必须是有发展意识的,回顾书法史,每一个出色的书法家在他那个时代都具有其不可替代的当代性。
而风格恰恰是一种逻辑发展的结果,历代书法都是风格的不断生发伸展。风格问题不是图式的问题,不是形式感的问题,它是一个旗帜鲜明的价值判断,原来的审美经验提供你的新经验,给审美领域要提供新东西。风格的出现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出现得早些,有的人晚些,绝大多数人可能终生都没有。风格对于一个书家的要求实在太苛刻了。而且在风格形成的初期有人也是很不顺的,齐白石刚到北京时也是不顺的,是靠陈师曾、徐悲鸿一些人力挺他才起来的,所以有的时候,风格的形成也是迫不得已。
但一旦有了自家面目,也就将自己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你切断了其他的可能性,而只留下了一个可能。但是对于这个可能,你也不一定走得过去。关于风格的这个命题,描绘一下基本状态:开始的时候,灵光一闪的时候,如果你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有可能就把它选定了,它是瞬间来的,你也要当机立断,取舍定夺。你要把它变为自觉的立点,这个立点非常鲜活,但也非常地不稳定,通常你的表达会过分,会夸张。过分的表达是风格形成的初期一个必要的阶段,写不好也不要觉得惭愧,没有过分,没有不恰到好处,就没有后面的发展。只有觉得哪里感觉不对,你才会去调整,调整到一个比较坚固、合适的方向去。之后你还会觉得不足,还会用其他的方法来调整,进一步地去突破。
风格之路上总归是免不了要反反复复,曲曲折折。说不好怎么去把握分寸,因为分寸感是动态的,随着你的年龄、见识、经历的增长,甚至随着你的肌肉、神经等等生理的变化,它们合成的状态都会不一样的。关于风格我想说:它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又是主体不断选择、提炼、强化、调整、生成的过程,急也急不得,有了也不要谦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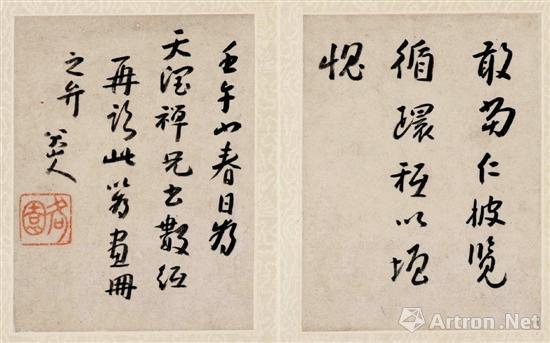
刘一闻:临摹是不断的体验和实践
有见识地去临摹
临摹和创作,这个问题几乎和每一个搞书法篆刻的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书法和篆刻是传统文化,是两门传统艺术。无论是广义上的或是狭义上的借鉴,都是跟临摹有关系,所以,平时写字也好,练习书法也好,学习印章也好,开始那一步一定是临摹,是绕不开的。谢稚柳先生曾经说“借鉴之道,是借鉴愈深则自创愈高。”虽然没几个字,但是他说出了这个辩证关系。如果你不在乎借鉴,不在乎临摹,想当然地想做自己心目当中的艺术,恐怕还不行。
临摹有很多方法,比方说你不是一笔一画、亦步亦趋地照着写,依葫芦画瓢。临摹本身,还是会牵涉到很多细细小小、方方面面的所谓的方法问题。我个人花在临摹上的时间并不很多,临摹与读帖在时间分配上大致参半。年轻的时候喜好书法,但是不知道书法是何物,看不懂所谓好的书法究竟好在哪里。因为看不懂好在哪里,就无法入手,那怎么来学习它,来临摹它?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识字时,对书法完全没有概念,当时只是觉得,字要写端正,要写得好看。记得读一年级时,学校里发方格本,让我们从一二三四开始写,恰巧我看到路边的招牌上有一个“一”字,跟课本上的那个“一”是不一样的,它有点弧度,我觉得很好看,于是,我就不照课本上的那个一字写,而是照着马路招牌上的那个有弧度的写。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为什么不照着课本写?”我说:“我觉得马路上的那个‘一’比课本上的好看许多。”这是当时对书写的一种很朦胧的认识。
书法本身有一个严格标准,或者说是有一个客观的高度。问题在哪?正在于不知,因为不知,所以就无法入手。因为不懂它好坏,就不晓得要怎么来学习它,那么我们就会跟着大人的意见走,大人让怎么写柳公权我们就怎么写柳公权,大人让怎么写欧阳询我们就怎么写欧阳询。记得我最初是从写欧阳询开始的,实在写不进去,欧阳询的一笔一画是那么标准,我写不了。然后就写柳公权,我觉得这个字倒还蛮好写的。但是又有老师提出,柳公权的字格调不高,你不能这么写。所以小时候写字真是很犯难,不晓得听谁的好,心里又很着急,想赶快把字写成大家都一致认为的好字。就这么磨磨蹭蹭、来来回回、反反复复。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交友圈子的扩大,结识的高手也越来越多,情况就发生了改变,就开始一点一点明白写字是怎么一回事。当十年二十年以后,我再回过头来看欧阳询,跟我最初认识的欧阳询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学习艺术,我笼统地讲,一定要有见识,一定要听从高手的话,听从有水准老师的指点。我们小时候写字,老师就跟我们讲,开口奶一定要喝得好。小孩子可以在他长大的过程当中学习文化,学习知识,如果教他的方法不对,岂不是费了时间又没学到东西吗?但是学的人却容易当局者迷,他不认为就是这样,他觉得他的老师教得最好了。所以,我有时也会谈到这个话题,我说我的一生算是很幸运的,如果我没有碰到谢稚柳先生,如果没有碰到唐云先生,如果没有碰到关良先生,如果没有碰到沙孟海先生,也许我的眼力就会仅仅停留在马路上的那块招牌的水准上。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客观的高度,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眼界的扩大,随着看到那些原来不懂的东西变得一点一点的明朗,然后你再来思索那条自己以往走过的路,才会变得清晰起来。
从面上看,所谓临摹,是找一本字帖,照着它照式照样地写就行了,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鲍贤伦老师说临摹需要找到跟自己的性情和审美比较靠近的这一路来实施。我觉得这个想法对大多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其实临摹也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比如老师让你学习写隶书,但是隶书有好多种,哪一种隶书是和你对路的呢?你是写《曹全》还是写《张迁》呢,是写《鲜于璜》还是写《礼器》?还有即便是你手里有宋拓的好本子,你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去临,这个方法也是值得商榷的。我是到了40岁左右,才生出了这么一个想法,因为我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我在读《张迁》的时候,就发现它里面有若干同样的字,但写法却都不一样,所以,临摹到了后面的阶段,当看到了一些问题之后,我们就要想办法把这些问题单独拎出来去解决。当初我们开始学写字的时候,看到那些名碑名帖,是不敢往其他方面想的,就觉得本子里所有的字是没有一点毛病的,是无可挑剔的。但是事实是,再伟大的书法家,再著名的碑帖,都有不足的地方,这是合乎客观规律的,是合乎辩证法的。如果认清了这一点后,再来有选择地去临摹,我想最后所得到的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临摹的的确确是我们学习传统书法的一把金钥匙。清代初期的大书法家王铎,有文献记载他是隔天临摹,隔天创作。他的功力已经很深了,为什么还要临摹呢?因为他觉得古人的碑帖中还有一些现象让他揣摩不透。而哪怕是同一个问题,一个人20岁时候的看法跟他30岁时候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已经快70岁了,我看古代的碑帖也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所以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是一点一点积累的过程,是一个需要不断体验和实践的过程。如果只是纸上谈兵的话,恐怕一辈子都认识不清楚。
写字与书法不是一回事
写字这门功课跟书法这门学问,我在青年时代是分不清楚的。念中学时看到别人字写得好,尤其是老师们的字,心里就想:哎呀,书法写得这么好!因为分不清书法与写字是有区别的,而且自己心目当中的所谓好的标准,就是功夫扎实,一点一画,整整齐齐。
我曾经在不到20岁时,去拜访任政先生,恰巧见到任政先生给一个学生临摹的《兰亭序》,我瞥了一眼,一下就被吸引住了。可是这个学生要先走了,于是在这个学生出去了大概两三分钟后,我也找了一个借口,跟着就追了上去,急不可待地看了以后,好佩服啊,字居然可以写到这一步,简直是铁画银钩!我当时看到那个《兰亭》临本,甚至觉得比王羲之写得都好啊!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幼稚的认识,真觉得可笑。然而,我们都是从那种懵懂的状态走过来的。
你的识见要高,除了你原本的才气天分好以外,如果没有识见这个前提,那么只具备才气天分当然是不够的,学书法难就难在这。我们可能听到有这么个说法:“在老年大学学画画,学五年,也许就可以出来卖画了。”然而你如果学十年字,恐怕都还入不了门。因为书法原本是比较抽象的东西,它的标准往往也不一致,不具体,尤其在叙述上很难清晰分明。我在博物馆书画馆经常会碰到一些观众,他们知道我是馆里的工作人员,就会拉着我问:“老师啊,这里的有些字,我看来看去也还是觉得不好看,您给我们讲一讲它们到底好在哪里啊?”要答复这么一类的问题,恐怕要牵涉到书法美学的专门话题,恐怕需要一堂课的时间,我并不是危言耸听啊。
书法跟写字的不同在哪里呢?写字只是把它写端正,写整齐,它的作用让看的人能看清楚、谈明白,顶多再加一个赏心悦目,写字的功能到此为止了。但是书法却不同,书法不能按照自己惯有思维来看,看得顺眼的,你就觉得它是好书法,看不顺眼的,就说这个字怎么写得这么蹩脚,我也写得出来。这个你倒大可以试试看,看能不能写出来。所以在我们平时的学习当中,的确要运用一些方法,比方说比照的方法。这个比照不能是异类比照,它要同类比照,同样写工整一类的字,你把它们作为一个大类别,再从中比较,此中的高低就区别开了。谢稚柳先生有时候跟我说到书法的话题。他说自己在书法上不曾下过很大的功夫,当初写陈老莲的字,原因也是为画画所需,陈老莲这路的画要这一路的字才能配得上。谢稚柳先生的书风逐步演变,由陈老莲那一路又楷又行的书风居然一下子变到了纯粹的《古诗四帖》风格,这个变化是非常难的,当然谢稚柳先生在艺术上的才分向来是一致公认的。但是作为书法,如果你光靠眼睛看,自己不去动手的话,恐怕你无法再往前走一步,常常我们看到的是他人已经写成的完整的书法作品,譬如说谢先生写的《古诗四帖》是如何如何的好,谢先生在背后所下的功夫是别人不知的,不然不下功夫便显出高度来,那是再聪明的人也走不到这一步的。
我写的字虽然跟别人不大一样,对于“度”的把握有多好也不见得。我只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思索,一直在看一些好的作品。古人的好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怎么去学习他们也可以有许许多多的方法,但重要的是能抓住那些现象背后的本质。南朝的王僧虔曾经讲过八个字:“神采为上,形质次之。”这八个字纠正我们一些认识上的偏差,比方说我们写字往往会注意用笔的周到,间架结构的周到,那么,你对神采如何看?因为神采是无形的东西,是很难说明白的东西,所以书法创作难也正难在这里,使你难以琢磨,只能在形质、形态上去把握它。柳公权一个横划从起笔、运笔到收笔,很有特点,你就照着它一笔一划地写,可以写得很像,但是即便写像也只是“形质次之”的问题。你还要找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神采。如果你对书法一知半解,或者你学习书法的时间很短,我可以断言你说不清楚什么是神采。但你既然接触了书法,就必须得明白神采是什么。古人有很多书论说得非常深刻,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在学习书法的时候,可以多读一读古人的这方面的论述。看看明代的董其昌,他有很多话对我们很有用,有一节他说:用笔要干干净净,才能做到含蓄。听起来很矛盾,但是我们去体验一下,就会知道董其昌说得很有道理。所以我们对书法创作既不能不花功夫,但是又不能一股脑闷着头就去写,这样的话恐怕很难写好。
有一次,有人跟我辩论,字写到纸外面去了,写得行不行啊?我就跟他犯着急,我说这个写到外面去无所谓的,关键是这个字,第一,笔性好,就像唱歌,音色特别重要,这是别人学不了的,对音乐的敏感性,也是别人学不了的。第二,他写的这一路不少人都写过,但是能写到他这么风格鲜明,笔调肯定,而且气格很高的几乎没有。鲍老师的书法难在哪里,难在他取法的字源太有限,一个礼拜的粮食却要你吃一个月。帛书的字数原本不多,要创作的对象却又是无数个字,要把无数个字表现得轻轻松松、自自然然、而不露挪移和描摹的痕迹真的很难。作品要有高度,如果太通俗了,艺术的含金量肯定就有问题了。不见得大家都懂毕加索,不见得大家都懂德彪西(作曲家)啊。尖端的艺术只是一小块领域,尖端的艺术家始终也只是一小部份。人们常说的阳春白雪,也许就是此类比喻吧。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