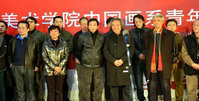秋子
一、甘肃古代书法概说
在中国书法史上,从上古时期(夏代至秦代)的后半叶到中古时期(西汉至明代)的前半叶,即从战国到北宋这长达11个世纪的时间里,甘肃始终扮演着“领舞”的角色,产生过辉煌的成就和十分重要的影响。
史前甘肃不仅是华夏文明和中国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也是汉字及书法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孕育了汉字及书法的胚胎,早于西安半坡陶文千余年、继河南舞阳龟甲刻符之后的仰韶文化晚期的秦安大地湾遗址彩陶刻划符号,不但是中国原始文化的直接标志,而且是“先文字”和“书法始祖”的有力佐证,显示了甘肃先民的伟大智慧和文化创造力。
夏商时期是书法产生、形成的滥觞时期。甘肃尽管未发现有如河南殷墟规模的甲骨卜书,但从庆阳出土的国内所见唯一一件商代玉铭《作册吾玉戈》和多件商代青铜器铭来看,也证明在甘肃留存有书法产生、形成阶段的多种踪迹。

商代玉铭《作册吾玉戈》
两周时期,甘肃书法在整个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灵台西周墓出土的一批青铜器铭(如《兮甲盘》)、天水出土的八枚西周象牙骨牌刻辞,到礼县出土的被金石考古学家马衡认为“是印刷术中活字印刷的鼻祖”和学界公认“两周时期三大籀文代表作”之一的《秦公簋》,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宣告古隶书体形成并成为新的母体的战国时秦《天水日书简》及《秦公铜鼎》《梁邑布铭》《战国蚁鼻钱铭》等,都充分说明了甘肃书法地位的显赫。

青铜器铭《兮甲盘》
秦代是上古与中古的分水岭。秦代虽然短暂,却是文字统一、书法整合的重要阶段。天水、定西和镇原等地出土的《家马鼎》、诏版、秦权等,其铭文显示的天真烂漫的线条美感和质朴生动的书法特色,说明它们在秦代以至包括先秦时,都可谓最具书法意味的作品。
甘肃书法在两汉的四百年里,以其绝对优势领先于全国。除十多件古纸墨迹堪称“中国之最”(最早的纸上书法)外,数以万计的“甘肃汉简”所反映的小篆、古隶、分书(汉隶)、草、行、楷以及各种过渡书体,创造了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书体演变和形成的无比辉煌成就;经过1800多年至今仍完好保存于成县的《西狭颂》摩崖刻石等,在中国书法史上传唱了永恒的组歌。甘肃的两汉书法“已成为古代书法的海洋”,产生了张芝、赵壹、梁鹄、仇绋、仇靖等名垂青史的书法家和书法批评家。
从魏晋到宋代这长达700年的中古史期,甘肃进一步创作了中国书法的大戏长剧,数以万计的“敦煌遗书”构成无所不有的重大板块。截至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石窟纪年壁书———420年书题于炳灵寺石窟的《崔琳题记》,以及《大代碑》《南石窟寺之碑》
《王司徒墓志》《新路颂摩崖》《哥舒翰纪功碑》《承天观碑》《王母宫颂碑》《吴挺碑》等存留于各地的大量刻石和铜器、漆器、砖铭、木刻等,足以说明甘肃书法在这一时期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同时,出现了以
“章草宗师”索靖为代表的书法家,为甘肃书法乃至中国书法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创新作用。安氏家族几代人以刻碑而名的史实也说明宋时的书法,尤其刻石书法十分兴盛。
11世纪后的金元时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吐蕃、党项、蒙古等民族政权轮番兴居,经济破坏较大,甘肃书法发展亦显迟滞,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低态势。虽也产生了像傅慎微、余阙、边武等书法家,但除了像《黑河建桥敕》《赵孟頫书赵世延家庙碑》等一些碑刻、摩崖书迹外,未能出现名显于史的书法作品。很明显,这无疑是文化南迁所造成的。
明清以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振兴发展,甘肃书法逐渐走出低谷,迎来新的春天,以《肃府本淳化阁帖》的翻刻为标志,复起了可喜势头。天水的《集王羲之书二妙石刻》《赵松雪诗碣》,岷县的《文徵明诗碑》,庆阳的《黄庭坚云亭宴集诗碑,临洮《记开煤山稿》,以及清代《吴大澂三关口碑》《大河店修路碑》《宋琬杜诗刻石题后》和省内各地数以百计的寺、观、祠、塔、楼、桥、墓、坊等重修或记功书刻,都是明清五百多年间产生的书法遗迹。此间出现了李梦阳、米万钟、胡缵宗、王了望、朱克敏等书法家,对甘肃书法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引领作用。
综上所述,可见甘肃古代书法的大致轮廓,这些从总体上构成了甘肃古代书法的“敦煌风”。

《赵松雪诗碣》

《文徵明诗碑》

《黄庭坚云亭宴集诗碑》
二、“敦煌风”的内涵及意义
首先,从时间跨度来说,“敦煌风”是一个大概念,涵盖了有史以来甘肃书法的全部历史。其次,从涉及范围来说,“敦煌风”也是一个大概念,包括整个甘肃地域留存的书法遗迹。
我曾在《敦煌风初探》一文中对“敦煌风”的含义做过梳理和归纳。
一是从大地湾、马家窑彩陶刻划符号算起,历史遗留下来的数以百计的历代摩崖碑刻都是甘肃历代书法瑰宝,当然也是“敦煌风”的本然内涵。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有于右任先生当年转赠的两千多件历代碑拓,也给“敦煌风”增添了无尽光彩。
二是五万余枚简牍和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六万多页写卷墨迹及《西狭颂》等摩崖刻石,可谓古代民间书法的海洋,以长达11个世纪的辉煌向世界宣告,甘肃古代书法在中国书坛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无疑是“敦煌风”的本然内涵。
三是《肃府本淳化阁帖》汇聚了古代书法的精华,天水清刻《集王二妙三碑》极尽书圣大风,赵孟頫的手迹向我们展示了一代大家的风范,这些又给“敦煌风”灌注了丰富的内涵。
四是甘肃历史上产生了像东汉张芝、梁鹄,西晋索靖,清代王了望、朱克敏和当代以创出“魏隶”“魏行”而独树一帜的魏振皆这六位彪炳史册的书法家,我曾将他们称之为甘肃书法史上的“六面旗帜”,他们的书法精神早已为“敦煌风”奠了基、雕了形。
五是上世纪60年代初,张邦彦先生偕同陈梦家、何乐夫、梁启超弟子冯国瑞等考古与石窟研究专家,对甘肃出土的汉简进行整理和临摹,拓开了“敦煌风”的主河道。到70年代,甘肃形成了以徐祖蕃、赵正等书家为代表的“简牍书法热”。80年代以来又兴起了“敦煌写经热”,以尹建鼎为首,1987年在日本东京举办的“敦煌写经临书展”,将“敦煌书风”的研究推向国际性。直到90年代后半期,受“展览效应”的影响,书家们的书法观念发生变化,“简牍热”和“敦煌书风热”受到不小的冲击,热度渐减。
三、“敦煌风”的精神与特征
“敦煌风”作为崛起于甘肃大地上的一面书法旗帜和象征甘肃书法风格的一个流派,就其本质而言,具有颇为深刻的精神内涵与文化特征,概言之,大致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创造精神特征。翻开甘肃书法史我们会发现,最有超现实创造意义的书法墨迹莫过于数以万计的简牍墨迹和敦煌遗书,众多的无名书家以其书法天籁精神、文化创造精神和自然表现主义精神,创造出了百花竞妍、丰富多彩的“民间书法”,如前所述,很多著名作品都属于书法史上的戛戛独造。况且,像张芝、梁鹄、索靖、王了望、朱克敏、魏振皆等,都是甘肃历史上书体、书风的创新及创造者。
二是人文科学精神特征。人文科学精神是指研究文化艺术和社会现象的自觉精神,表现在书法艺术领域,甘肃自古以来都具有这种精神。东汉的张芝正是因为他认真研究草书技法,才成为一代“草圣”;赵壹站在卫道立场审视和研究书法的文化现象,对当时产生的草书新风气横加指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书法研究精神和批评精神,可谓中国书法史上开批评先河的旗手、勇士,进而大大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西晋的卫恒《四体书势》所载“梁鹄因书得命”的故事,更是人文精神的写照;索靖不仅是“章草宗师”,而且在书法研究,尤其是草书研究上下过很大功夫,其《草书势》成为古代书论经典,对后世影响很大。如果把唐太宗李世民(《旧唐书》载祖辈为陇西人)视为甘肃人的话,则正由于他崇王尚王、研究“二王”,才有了唐代书法的鼎盛辉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二王”进行十分深刻的研究和学习。史载他在位时常与虞世南、欧阳询等研究书法,无疑是人文科学精神的一种体现。至于明清以来,由于科举考试制度的推行,像王了望、朱克敏及后来的魏振皆等人,当然无一例外是书法研究并有论有述的自觉者;更有与孙星衍共同搜访、完成《寰宇访碑记》的张澍,已成为清代学有所现、研有所著的历史人物,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人文科学精神和书法艺术精神。
三是地域文化精神特征。所谓地域文化精神,狭义地理解就是地域书法风格的塑造精神。艺术越是具有地域特色,越是有发展空间,越能产生长久的生命力。地域风格或流派就是指一个地区的艺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创作手法、创作规律和独特个性。就书法而言,几千年的书法史无不证明,无论秦汉两晋南北朝,都有地域书风相互媲美和补充,流传下来的作品也都是颇具个性和地域特色的,而且让我们耳熟能详的真正的书法大家迄今为止不过百人。“敦煌风”就体现着这种地域文化精神特征。
四、关于“敦煌风”对当今书法创作的借鉴
上面谈了很多“敦煌风”的内容,多是讲历史、讲传统,现在说说“敦煌风”对当今的书法创作的借鉴问题。
这个问题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就是“敦煌风”与当代书法创作的关系及意义何在。依我之见,“敦煌风”是甘肃书法的根,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中国书法的根。“敦煌风”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可谓博大精深,无所不含,大致除了甲骨文字和楚简、楚金文字外,几乎囊括了整个书法传统。《肃府本淳化阁帖》的刻制在宋代就为甘肃书法提供了传统经典之大要,尽管可能由于编次者王著的个人偏好未收一帧颜真卿的墨迹,但仍不失为一部皇皇巨制,仅“二王”墨迹就占一半,尤其是行草书占其大半,可见行草书在宋代已成为崇尚风气。这说明,“敦煌风”是书法传统,是传统,当然就关系重大、意义深远,此其一。其二,陈寅恪先生在半个世纪前写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指出:“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倚艺术为资用。”敦煌卷子多为宗教典籍、文献,书法又属于艺术范畴,由此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同时,不仅敦煌文献,还有汉代简牍及《西狭颂》《淳化阁帖》等诸多历代文书墨迹,本来就是书法的认同。
下面说说如何继承“敦煌风”传统来进行当今的书法创作。
1.学习和运用古代先贤的书法创造精神,指导当今的书法创作
不少书法朋友都曾以为,我提出、倡导“敦煌风”是要大家都去写敦煌卷子、写汉简,其实这是一种曲解,是一种狭隘的理解。经卷、汉简之类的墨迹固然是“敦煌风”的本然内涵,但不是全部。即使是,如果一百人都写同一帖本也会写出一百种风格的,如果写出同样的风格就不是创作,顶多算作临摹。我举个章草例子。章草这一书体是隶书的草写形式,是介于隶书和今草(就是我们常说的草书)之间的过渡书体,历史上留给我们可资借鉴的经典范本也不是很多,但汉简、写经里面都有;从书法家来说,不外乎汉章帝、史游、张芝、皇象、索靖、王羲之、赵孟頫、宋无名氏、邓文原、杨维桢、宋克、王世镗、王蘧常以及我们甘肃当代书家王创业等人;就个人主体风格而言,大致除后面的王世镗、王蘧常外,也并非他们的代表性风格,比如王羲之的《豹奴帖》就那么七行字。王羲之的主要书体是行书和草书,章草不过是他早期涉猎、学习的书体而已。《平复帖》可视为章草,但很有可能并非陆机所书,这个问题有争论,我倾向于否认陆机所书。但就章草书体而言,若仔细去看,自古至今的风格没有一个是雷同的,史游和皇象的章草《急就章》一笔一画,近乎楷书简写,不愧是一种楷书或者说隶书的“急就”写法;所谓索靖的《出师颂》与《月仪帖》也在风格上有很大不同;赵孟頫的《急就章》与史游、皇象的《急就章》也不能同视一格。由此说明,同一种书体可以写出无数种风格,其根本一点在于“创造”。所以,创造精神是“敦煌风”的根本精神。
2.学习和掌握古代先贤的书法文化精神,不断提高书法学养和修养
书法创作是一个艰苦实践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思索追求的过程,始终贯穿着一个书家的审美思想(即对书法的理解与追求)、个性修养、学识见解和技法积累的合理应用。传统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技法、形式、风格之类,还包括文学、史学、文字学、哲学、美学、艺术学,也包括数理学、物理学等等。遗憾的是,很多人迄今为止都没看见过多少真正属于“敦煌风”本然内涵的墨迹。出于书法研究的需要,我在2009年编选、出版了三卷本《敦煌写卷墨迹精选丛帖》,其中晋写本《三国志·步骘传》、北魏454年写本《大慈如来告疏》和约写于晚唐的《因明入正理论》(见图六),都是具有创新性质和体现着时代文化精神的书法墨迹,完全可以从中吸收养分,来融入自己的创作。

《因明入正理论》(晚唐)
需要说明的是,“敦煌风”的内涵博大精深,无论是书体还是风格,民间的、官方的,正统的、随意的,草率的、呆板的……无所不包。比如陇南陕南交界之地的一些碑刻,像《石门颂》、《郙阁颂》等,有多少人真正去看过?有多少人写它们?问题是,我们很多书家总喜欢追风赶浪,放着自己身边很多好东西不学,硬是去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赶浪潮,结果是浪潮没有赶上,反而丢失了自我。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对自己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3.书法创作是艺术创作,必须要有创作意识,有悟性、激情和灵感
何谓创作意识?创作,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即“创造文艺作品”。很显然,一是“创造”,二是“文艺作品”。这就是说,书法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种相对纯粹的艺术,它从性质上已属文艺作品,所以是需要具有悟性、灵感的书家去“创造”“创作”的。
敦煌写经中有很多作品都是“创新”意味的,比如隶书向楷书演变过程中的《三国志·步骘传》《十诵比丘戒本》《大慈如来告疏》以及《因明入正理论》《妙法莲华经》等等。尤其是《因明入正理论》,近两万字的篇幅几乎一气呵成,极少涂改补漏,书法十分精彩,而且与历史上的其他草书都不一样,可以说是继承和发扬当地人———张芝和索靖的书法创造精神的创新之作,体现出一种独特的“章草”风格,我将它称之为“敦煌草书”。站在书法风格史的角度看,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而且书者肯定是一位技法娴熟、造诣很深、水平极高的“书法巨擘”,否则是写不出如此精彩的作品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