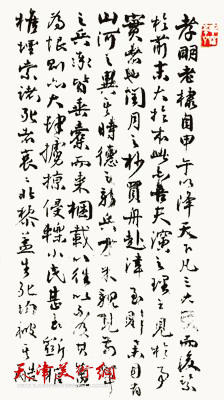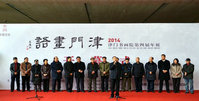20世纪30年代的书法美学成果—张荫麟书法学科论与书法美学方法论述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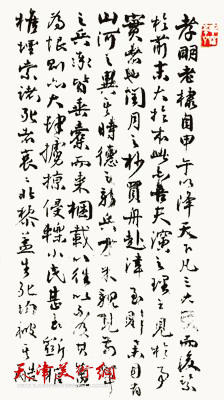
严复信札
·张荫麟书法学科论与书法美学方法论述评(下)
毛万宝
今人刘景山指出:“作为强调‘和谐’的中国文化,其思维方式趋于寻求对立面的统一,长于综合而短于分析。在天与人、理与气、心与物、体与用、文与质诸组范畴的两两关系上,中国哲学虽然也讲对立面的斗争,但总的倾向是不主张强为割裂,而习惯于融会贯通地加以把握,寻求一种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三个基本命题……这三个命题都带有笼统、直观把握事物的无限涵容性色彩,均属素朴的整体观念。这种涵盖天地、兼容并包的运思方法,使得中国古代哲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描绘世界‘有机整体’的图景上,而不太注意细节,表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整体’或‘有机’的思维方式。”受此影响,中国传统学术中的文史哲从未分过家,谈论书法的有关文字被笼统地称为书学,像孙过庭《书谱》、张怀瓘《书断》、项穆《书法雅言》、刘熙载《书概》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等经典书论,既谈书史源流、创作技法,亦谈批评鉴赏、审美特征,还兼及书家传略等,很难强行将它们划入“史学”“美学”或“批评学”等具体学科类别。
但进入20世纪之后,以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胡适等人为代表的先驱人物,掀起了学习西方文化、用西方分析归纳的逻辑思维取代笼统模糊的整体思维的热潮,很快便形成风气,特别是年轻一代学子,不再恪守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而是把擅长科学实证且带有几分机械的西方分析思维作为自己的思维方式。正因为置身如此文化背景下,加之赴美留学期间(1929年秋至1933年夏)对数理逻辑课程的迷恋,张荫麟(1905-1942,任过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我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撰写(而且是赴美留学期间撰写)《中国书艺批评学序言》(署“素痴”笔名连载于《大公报·文学副刊》1931年4月20日、27日和5月4日、11日)时,便非常自然地提出了他的“书法学科论”。
张氏的“书法学科论”首先是关于书法美学的,其次是关于书法批评学的,着眼点既包括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也包括相应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宗旨等。他认为:
是故,吾人有待解决之问题如下:
(一)我国书艺与众文化所公认之诸艺术,有无根本相类之点,使书艺得成为一种艺术?精析言之,此问题实包含两问题:(甲)书艺与诸艺术有无相类之点?(乙)此共同之点是否即艺术之要素?
(二)艺术之要素,苟为书艺所具,如何在书艺中实现?
(三)书艺与其他艺术又有何根本差异之点,使得成为一特殊艺术?换言之,书艺就其为艺术而论,有何特别之优长,有何特别之限制?何者构成书艺之“型类”?
(四)书艺之派别有何美学的意义?
此诸问题之解答可以构成美学之一新支,吾人可名之曰“中国书艺之美学”。以此学之原理为基础,可以建设一“书艺批评学”,其任务在探求书艺美恶之标准,并阐明此标准之应用,故题曰“中国书艺批评学序言”云。
除书法美学、书法批评学之外,张氏的“书法学科论”还道及书法史学与书法创作学的构建,并且标明了它们的特定学科位置———从属于“国学”,以及它们的现实效应与历史意义———使“中国书艺”将因此“始得昌明也”。张氏设想道:
书艺为一种具有特长之艺术,与其他艺术等有同等价值。
唯然,则书艺应与其他艺术受吾人同等之注意,其过去之成绩及技术之传说,应在整理研究之列。惜乎今尚无从事于此者,倘将来有人为之,则“国学”内可辟一新领域,其内容大略如下:
(一)书艺中有价值作品按个人、按时代或按派别之搜集、影印。
(二)作品真伪之鉴别及年代未详或可疑者之考定。
(三)书家评传之撰作,特别注意其书艺上之修养、作品之年历,及其技术之进展。
(四)诸体及诸派之比较研究,辨其异,溯其源流,著其得失。
(五)过去关于书艺之理论及实诀之汇集与研究。
此等研究之综合,则可成《中国书艺史》及《中国书艺之法程》二书。必待此二书之成,而后中国书艺始得昌明也。
固然,在张氏笔下,书法学科的构想尚是初步的、简略的,但它出现于上世纪30年代初却显得异常珍贵。不要说发表之际如空谷足音,就是40多年后的80年代初仍然没有响应者。直到1985年,我们才在《书法家》杂志第1期上读到周俊杰撰写的《书法学刍议》,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书法学科构建的设想;其后,随着陈振濂主编《书法学》的出版,连续三届“全国书法学暨书法发展战略研讨会”的召开,书学界关于书法学科的认识又进一步趋于成熟。而其中的书法美学、书法史学、书法教育学、书法比较学、书法人才学、书法创作学、书法鉴赏学、书法批评学与书法文献学等,都有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果。今天,我们为这些成果欢欣鼓舞的时候,切不可忘记30年代初张荫麟在书法学科构建上的筚路蓝缕之功。
19世纪以前,我国传统书学虽然没有“书法美学”之谓,但对“书艺之特质”的探讨却从未停止过。从东汉蔡邕的“书者散也”,到清代康有为的“盖书形学也”,历代都留下了若干关于“书艺之特质”的言论。这些言论基本上都是古代书论家们感悟的结果,未经论证便直接道出,显得言简而意赅。但进入20世纪以后,受西方分析思维之影响,人们从事学术研究都得遵循由大前提到小前提再到结论的逻辑规定,不能只有结论,还要有相关论据以及尽可能周密细致的论证过程。张荫麟的书法美学研究采用的正是这种西方式的方法。他在提出书法美学的学科设想之后,告诉我们:“欲论书艺之特质,宜先明何为审美之经验。”
于是,我们看到,张荫麟接下来就将他的笔触“伸”向西方美学中的康德美学和鲍桑葵美学。他几乎用了近三千字的篇幅,不厌其烦地介绍了康德美学中审美无功利的基本观念和鲍桑葵美学中的情感“觉相”论,尔后指出:“寓此类情感之有结构的觉相谓之美,此类觉相所置之物,其成于人造者谓之艺术品。有结构的觉相书艺作品之所呈也。正的情感为觉相规律所支配者,吾人观赏书艺作品时所恒经验者也。故吾人可下一结论曰:中国书艺为一种艺术”,“优美与壮美,书艺中兼具之”,书法情感源于书法创造(即有什么样的觉相或形态,便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感,创造情感与观赏情感相同。绝非如曾国藩所说书家先有某种情感在胸,然后用书法加以表现)。
张荫麟之所以如此“兜圈子”,先谈有关美学观念,后及“书艺之特质”,无非因为他持有这样一种想法:书法美学是“美学之一新支”,如果不把有关美学问题说清楚,那就无法把“书艺之特质”弄明白。应该说,这样的想法完全正确,特别在20世纪初叶人们对西方美学思想还不太熟悉的情况下。
张荫麟探讨“书艺之特质”,除站在西方美学高度予以宏观把握外,还调动了另一种方法,这就是通过艺术分类加以比较认定的方法:“艺术之分类,尚无满意之方法,大抵顾此失彼,赅甲则遗乙。然试就各种曾经提出之分类法,而观书艺之当入何类,则可以明书艺之特质及其在诸艺术中之位置焉。”
这部分篇幅张荫麟拉得更长,大约有五千言之多。通过多方面的分类比较,他非常明确地告诉读者:
其一,书法相同于绘画、雕刻、建筑、跳舞等,是一种视觉艺术。
其二,书法“各部分同时存在”,一如绘画、雕刻、建筑等,属于空间艺术。
其三,书法与绘画所用工具相同(或相近),都可归入“绘写艺术”类,而不同于诗歌、小说等“语言艺术”类。
其四,书法“其美仅存于符号之形式,与符号之意义无关。构成书艺之美者,乃笔墨之光泽、式样、位置,无须诉于任何意义”,同音乐、建筑一道,属于鲍桑葵所谓“直达的艺术”类。
其五,书法不同于绘画与小说,绘画与小说属“纯粹艺术”,“其本质并无适合非艺术的目的之需要”。书法是一种“饰用艺术”,与建筑同类,“此等艺术之工具其造始时原非满足艺术之欲望”,“书契之肇始原以代结绳而为记事之符号而已。当文字开始受美观化时,其形式大体上已受实用之目的及盲目之机会所断定。其后字形虽屡有变迁,然其主要之‘导引原理’似仍为实用的与习惯的,而非艺术的”。
结论则是:“我国向以书画并称,似书艺在一切艺术中与绘画为最近似者,此就材料上言则诚然:二者同为视觉的、空间的艺术,其近一也;同用形与线为材料,其近二也。然统观其一切属性,书艺在诸艺术中实与建筑为最近:同为空间艺术一也,同为直达艺术二也,同为饰用艺术三也。然就最后一点而论,书艺与建筑有重大之差别:建筑之形式与其实用之目的为相关切的,户牖之位置、堂室之广袤、墙壁之高低,非可任意而定者也;唯书艺则不然,同一言也以篆书可、以隶书可、以草书可、以楷书可、以注音字母拼写可、以罗马字母拼写可,即另发明一种书法亦无不可。唯其形式与实用目的间之不能有密切关系也,故不能不以一种盲目的、武断的习惯为准。习惯一成则不易改变,其结果创作之自由少。建筑之形式与其实用之目的可有密切之关系,而此目的对于形式之限制又非紧严,故其中创作之自由多。”
在对20世纪书法美学进行述评时,笔者曾提出这么一种比较宏观的看法,即20世纪内,人们关于书法艺术性质的探讨大致经历了三大阶段(或三大层次):第一阶段是着力探讨书法的艺术共性,解决书法进入艺术家族的资格问题,最终目的在于让书法“入籍”,时间大约从20年代到60年代;第二阶段开始于70年代末,延宕到90年代初,在最终目的上表现为“别类”,探讨重点已转向书法与哪门艺术相同或相近,属于何种类型的艺术,比如说是“形象艺术”还是“抽象艺术”,是“表现艺术”还是“造型艺术”,是“抒情艺术”还是“写意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的艺术”还是“哲学艺术”与“象征型艺术”等;最后一个阶段可称之为“体性”,它要求得到的定义或结论必须体现书法这门艺术的个性化特征,绝不可用来解说书法以外的其他任何一门艺术,也就是为书法所独有,像章祖安的“虚象”说与金学智的“多质”说便如此。以我们这里所说阶段论来反观一下张荫麟的分类比较,能否认定张氏具有超前性,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做了大家普遍到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才做的“别类”性质观探讨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张氏的分类(即“观书艺之当入何类”),只是一种手段,就目的言,他无非想通过多样化的分类来观照一下“书艺之特质”、标明一下“书艺在诸艺术中之位置”而已。而且,张氏所云“书艺之特质”亦非我们上述所说“体性”阶段要探讨的书法之“个性化”本质,相反,它着力探讨的却是书法与其他各门艺术间的“共性化”特征———要么与绘画同类,要么与舞蹈、雕刻同类,要么与建筑、音乐同类,唯一没有同类过的仅“语言艺术”一项而已。所以,我们坚持认为,在这点上张氏并没有超前意识,他的书法性质探讨一如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等人,依然处于我们上述所说的“第一阶段”,在为书法做着“入籍”的努力:书法具有与绘画、音乐、雕刻、建筑、舞蹈相同的艺术属性和审美特征,是一门当之无愧的艺术(用我们以上所引张氏本人的话来说,就是为了回答“我国书艺与众文化所公认之诸艺术,有无根本相类之点,使书艺得成为一种艺术”的问题)。(上)
·张荫麟书法学科论与书法美学方法论述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