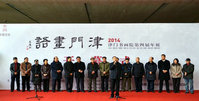黄建华 江村即事
曹工化
看黄建华的山水画近作,明显见出与以往的不同。这不同,并不在于视觉图式上的转变——或者可以准确一点地说,视觉图式的转变并不是最重要的,也可以说,他视觉图式的转变对我来说并不是最值得关注的,当然从视觉层面上看,这种转变也确实显而易见。
我关注的是,在黄建华的山水画近作中见出的他对于笔墨的态度。在这之前——也是黄建华一直以来对于笔墨的态度是,竭尽全力地进入、把握与彰显,并且时时刻刻牢牢“记住”,一刻也不敢“忘记”。尽管他自己并不满意自己的“笔墨”——因为他总是把自己放在中国绘画史大师的笔墨坐标之中,但这种努力在他的画中是日见其成。
就在“这个”时候——也只能在“这个”时候,黄建华突然——对于我来说是“突然”而对于他来说可能是“必然”地“背道而驰”,或者说“逆向行驶”——这是一种疑似“违章”的“冒险”——黄建华正在竭尽全力地“忘记”笔墨。这种努力在他的近作中也是日见其成。
黄建华为什么要“这样”,这让我又重新思考中国画中的“笔墨”问题——这个“陈词滥调”但又“日日新”的问题。
我想,我们在很多时候是“忘记”了应该“记住”的东西。在中国画的文化传统中,“笔墨”是居于其核心理念体系之中的。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把他作为最高评估标准——当然这是指传统的中国文人画。既然是“文人画”,那么这种标准当然也是一种“文化”标准——但它里面的“技术”指向也是十分明显。这都是我们——努力把自己炼成“文人画家”的人时刻牢记在心的。
论“笔墨”,中国山水画的巅峰人物——荆浩的《笔法论》应该是当之无愧的绝对经典。就是在这里,荆浩告诉我们:“画有六要:一曰气,二曰韵,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笔,六曰墨。”也就是在这里,荆浩告诉我们在中国画文化中“似”与“真”的问题:“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这就是“不求形似”的前置“解决方案”。当苏东坡提出这个中国文人画核心理念体系中的又一个评估标准并且被之后的文人画家狂热追捧的时候,我们会问,“不求形似”那“求”什么。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把它误读成“求形不似”。其实,在苏东坡之前,荆浩就说,求其“真”。后来吴昌硕说自己“苦铁画气不画形”也就是求其“真”的意思。而黄建华的画中,“气”从来就是他“求”的——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如何求其“真”,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哪里。荆浩也在《笔法论》中为我们准备好了——那就是“忘记”笔墨,他说:“忘笔墨而有真景。”
“真景”——我想,按照荆浩的意思,非“笔墨”也非“景”,而是“景”之“笔墨”亦“笔墨”之“景”,是“笔墨”融于“景”,“景”融于“笔墨”,是“景”与“笔墨”合一也。“景”之“真”当于“笔墨”取之,唯“笔墨”取“景”之“真”者。而取得“真境”又必须是在“忘记”笔墨之时。唯“忘记”笔墨才能得到“真境”。“笔墨”的评估标准,当在是否能得其“真”。这是超越“笔墨”(自身独立的形式美)的“笔墨”,这是被遗忘的笔墨评估标准,或者它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这是被忘记的“忘记”。这是我们应当记住的“忘记”。
没有笔墨得不到“真境”,有笔墨也得不到“真境”,唯有有笔墨之后再“忘记”笔墨,才能得“真境”。没有笔墨的山水徒具其“形”,有笔墨的山水徒具“笔墨”,而有笔墨而“忘记”笔墨的山水才是“真境”。这倒又合了一个陈词滥调——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再到“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是一种人生的境界,这对于山水画来说,就是走向“真境”的路径。
在一个“迷信”变化“迷信”创新的时代,我们往往“忘记”了有些也许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那些“不变”的东西,可能也是永恒的东西。“易”,我们往往记住了“变易”而忘记了“不易”。只有“不易”的东西才是“必须”的,因为只有“不易”的才是“根本”的,才是“这”成其为“这”的依据——这是它的“身份证”。中国画——中国文人画,之所以成其为“中国画”就是有其“不易”在。“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荆浩,这位生活在五代的画家,在相距1000多年之前说的这些话,对于1000多年之后的我们——今天的中国画与中国画家来说是不是仍然有效。我想,可能有很多人——也可能是绝对多数画家都不相信。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相信。我想,黄建华可能也相信。不然,他不会如此义无反顾,“虽千万人吾往矣。”
“笔墨”对于中国画与中国画家来说,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但这也只能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