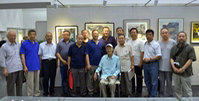-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王耀庭:顾恺之《女史箴图卷》画外的几个问题

大英博物馆藏东晋顾恺之(传)《女史箴图》(局部)
今日所见大英博物馆藏顾恺之《女史箴图卷》,已是经过历代辗转流传,画幅上多出了相关的印记,改变了装裱。本文探讨的问题不是绘画本身的风格,而是原画之外,因流传所增加诸事件。当然无关于画幅书幅本题的质量及真赝,但是既然它存在于画卷上,如能厘正这些问题,未尝也不是对一幅长远流传的名迹增多一份了解。
唐内府收藏之说
张华(232-300)的《女史箴》完成后,何时出现《女史箴图》呢?梁朝(502-533)就有《女史箴图》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女史箴图》被认为唐代皇室收藏,根据的是幅后“弘文之印”印。对照张彦远(9世纪后半期)《历代名画记》:“又有‘弘文之印’,恐是东观旧印印书者,其印至小。”以往被误认为唐代翰林院“弘文馆”的收藏。然而,从现存同型诸多的印章,出现在宋朝的书画上,就有多例。如上海博物馆藏传为王献之(344-386)实为米芾(1051-1107)或宋人临写之《中秋帖》,就有相同的“弘文之印”。上海博物馆藏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卷》幅最后下钤有“弘文之印”似又与《女史箴图卷》不同。此卷传为宋人所作。“弘文之印”出现最多当是《宝晋斋法帖》[咸淳四年(1265)曹之格摹刻本]第三卷中,王羲之《裹鲊帖》等法帖。这几帖已非全米芾所原藏,如《裹鲊帖》原本出自米芾好友薛绍彭之刻石。这两件的“弘文之印”,又是另一印了。(“文”字之交叉为近圆弧形。)这又是启人疑窦了。
又唐杜牧《书张好好诗卷》卷前右上方亦有“弘文之印”,惟此印“印”字笔画转折是方。(此点,于2001年6月大英博物馆《女史箴图卷》讨论会时,杨新先生亦说明是与《女史箴图卷》上不同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之南宋《朱熹易系辞》,最后一页亦有相同之“弘文之印”。这两印显然又不一了。周密《志雅堂杂钞》记:“(癸巳)三月二十八日,至困学斋观郝清臣字清甫所留……《孙过庭草书千文》用五色纸,……中有唐弘文馆印。……。”惜不知有否存世,能一见以为比对。
又以张彦远原文:“弘文之印……其印至小”所指来比较,此印恐不足相信为唐朝收藏印。实际上今日所见法帖上的“贞观”连珠印、“开元”印,可以说是小印。这“弘文之印”约二点五厘米见方,何能说是“至小”?可见此印之不可遽信为唐代印。“弘文”是个相当平凡的名词,与其说是唐代弘文馆,不如说是宋代或宋以后某个不知名的收藏者印章,乃至于是出于作伪者之手。
宋代收藏印的探讨
《女史箴图卷》十一世纪顷,见米芾所著《画史》。再记录于宋徽宗(1082-1135)《宣和画谱》。1966年山西出土的北魏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列女古贤图》(484),有类似的图画,可见古画本应有相当多的摹本出现。所以,米芾《画史》所记,是否为“宣和”(宋徽宗)所藏?如果以“弘文之印”出于喜欢作伪的米芾之手,那今日大英博物馆所藏的这一卷画就是了。
1. 宣和诸印的问题
“宣和”藏品的钤印和装潢格式,一般所见是有定式的,况且今天经“宣和”收藏的名品尚多,足供比较。《女史箴图卷》的装裱看来,最主要的是前隔水黄绫;中间是画本幅;后隔水两幅黄绫(绢)拼成;再往后是《金章宗书女史箴文》。又往后是拖尾清高宗乾隆的跋及邹一桂的《松柏图》了。(实际上,今日大英博物馆已将《女史箴图卷》割裂,裱褙成平板式上下两段了:一、引首前隔水及后段金章宗女史箴文、乾隆跋。二、《女史箴图卷》本幅。余乾隆朝仿制缂丝包首、《邹一桂松柏图》,则又另成一板。)
本卷只从钤印所见,被认为是宋徽宗(1082-1135)所藏者:前隔水黄绫上,有“政和”(在骑缝书“卷字第柒拾号”下方);卷前则为“御书”(瓢印)、“宣龢”(卷中第二“睿思东合”印右旁上有一“宣和”印,已相当模糊);卷后“宣和”,后隔水上则钤有“内府图书之印”九迭文大印。
当然,目前《女史箴图卷》已失去第一、第二两段,那是否当年宋徽宗“宣和”所藏就是如此状况,也无法得知了?《女史箴图卷》所见,与一般“宣和装”上“宣和七玺”的钤盖,不但不完全,位置也显然与其他名卷不一样。“宣和七玺”除了钤盖在拖尾“宋白纸”上的“内府图书之印”大印,其余都是作为骑缝印,(“黄绢”上大半与本幅小半)古书画屡经装裱,难免不能完全保存原样,古书画也不一定有完全一样的空间,能供同一收藏者作同一形式的钤盖收藏印。从所知的宋徽宗收藏名品,也未必是一致的,就可了解不能以绝对的形式来要求。
以个人曾目见之《晋王羲之远宦帖》与《行穰帖》、《唐孙过庭书谱》为准,后两件并著录于《宣和书谱》。这三件前后隔水都是黄绢本,肉眼所见,这些宋徽宗的印记印泥都是“水调朱印”,三者的钤印位置都是一致的。
《女史箴图卷》后隔水是两幅拼接,第二幅上有“内府图书之印”九迭文大印一方,此印台北与故宫藏《宋易元吉猴猫图》上之印,却是相符合的。台北故宫藏《如来说法图》亦有此印(按本画边角存有宣和装之诸印半印,疑伪,然可见为宣和旧藏)。
再从印泥的差异比较,“内府图书之印”印泥晕散的现象至为明显,相对地,《女史箴图卷》卷幅内三印:“宣龢”(连珠)、“宣和”、“御书”,印泥少有晕开,且笔画显得较细硬。对于同一套收藏印,钤于同一幅画上,竟有如此差别,那该如何作想?
更有趣的是台北故宫藏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幅前隔水是花绫,宣和钤印形制也与前举三幅有黄绢隔水者不相符。惟将此花绫隔水上之“宣龢”连珠印与《女史箴图卷》上之“宣龢”连珠印比对,却又是相符合的。又两幅中之“宣和”也可视为同一印。至于同为前隔水的“政和”,也可认为同一印。“和”之“禾”最后一捺,应是印泥堵塞所成,这又见之于《唐吴彩鸾书唐韵》上倒钤的“政和”印。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从宋徽宗藏书法的《宣和书谱》查证,《平安何如奉橘帖》是否为宣和内库所藏?按现在所见《奉橘帖》是在最后,而签标只写《晋王羲之奉橘帖》,就殊堪玩味了。查《宣和书谱》只有《平安帖》的名目,如果当时三卷(帖)已在一起,那此卷应以第一卷为题签名,或者三卷之名同时罗列,方是合理。这些不合常理的疑点,令人想起此卷必定不是宣和所藏原状。再看题签瘦金书的风格,与《远宦帖》的纵横自如,飘飘然如闻有风声,则《晋王羲之奉橘帖》诸字的短截瘦硬,应是别出另一手了。(意以为近于《李白上阳台赋》上的瘦金书。)
或许可以如此想,《平安帖》上“宣和”诸印是后来所妄加。那《女史箴图卷》也可做如是观了。
2. 睿思东合印
《女史箴图卷》上有“睿思东合”大印八方(明可见者六方,另一为乾隆“八征耄念之宝”所迭钤;一在卷最后,已模糊)。对于同一卷画上钤盖大印八方,即每一段文字,有一大印。(第六印上缘未在幅内)足以援引比对者有上海博物馆藏唐孙位《七贤图》(前名《高逸图》),此卷画上亦有三方“睿思东合”大印,分钤于四位人物之间隔上,本幅大印上缘也是略被切去。(此卷有宣和题签及诸印)
“睿思东合”大印,该属于北宋徽宗,或是南宋高宗(1107-1187)呢?所见南宋皇室诸印,如“内府书印”(钤于《米芾草书四帖》,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如“睿思殿印”(钤于《米芾苕溪诗帖》,北京故宫藏)、“缉熙殿宝”(钤于《黄庭坚七言诗》,台北故宫藏)都是作为“骑缝印”,而且是纸本。按绢本之长度远超于纸本,接缝是少的。唯一的解释,“睿思东合”大印就如前面所述,它原来应该是每段一印才能解释得通的。画上此大印殊不完整,就存世诸印做一比较。“睿思东合”大印见于名迹上者,如北京故宫藏《唐韩滉五牛图》、《黄筌写生卷》、《唐韩滉文苑图》,台北故宫《宋黄居寀山鹧棘雀》、《唐韩乾牧马图》。《宋黄居寀山鹧棘雀》上的“睿思东合”大印其边宽是7.4厘米,应该与《女史箴图卷》上的“睿思东合”是符合的。《宋黄居寀山鹧棘雀》不但见于《宣和画谱》,画上也是典型的“宣和装”。且此幅也未见有宋高宗收藏印,因此,将“睿思东阁”大印作为宋徽宗的收藏印章,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此外,《唐韩滉五牛图》也见之于《宣和画谱》。至若《唐韩乾牧马图》无论是视为宋徽宗本人作品,或当时画院画家所摹,这都足以证明《女史箴图卷》是北宋时已存在。“睿思殿”成立于北宋熙宁八年(1075),著名的《王羲之定武兰序》原镌刻石,当“薛绍彭(11世纪后半)既易定武兰亭石归于家,政和(1111-1117)中佑陵(宋徽宗)取入禁中,龛至睿思东合”。睿思东合作为收藏书法的场所,是可以了解的。另宋徽宗时尝于“睿思东合”造香。
3.贤志堂印与吴皇后
本卷中重要的南宋宫廷拥有者是宋高宗吴皇后(1115-1197),她的收藏印:“贤志堂印”。此印之所以被认为是吴皇后,据《宋史》:“宪圣慈烈吴皇后,开封人。……后益博习书史,又善翰墨……尝绘《古列女图》,置座右为鉴,又取《诗序》之义,匾其堂曰‘贤志’。”《古列女图》与张华《女史箴》本是一体。《女史箴》源于西汉末刘向(77-6BC)的《列女传》,不仅题材相承,内容也有联系的。刘向以为王教由内而外,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的法则,共列传八篇,以劝诫天子。此时,赵后姐妹(活动于公元前一世纪)嬖宠,《列女传》就是用以为劝诫。《列女传》成书不久,东汉梁皇后(106-150),常以《列女传》图画置于左右,以自鉴戒。若此,则吴皇后收藏此《女史箴图卷》是不唐突的。
单纯地从画幅上所见印记的先后收藏史,何以从宋宫流向金朝呢?宫廷收藏的流出应该是以赏赐臣下或作为邦交礼物。吴皇后的侄儿吴琚(活动于1173-1202)也是名书法家,就曾多次出使金国。“金人嘉其信义,……言南使中唯琚言为信。”这一卷是否由此管道送出作为外交的礼仪,出为金国所有?这只是做一种背景性的猜测。问题是这样的背景也有未必正确的。
金章宗与本卷的问题
关于此卷之归于金内府或章宗(1168-1208),从《女史箴图卷》本卷上来说,收藏印最为清楚处是钤盖在本幅后方的“广仁殿”印,及后隔水两幅拼接上做为骑缝印的“群玉中秘”印,还有卷后的《金章宗书女史箴文》。
1.金章宗的收藏与书迹
金朝内府的书画收藏,当然是在靖康之乱(1126),金人攻下汴京后,直接得自于宋皇室为最大宗。接收徽宗收藏,说得更清楚的是:徽宗平时爱好珍宝,但有关单位并不知道存放在何处。这时,在金军营中的内侍梁平等人为了讨好金人,便指出存放的地点。金军便向宋廷索取。于是,徽宗所收藏的珍珠、水晶、帘绣、珠翠、犀玉、古书、珍画等珍宝,都络绎不绝地被搬运去给金人。此外,金人又取去皇帝的白玉之宝十四枚,青玉之宝二枚(其中一枚即秦玺),金宝九枚,银印一枚,以及皇后、皇太子等印宝。
金章宗的收藏到底有多少?明昌三年(1192)王庭筠(1151-1202)“召奉为应奉翰林文字,命与秘书郎张汝方品第法书名画,遂分入品者为五百五十卷”。
今日所存于卷后的金章宗书写于后段的《女史箴文》,此中是否别有用心?按:金章宗时有李师儿(元妃)(活动于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出身微贱而见宠,兄弟皆贵,朝臣附之以得宰相,参以立卫王谋,不久被卫王(十三世纪)赐死。”以妃妾干政,这样的个案,几乎是晋朝《女史箴》的撰写人张华(232-300)用意的翻版。晋惠帝(290-306在位)即位以后,贾后(256-300)专政,国家乱象已显。《晋书:张华传》称:“(张华)尽忠匡扶,弥缝补阙。”当时已有正直的忠臣提出废后的主张,《女史箴》写作的主要目的,正是讽谏贾后。
金章宗汉化及与宋室的关系是相当深远的。
金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章宗凡嗜好书札,悉效宣和,字画尤为逼真。金国之典章文物惟明昌为盛。
前一段姻缘固然是错误的,但是宋徽宗有好几个女儿与女真皇族通婚则是事实,生活中也颇和徽宗有关:
承安三年(时宋庆元四年;1198)春,国主幸蓬莱院,内宴内侍都知江渊与焉。时所陈玉器及诸玩好盈前,视其篆识,多南宋、宣和物,恻然动色。
宸妃解之曰,作者未必用,用者未必作,南帝但作以为陛下用耳。……是冬,赏菊于东明园,主登其阁,见屏间画宣和艮岳。问内侍余琬,曰:“此底甚处。”琬曰:“赵家宣和帝,运东南花石筑艮岳,致亡国败家。先帝命图之。以为戒。”宸妃怒曰:“宣和之亡,不缘此事,乃是用童贯、梁师成耳。盖讥琬也。”
徽宗书法传世既多,复有题识,故容易辨识,而传世之金章宗书迹,就个人所见,并无款识,这难免要费一番考虑了。《宋徽宗捣练图》上题签为:“天水摹张萱捣练图”。拖尾有张绅跋语:
右宣和临张萱(八世纪中叶)捣练图,明昌以郡望题签款之七玺,盖亦爱之深,乃知嫫母之姿,亦有效其颦者。何邪?齐郡张绅。
根据张绅(14世纪下半)提出“郡望”的说法,此签之瘦金体书法出于金章宗是为人们所接受的。同样的见之于辽宁博物馆藏《虢国夫人游春图》题签也是以“郡望”:“天水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问题在于章宗学徽宗,其间的差异如何呢?作者所见分辨的说法是:“图”字的写法,囗内小口,徽宗用“口”;章宗用“△”。验之于上两件确实是如此。再以《五代南唐赵乾江行初雪》前隔水上的乾隆题识“赵乾江行初雪图”,根据安仪周《墨缘汇观录》:“前锦黄绫隔水,有御府瓢印,金章宗墨题‘赵乾江行初雪图’。”今所见乾隆之御题“图”字,应是仿自金章宗瘦金书,是以“图”字也作“△”。又台北故宫藏《唐周昉蛮夷职贡图》有金章宗“明昌”印,其题识也做“△”。对于金章宗的题识,台北故宫藏《郭忠恕雪霁江行图》图上“雪霁江行图郭忠恕真迹”,也被研究者认为是出自金章宗。
2.广仁殿印
本幅后段有“广仁殿”一印。“广仁殿”在上京,金章宗时已有在此殿活动的记录。“广仁殿”印是否可确定为真?此印尚出现在《唐吴彩鸾唐韵》及《王献之中秋帖》。值得注意的是将上述三件做一收藏印之比较。“宣和”诸印多是伪加,尤其是“宣龢”连珠印这三件均有钤盖,也均是伪加。“绍兴”诸印也多疑伪。那是否“广仁殿”印也是这一套假印之一?就个人所见,出现于台北故宫藏题名《宋张择端画春山图》的“广仁殿”印,这一幅是明代的伪本,幅上的“广仁殿”印,就相同于《女史箴图倦》上所钤盖者,自是伪印。“广仁殿”在这样的状况下,我想目前应该说此印为伪。
“广仁殿”印之外,画幅本身并不出现其他与金朝(或章宗)相关的收藏印。再按《金史》“广仁殿”为凉殿之东庑南殿,建于皇统二年(1142),年代与宋高宗吴后(1115-1197)时期是可以交会的。即使“广仁殿”一印为真,这也令人起疑?在如此短的期间能转换为金朝(或章宗)收藏吗?如果“宣和”、“绍兴”诸印皆伪,只有“睿思东阁”印为正确,那可解释为北宋徽宗收藏,因“靖康之难”直接为金朝所北载而入金内府。然而,如此一来,那作为南宋高宗吴皇后收藏印,又如何解释呢?
3.群玉中秘印
其次,出现在后隔水的“群玉中秘”印,此印一向被认为是金章宗“明昌七玺”之一。“群玉中秘”一印的钤盖位置,目前被认为周全的出现七玺者:台北故宫藏《五代南唐赵幹江行初雪》,及波士顿藏《宋徽宗捣练图》。这两件无论装裱及七玺钤盖的位置是一致的。比对之下,《女史箴图卷》隔水上“群玉中秘”与这两件上的“群玉中秘”,略有小处差别。同样,台北故宫藏《唐人十二月朋友相闻书》的“群玉中秘”,“示”字旁也是“一横”而已。比对之下,可以说:台北故宫藏《五代南唐赵幹江行初雪》、《唐人十二月有朋相闻书》及波士顿藏《宋徽宗捣练图》,明昌七玺的印是一致的。[《唐人十二月朋友相闻书》目前虽为册页装,且缺最前之一、二月及五月,但就现存“御府宝绘”、“内殿珍玩”、“群玉中秘”、“明昌御览”之钤印位置是一致的。更相符的是“群玉中秘”骑缝印“群玉”(右方)都是龟甲纹绫。]
进一步令人注意的是台北故宫藏《唐怀素自叙帖》及《晋王羲之远宦帖》。这两件上的“群玉中秘”,“秘”字作“示”字旁作“二横”,又是另一方“群玉中秘”印了。
按一向被认为最标准的“明昌七玺”钤印在《南唐赵幹江行初雪》及《宋徽宗捣练图》,“群玉中秘”的位置应在“后隔水”骑缝的中央,而《女史箴图卷》上同样地作为骑缝印却是在上方了。这种不同于“明昌七玺”制式钤印的情形,出现在另外一件名迹:台北故宫藏《唐怀素自叙帖》。“群玉中秘”印也是钤盖在“前隔水”裱绫上方。然而状况也未必完全是如此。“群玉中秘”出现在《晋王羲之远宦帖》,且是“后隔水”骑缝中央了。这该如何解释呢?到底哪一方“群玉中秘”印是正确的?事实上,再就另一方大印“明昌御览”来比较,也出现明显的差异。如《远宦帖》上的“明昌御览”就与《南唐赵幹江行初雪》等不同。简单地说,“秘”字“示”旁,作“一横”与“二横”,所配的各有一套。这真令人困惑,如情势上一定要做唯一选择,那理智上的选择还是以完整整套出现,“示”字旁作“不”者为准。由于“群玉中秘”印,应是后隔水与拖尾的骑缝印。“群玉中秘”印,更疑为伪。《女史箴图卷》的图与书法,原本非一卷,下文将有论述。历经典藏的过程,有毁损、割裂,重组,所以“群玉中秘”印从何而来,位置更动,当然成谜。现存成前后一卷。
《女史箴图》与女史箴书法
抛开“群玉中秘”印的真伪不一,更必须面对这个“群玉中秘”印,是否与前段《女史箴图》相关联?还是与后段的《女史箴文》有关?更可以考虑,由于钤印相对位置与常见有异,它或许是完全由外来另一件不相关的书画上所移配者?单从图与文的收藏印记,除了项元汴(1529-1590)在书幅前隔水的骑缝印外,画幅与书幅两边的收藏人几乎无相重复者。《女史箴文》上,只有“张镠”(约17世纪)、“大明安国鉴定真迹”、“大明锡山桂坡安国民太氏书画印”。以项元汴之喜爱钤盖收藏印,竟然画幅与书幅如此不平均。相对地,安国(1481-1534)的收藏印,也没有在《女史箴图》上出现,《女史箴图》上众多的明末清初收藏者,也没有在后段的《女史箴文》上重复出现。这也间接可以说明这前后图与文是分开的。
今日所见的《女史箴图卷》历经改装而次序上有所变动,惟其中金章宗书《女史箴文》是梁清标(1620-1691)所加上,成为今日的后段。曾是本卷的收藏者清安岐(1683-1744)所著《墨缘汇观录》(成书1743)记:
图经真定梁苍岩相国(清标)所藏……后有瘦金书,自“欢不可以渎,宠不可以专”起,箴书一段,绢本十一行,字大寸许,必相国增入者。
另外,往上追溯,著录上所见的《女史箴图卷》从未见提到本卷附有金章宗书写的《女史箴》文。
《女史箴图卷》卷历代的著录并不丰富,米芾《画史》所记,早于金章宗,《宣和画谱》也只见画目,也早于金章宗。董其昌(1555-1636)于项元汴家观看《女史箴图卷》(约万历十年,1582),只说:“昔年见晋人画《女史箴》,云是虎头笔。……”董其昌将画上诸段“女史箴文”刻入《戏鸿堂帖》,未见有后段金章宗书女史箴文。明陈继儒(1558-1639)《妮古录》:“《女史箴》余见于吴门,向来谓是顾恺之,其实为宋初本,箴乃高宗书,非献之也。”至张丑(1577-1643)《清河书画舫》(序1616)已记有“顾恺之画”四字款,吴其贞于乙未(1655)四月六日舟过丹阳观于张范我家,观看《女史真图》,也未记载此卷有此未后段之瘦金书《女史箴文》。朱彝尊(1629-1709)《曝书亭书画跋》仅记:“康熙壬子(1672)春,观《女史箴》于江都汪氏。”卞永誉(1645-1712)《式古堂书画汇考》(序1682)本是抄录而来,也只记画卷本幅,而未及于后段有另一段书写的文字。对于后段箴文的书写者,向来也认为是宋徽宗所书写。当图文合一以后,晚于梁清目标吴升《大观录》(序1713),记《女史箴》:“宋佑陵(徽宗)复摘箴中语,书于绢上,计十一行。……”其后如《石渠宝笈初编》:“后幅素笺本(误记,是绢本)、宋徽宗楷书《女史箴》一则。计十一行七十六字。”清胡敬(1769-1845)的《西清札记》也是照录而已。指出是金章宗书《女史箴文》,已是二十世纪日本矢代幸雄与外山军治两教授了。
安岐所说梁清标之增入“瘦金书”(金章宗书女史箴文)一段,从现存原件所见,中隔水绫上有“张镠”(古篆朱文)、“黄美曾观”两印;《金章宗书女史箴》本卷上既有“张镠”(小篆白文)印,也不禁让人想起,这位梁清标聘请的扬州名裱画师,又精于鉴定宋画的古董商,应该就是将《金章宗书女史箴文》售与梁清标,并将书画合成一卷的操刀者。
话说回来,我们能尽信安仪周所说吗?画幅与书幅之结成一卷是在梁清标收藏时所整合?这一段的前骑缝印最上为清乾隆帝的“内府珍藏”;下方依序是项墨林(1525-1590)的“墨林子”、“墨林山人”、“子孙世昌”;后隔水才是梁氏“冶溪渔隐”。书幅前隔水之项墨林三骑缝印早于梁清标,要如何解释呢?难道以安氏之精鉴,又是本卷的收藏者,竟然无视于此三印之存在?或者三印的左旁是后来另填加?此三印:“墨林子”故意作模糊,“墨林山人”,两次出现,足以说明,《女史箴图》与金章宗书《女史箴文》,在项氏(1529-1590)之前,及在项元汴收藏时,是书画分开的两件。
与项元汴同一年代,值得注意的是文嘉(1501-1583)于嘉靖乙丑(1565)参与查抄严嵩(1480-1565)收藏书画,成《钤山堂书画记》一篇(1568记),内“法书”“宋”有《徽宗书女史箴》(下注“绢本瘦筋书”);“名画”“晋”有《晋人画张茂先(华)女史箴图》,显然书法与画是分开的。进而再查更详细的《天水冰山录》,“宋徽宗”下有“《女史箴》等帖两轴”。这两“轴”(案:古人轴卷常不分,如此卷之旁记“怀素自叙等两轴”,《怀素自叙》当是卷,不可能是轴,这或许查抄地点不一,而有此差异。)也足以说明宋徽宗(金章宗)书写《女史箴文》应该是全文,今日所见也只是最后一部分了。
检视今日的原件,《金章宗书女史箴》并非完全的一片绢,更足以说明书幅和画幅原来是不相干的两幅。书幅原件并不是完整的一片绢,它是由十三直长条幅拼成。再看第二行的第一字“可”、第三行的第二字“极”、第四行的第三字“有”、第五行的第四字“以”、第六行的第五字“子”、第七行的第七字“之”;第十行的第一字“所”、第六字“自”;第十一行的第二字“显”、第六字“史”;第十二行的第三字“告”,下面均有横切的痕迹。这说明了什么呢?书幅为了配合画幅,原来每行应该是八(九)字,改成是每行七字(最后一行八字)。也就是说,原来书幅的高度大于画幅,如果金章宗书写的《女史箴文》是为前面的《女史箴画卷》所写,那选用的绢,高度就是应该是一致的,也就用不着有此切割了。切割时为了避免损毁掉字的痕迹,如“致”(第三行)字的最后一捺、“美”(第四行)字的最后一捺、“翩”(第五行)字户旁的一撇、“子”(第六行)字的一横、“敢”(第十二行)字的最后一捺,都留下避开的尖形拐角痕迹。这就像是拓自大石碑的大拓本,装潢成小册时,用的是“蓑衣裱”的方法。就中“自、史”两字之割切则是为了调整字距,第七行不在 “此”而是“之”字,亦同此理。其切割痕与复原请见说明。另一种我认为也有可能,那是行与行之间隔,远比今日所见宽阔,行与行的间隔处上面有严嵩的收藏印,这个奸臣的印章是收藏者所忌讳,不用挖补,而是整行裁弃,再拼回,也就是行间横宽缩短了。
宋元明的民间收藏
从《钤山堂书画记》与《天水冰山录》的记录可见,当时严嵩曾经收藏《女史箴(图)》,“书、画”是分开的。果如是,那金章宗(1169-1208,1189起在位)有否收藏《女史箴图》固然无法从“广仁殿”印来证明,那“群玉中秘”印钤盖的后隔水裱绫,从别处移配来也不无可能。
这卷《女史箴图》曾为贾似道(1213-1275)所收藏,见之本幅者为“悦生”瓢印,后隔水裱绫出现了:“长”、“秋壑图书”。这三方印与著名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黄庭坚《松风阁诗》及《宋四家真迹》钤印都是一致的。金章宗与贾似道的活动年代差距,允许此件由北地来南。(前述著名的《唐怀素自叙帖》就是“群玉中秘”印与“秋壑图书”印接连出现于前隔水。)即使肯定《女史箴图卷》后隔水上的北宋“内府图书之印”及金章宗“群玉中秘”之印为真,它是否与《女史箴图》或《女史箴文》,宋徽宗或金章宗有直接的装潢关联?这一片后隔水,安仪周认为是“宋绫”安氏又提到《自叙帖》上的前隔水是“描金鸾鹊宋绫隔水”,尽管这《女史箴图卷》与《自叙帖》上的“群玉中秘”印是有所差别,但说来钤盖的位置是违反常态的,再说,本图卷后和后隔水的骑缝印,已经晚至“项元汴”了。这还是要再说一次,本卷“女史箴图”与“文”,原是两件,其后屡经更改装裱,也就令人起疑问,本件后隔水绫是从他处移配来。
接着,单从目前装裱上骑缝印最早的印记探查,前隔水与本幅上的“三槐之裔”与“思无邪堂”印应该是最早的(其次为项元汴诸印)。“三槐之裔”是元代名道士王寿衍(1273-1353)(见台北故宫藏《元李士行江乡秋晚》拖尾)。明代王鏊(1450-1524)也有此印,若此印确为王鏊所有,则时间已延至十五、十六世纪之际。“思无邪堂”印,此印之拥有者为何人?一时无法考定。“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也”。宋高宗吴皇后既是引《毛诗》序以为“贤志堂”,则“思无邪堂”印也归为吴皇后收藏印,并不唐突,但这不是绝对的直接证据。
这儿,再回到何以在如此短期间能从宋转换为金朝(或章宗)收藏。如果“宣和”、“绍兴”诸印皆伪,只有“睿思东合”为正确,那可解释为北宋徽宗收藏,因靖康之难直接入为金朝所北载而入金内府。然而,如此一来,那作为南宋高宗吴皇后收藏印的“贤志堂印”,又如何解释呢?主张“贤志堂印”为吴皇后者是明代丰坊(1492-1563?)。他为华夏(约1465-1566)作《真赏斋赋》(嘉靖廿八年;1549)有:“握如脂之古印”一句,下注:“又一印曰‘三槐之裔’……朱文。高宗吴后二印,‘贤志堂印’白文螭纽,‘贤志主人’……。”此印既尚存于明代华夏之收藏,则《女史箴图卷》上之“三槐之裔”、“贤志堂印”是否出于明代华夏时所钤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上后隔水有“真赏斋印”(白文方印),又有“贤志主人”及“三槐之裔”印。《唐颜真卿祭侄文稿》后隔水上也有“真赏斋”印(朱文长方),也有“贤志堂印”,惟此“贤志堂印”位置在左下角,因此,时代应在上方诸印之前。且同隔水右下及左上骑缝,又另有“瑞文图书”印。此印亦为高宗贵妃刘娘子印,是此《唐颜真卿祭侄文稿》卷为南宋内府所藏。但《平安何如奉橘帖》之“真赏斋印”(白文方印)钤于后隔水与拖尾之骑缝,显然曾经华夏之装裱,则其上“贤志主人”及“三槐之裔”,有可能出于华夏之钤盖。惟《女史箴图卷》未见华夏之收藏印,只能提醒十六世纪之间,“贤志堂印”、“三槐之裔”两原印尚存于世,并作此猜测了。这也可以作为宋、金之间收藏的问题,思考的方向猜测。
另外,“花押”印(如“雍”字之行草写法)一方,亦见于《平安何如奉橘帖》上。目前未见有学者指出是何人所有?又见本幅卷前有帕思巴文“阿里”(阿里活动于十三世纪后期)一印。此处也不得不说,《女史箴图卷》与《平安何如奉橘帖》、《中秋帖》、《吴彩鸾唐韵》,从收藏印所见,实在太多重复性了。这几件本幅上的“宣和”、“绍兴”印,几乎全伪,但到元朝后,收藏印就不是问题了。此四件在元代,都归于“阿里”的收藏。元代又曾有一位“陈宪副”收藏过《女史箴图》,只是此图是否今日所见的《女史箴图卷》?《女史箴图卷》入明代,早期为谁所藏,并不知晓,后入严嵩之手。项元汴之外,如顾正谊(?-1597之后)曾收藏本卷,但幅上并无其印记。余就收藏印所见,如“张准”(“准印”)是否即前引吴其贞于“乙未(1655)四月六日舟过丹阳于张范我家,观看《女史箴图》”之“张范我”。张范我字伯骏(1614-?),若以“我为准范”,“张准”可能就是“张范我”,即张捷(死于顺治二年,1645)之子。另又有昆山“张准”,曾任建安知县,不知是否同一人。“张则之”(孝思;活动于万历崇祯间。1573-1643)印,张则之(丹徒人)与张范我(丹阳人)均是同时人物。“陆经筵”一时无法查证生平。名“宾臣”者,不只一人,“宾臣”与“笪在辛”(重光;1623-1692)上下联钤大小相同(见前隔水),是否同一人亦待考。又有高士奇(1645-1703)、梁清标、安岐诸人印,最后入清宫为乾隆皇帝所收藏。英法联军之役流出清宫,后转入大英博物馆,这是颇多人知道的。至于后段金章书法的收藏者,为明朝安国、清朝张镠,已如前述。
“卷字柒拾号”骑缝半字题记
《女史箴图卷》前裱绫存有骑缝半字题记:“卷字柒拾号”。(左半存于画幅,右半存于登记册上存档,俾便查对。)这代表何意义呢?所见前人对此相同骑缝半字题记略有解释者惟吴其贞:“《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画前面隔首上有宋徽宗合(骑)缝眷字四十八号。”(此“眷”字当是“卷”,吴氏误认或误抄。)此卷是否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者?但目前“大阪”此件前隔水已见不到此“半字”题记了。吴其贞主张是“宋徽宗合缝”题记,然未加以说明。就此“半字合缝题记”又见于南宋画风的台北私人藏《宋谢元折枝碧桃图卷》之“卷字陆拾柒号”。又《传王维伏生授经图卷》有“卷字壹号”。又《五代阮郜阆苑女仙图》之“卷字拾玖号”;《宋高宗书洛神赋》之“卷字柒拾伍号”。既出现于宋高宗、谢元之书画上,明显的应该不是“宋徽宗合缝”题字。此外,原迹及图版未目见,都见于《石渠宝笈初编》记录,尚有《宋赵昌笔蛱蝶图卷》(现藏北京故宫),之“卷字拾号”。《女史箴图卷》与《宋谢元折枝碧桃图卷》、《传王维伏生授经图卷》、《五代阆苑阮郜女仙图》、《宋高宗书洛神赋》这五件同样的骑缝“半字题记”的书写风格是完全一致的。
这一个半字“?字?号”的编定年代,时代上限的订定,粗浅地说,这几件的时代即是同南宋或更早。那从宋高宗内府所藏追查,编号的方式,最常见的是“千文编号”。周密《齐东野语》卷六“绍兴御府书画式”:
应搜访到名画,先降付魏茂实定验,打千文字号,及定验印记进呈讫,降庄宗古分手装褙。
又周密《云烟过眼录》录“宋秘书省所藏”条:
乙亥(1275)春……书画别有朱漆巨匣五十余,皆今法书名画也。是日仅阅“秋收冬藏”,内画皆以鸾鹊绫象轴为饰,有御题者,则加以金花绫,每书表里皆有尚书省印,……。
所藏书画既是“秋收冬藏”编号,如此则可证明“千文编号”之存在。这段记载又提到的“通阅一百六十余卷,绝品不满十焉”。书画目“秋收冬藏”四字号,就有一六十余卷,则知每一字下又有分出若乾号。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卷”字并不在《千字文》内。因此这个“卷字半字”合缝题字编号,又可以肯定不是南宋内府所藏编号。
另《宋谢元折枝碧桃图卷》画之后又有“温字柒号”(全字),这又该如何解释呢?按北京故宫藏《唐卢楞迦笔六尊者》图册,第一开右下有“○字壹号”,字体是相同的。又《石渠宝笈初编》画禅室有《唐宋元名画大观册》第七幅《巨然笔江山晚兴》,左下方有“温字贰拾伍号”,上述前两件所见,这字号并非“半字”,且字上钤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并有“司印”半印出现。《巨然笔山水画》未见记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却有“都省书画之印”之半印(另下有半印不可识),若以习惯论,则此“全字号”当是明内府收藏字号较为妥当。
元内府收藏超越千件,有所编号也是可以理解的。《秘书监志》至正二年(1354)五月条:
本监所藏,具系金宋流传及四方购纳,古籍名画不为少矣。专以只备御览也。然至元迄今,库无定所,题目简秩,宁无紊乱,若不预将经史子集,及历代图画,随时分科,品类成号……置簿缮写……庶乎供奉有伦。……。
“品类成号”用千字文是顺理成章的,然而,我们检视目前尚存且曾经元内府藏的名迹,如《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卷》、《唐吴彩鸾龙鳞楷韵》、《唐孙过庭书谱》、《黄山谷书赠张大同卷》、《黄山谷书廉颇蔺相如传》、《顾恺之洛神赋》、《宋诸帝御容》等等,可能是历经装潢更动,今日也就无法看到“品类成号”的留存。
“女史箴、伏生、折枝碧桃、阆苑女仙、洛神赋”五件既然同一“卷字”号,且字迹统一,是否可视为金或元内府藏品字号?金章宗之所藏为“五百五十卷”,不知如何编号。但以谢元之时代(与马远同时或稍后)恐未必能入金章宗之收藏。巧合的是七件俱为“卷”字号,说七件装裱具为“卷”,则以“卷”为品类分号,即以装潢区分,如此,作金、元代宫廷之收藏编号,是否可以?目前所见,并无字号可见足供比对。显然,除了《五代阮郜阆苑女仙图》,梁清标曾是六件的收藏者,然而,梁氏的收藏今日犹多可见,却无人提起他有如此编号。
笔者的猜测,还是因某一共同事件的编号。贾似道被籍没,有“台州市房务抵挡库印”。元内府的编号虽不明,从这七件都是元朝以前的作品,也有学者指出它的可能性。元大长公主(约1283-1331)个人收藏似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做此“半字编号”。明朝如项元汴之收藏“千字文”编号,今日也颇多遗存,也不做此半字者。明代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已有千文字号相伴出现。因此,还是从明代查抄案思考。明初大案有胡惟庸(?-1380)及蓝玉(?-1393)案两件。因此,“司印半印”之用途,近有主张是查抄胡惟庸之书画收藏者。遗憾的是今日不知胡氏之收藏,(所见惟台北故宫藏《唐人明皇幸蜀图》有“濠梁胡氏”及“相府图书”两印,此幅未见“司印”半印。) 难以比对,今日尚多钤有“司印半印”之名书画,何以仅见这“濠梁胡氏”及“相府图书”两印呢?此外,最为人所熟悉的是严嵩案。沈德符(1578-1642)《万历野获编》“籍没古玩”:
严氏被籍没时,其他玩好不经见,惟书画之属,入内府者,穆庙(1567-1572在位)初年,初以充武官岁禄,每卷轴作价不盈数缗,即唐宋名迹亦然。于是成国朱氏兄弟,以善价得之,而长君希忠尤多,上有宝善堂印记者是也。后朱病亟,渐以饷江陵相,因得进封定襄王,未几张败,又遭籍没入官。不数年,为掌库宦官盗出售之,一时好事者,如韩敬堂太史、项太学墨林辈争购之,所蓄皆精绝,其时值尚廉,迨至今日,不啻什佰之矣。其曾入严氏者,有袁州府经历司半印,入张氏者,有荆州府经历司半印。盖当时用以籍记挂号者。今卷轴中,有两府半印,并钤于首幅,盖二十年间,再受填宫之罚,终于流落人间。每从豪家展玩,辄为低回掩卷焉,但此后黠者,伪作半印,以欺耳食之徒,皆出苏人与徽人伎俩,赝迹百出,又不可问矣。
“籍记挂号”者,可以说明书画上载有“数字”。至于目前,笔者并未见有“袁州府经历司印”及“荆州府经历司印”半印。按:清王恩寿《眼福编》于《王摩诘江乾雪霁图卷》跋:“严氏籍没,锦衣卫经历以印钤其字画之首,人嫌为不祥之物,辄割去之。是卷之首仅留印边,而去其文,明制锦衣卫六品方印。此必卫印无疑,既是卫印,此卷亦为雪溪图。”此画未能得见,割裂的实例可见于《五代南唐赵幹江行初雪》。张丑记此画:“嘉靖间归分宜权相家(严嵩),引首关防具存……”今日原件不但未见此“引首关防”,原金章宗墨题的前隔水锦文黄绫也为乾隆帝所更易。这个“关防”显然应该就是“袁州府经历司印”半印吧!这也说出了目前难见的原因。又可能如“典礼纪察司印”,在书画上只存“司印”两字,即便见到,也往往联想是明初“司印半印”,而不是此“袁(荆)州府经历司印”半印。从今日名迹上的“司印”考察,“司印”出现之尺寸,纵高在6.6至6.8厘米之间(这是绢本装裱时衬托张拉之差异),若传为《宋法常写生卷》有“司印”半印,纵则只有6.1厘米,“印”字下方“ㄗ”篆法亦不同,且印见于卷首,如此不一,虽然《天水冰山录》并未记载《宋法常写生卷》为严嵩所曾收藏,但也难免使人联想到此“司印”半印,非止于单一官署印:“典礼纪察司印”的可能。
上引文也说出原来严嵩收藏的《女史箴图》,籍没入官后,许多作品成为项元汴收藏的可能来历,但此卷应是由顾正谊再入项元汴之手。《天水冰山录》记严嵩之被籍没者,“古今名书画手卷册页共三二○一轴卷册”,且其查抄书画按“卷轴册”分类。此七卷中《女史箴图卷》及《传王维伏生授经图卷》两件曾为严嵩收藏。但《天水冰山录》也未必全都记录了严嵩的收藏,如上述之《赵幹江行初雪》。就此“卷字半字号”题记,再查《明会典》,它是有“勘合字号”的制度。如吏部于“洪武二十九年令本部每司各设勘合卷”。也制定各布政司、府、州使用的字号。遗憾的是没有“袁(荆)州府经历司”及“卷”字号的记载,然而,这种以查抄的骑缝籍记挂号,归之于严嵩事件,或许是思考的方向之一;当然,也可想到张居正(1525-1582)、朱宁、江彬等其他查抄案所有。(作者 王耀庭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