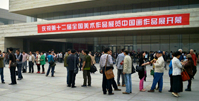-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画家闫勇:写意不可“贫学” 先论功夫再谈格调

画家闫勇
目光炯炯,亭亭而立,尾羽轻盈,俊采神驰。青年画家闫勇笔下的孔雀褪去一切繁杂雕饰,寥寥数笔,跃然纸上的便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艺术形象。问及为何钟情于孔雀,闫勇解释道:“孔雀体型较大,要用相对放松的泼墨来完成,这让我能更深刻地体会笔墨的变化。”而说起他笔下的孔雀为何如此孤傲,甚至神态如鹰,他便笑着回答:“画如其人吧,很多人认为孔雀温顺柔和,但我仔细观察过,它身上总有点清倔的劲儿,像我。”
这就是闫勇,若是论及绘画他便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若是聊起生活却又质朴豁达,童心未泯。正如他最钟情的小写意,既不拘泥于细节,也非过于激烈、大而化之。

闫勇作品:独立江鸟
文化基因不能破除
在闫勇看来,国画艺术中,师承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因传承而有文脉,时间的作用不可忽视。文化基因亦是如此,中华民族5000年发展的文明史,有根有据,代代相传。虽然在中曾有变化,但文化的总体传承是稳定有序的。”的确,华夏民族兴起于农耕文明,“继承”历史浩荡前行的生存法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当代书画大家从师从艺,下笔有神,汲取的正是古人积淀的无穷财富。
闫勇看重师承,自然也非常敬重自己的恩师范曾先生、陈玉圃先生。为了追随范先生,他更是几经周折才考取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正式成为他的学生。“我的老师曾游历欧洲各国开阔眼界,也非常敬重罗丹、米开朗基罗等西方古典艺术大师,但却不赞赏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过于追求花样和形式的做法。深刻的对比研究让他更坚定了发扬中国文化艺术的信心,因为,中国绘画艺术不逊于任何国家。”提起文化认同,闫勇对民族文化也有很强的自豪感。“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化受到了强烈冲击,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不行了。事实上,我们的艺术在世界上是一流的,我们要有这个自信。”虽未亲身经历,但多年求学也让他深刻地意识到,西学东渐,影响我们最深刻的还是科学技术方面,我们根深蒂固的人文精神和思想意识都未曾动摇。
除了范先生的理论观点和艺术成就让闫勇由衷钦佩外,更让他珍视的还有范先生本人的师承关系。“我的老师有很好的师承关系,他的老师有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这几位先生对他的影响很大。他们于范先生,正如范先生于我,都是‘真正领进门’的老师。”闫勇认为,范先生、陈玉圃先生是影响他最深的、将文化基因灌输给他的重要老师。
重师承自然讲门派,我国的经典艺术戏曲、武术无一不讲究门派,国画也是如此。“门派的确立有很大的优势,能保持艺术的发展空间、纯正性和优良性。但也有缺陷,就是容易闭塞。对画家来讲,你入门跟的师父非常关键,而凡是有大成就的,总是除了自己门派的优良基因之外,还会博采众长。”闫勇对门派的理解并不狭隘,所以,他也饱览古今画作作为日课。
任伯年和吴昌硕这两位时代变革浪潮中的画家最令闫勇倾心。这两人都是清末海派画家,彼时的上海是最早一批因贸易往来而开放并接受西方文化的城市。任伯年以画为生,无论造型还是用笔都有非常深厚的传统功底,山水花鸟人物无一不通。此外他还将民间画艺和文人绘画审美观完美结合,雅俗共赏,实力非凡。吴昌硕虽从师于任伯年,但不以绘画为主业,他曾经为官,本身具有传统的文人生活习惯,立体的人生成就了他内涵丰富的绘画风格。也许,正是这二人画作中体现出的文化包容吸引了闫勇,这与他广涉博取的治学态度不谋而合。
所谓“兼容并包”,传承古人的同时也要接受新事物。闫勇并不反对创新,但认为创新应该有着严格的规范,传承不能守旧,创新不能忘本。“现今中国画坛,总以创新为口号。乍一听挺有道理,可若没有时间、经验的积累,不可能说变就变。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孵小鸡照样需要21天,这是自然规律所致。”闫勇坚信,艺术也有自己的成长规律,想要质的飞越必经量的积累,有基础才能有突破。变化再大,也不可打破自然之道。

闫勇作品:《卧听林泉图》
艺术之路“慢慢走” 且勿急于求新、求成
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闫勇深谙艺术来源于生活的道理,所以多次上山采风写生,“国画对景写生万万不可单单追求画得像,画出来一定要有感染力,才能引起共鸣。中国绘画更讲究心理上的感悟,而不是视觉上的原样复制。”北宋画家荆浩《笔法记》中的“废物象而取其真”给了闫勇很大启发。“艺术是生活本质上的再升华,要给观者更大的想象空间。此间笔墨讲究节奏、结构和整体性。”
笔墨与意境,相生相依,早已在书画历史的长河中缠绵出佳作无数。自唐宋文人画大肆兴盛以来,绘画更成为民族文化的表白。文人画极重“逸气”,甚至提出鄙工取意的形神观。由此,中国画独有的审美特性也逐渐明朗,画者的修养成了决定画作水平高低的关键所在。然而,闫勇并不主张盲目释放个性,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扎实的基本功和厚重文化的积淀。他警觉到在文人画风渐渐向大写意发展的过程中,一部分贫学画家把鄙工取意的观点当成信手涂鸦的理论大旗,最终形神俱亡。所以,闫勇清醒地认识到“意境”并非用来卖弄,艺术之道,欲速则不达。
治学态度决定画作水平。闫勇的写意山水画大多连勾带皴一气呵成,不描述、不重复、不叠加,笔笔都透着直抒心意的自信和才情。比如表现山石、植被的肌理时,他并不依赖时兴的那些制作手段,而是将每一笔都真正写出来。画作中他灵活使用皴法,辅以勾勒渲染,娓娓道来,轻松适宜,看不出一丝技法的卖弄。“我作画和当下一些流行绘画风格不同,并不过分讲究程序。这也深受范先生影响,不喜涂涂改改,一遍墨稿、一遍着色,绝无二话。”
而在他钟情的写意花鸟中,他则致力于刻画神情意蕴。“花鸟画中最难的,就是将花鸟人格化。比如李可染画的牛如他一样强劲勤劳,李苦禅画的鹰如他一样豪放英武,那我画的孔雀自然也像我,有点倔。”
不论是一气呵成的山水画,还是带着自我符号的花鸟画,其难度都不可小觑。“凡是高的艺术,难度也高;凡是大的艺术,标准也大。”闫勇将“功夫”和“难度”看做区分真假画家的标准。所以,在当下写意画家极尽追求笔墨的同时,他也并未放松对设色的要求。笔墨可生佳作,而色彩若不妙便可前功尽弃。闫勇从不疏漏绘画的任何环节,用色舒缓而极具说服力。“这是戴着镣铐跳舞。如同写诗的格律,如果没有技术和难度,写诗就简单多了,正因为有了束缚,它才更完美,更要求工整。”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闫勇日积月累的研习中,除了对历代画家著作的痴迷,还涉及书法、古文诗集以及中外名著。在他缜密的治学态度里,真正的写意必定是先论功夫,再谈格调。显然,在对意境、笔墨和色彩的考量中,闫勇选择了最适中、最恰当的位置。

闫勇作品:《空山雨后》
画出大未来
闫勇现担任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绘画艺术系主任。提到当今的教育状况,闫勇认为中国目前的应试教育导致学生过于“现实”,上课太讲究实用性。“现在的学生需要补课,他们中小学没有学到的东西,我需要在大学课堂里给他们补上。”话语中透露着几分遗憾。一向崇尚民族文化的闫勇也承认,在教育方式上西方确实有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在西方,教育是由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完成的。不仅博物馆、美术馆对学生免费开放,就连好莱坞的诸多经典电影中也不乏脸谱化的人物和浓重的说教性,这都是全方位的输出。他们重视本民族的文化,素质教育已然深入整个社会。”
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有所侧重,我们国家着力于经济发展的一段时间内,艺术领域确实面临着投入产出不成正比的现状。但当我们的当代艺术家开始醒悟的时候,艺术修养就应该真正回归生活。“其实一个人有了艺术细胞,一辈子都非常充实和快乐。”绘画于闫勇而言,是郑重严肃的,也是轻松欢快的。
闫勇的朋友圈非常广泛,并非“知我者,二三子”的孤僻艺术家。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更能激发他的创作灵感和对写意精神的领悟。与抽象油画画家为友,更能领悟抽象笔法;与环艺老师为友,观其画作,便可体味到返璞归真的美妙;与好青花瓷者为友,立即可将绘画伸展到其他领域。闫勇在小写意领域刻下自己名字的同时,也从其他艺术门类汲取到更多质朴的快乐。
当然,闫勇对艺术的追求远不止于生活品质的提高,重大的责任感也支撑他在艺术这条路上永不驻足。“画画并非为了获奖,也不是纯粹为了商业,而是一个画家的本能。但获奖会激发学习兴趣形成良性循环、传递正能量。”对于过去的成绩,闫勇更多看重的是它为社会而非个人带来的影响,他衷心期待着民族文化的再一次复兴。为此,他脚踏实地地做着不竭的努力。“我有责任将我的学生领进门,开阔他们的眼界,即使是设计专业的学生,我也要求他们的审美有高度,设计出富有民族内涵的东西。于我个人的艺术发展而言,要更多地通过对中国绘画的理解和把控提高自我的艺术修养,从绘画的角度来展现我的艺术才能。”享受绘画之美是动力,弘扬民族文化是压力。闫勇顺利地在艺术环境里找到了平衡点,不急于辩驳和求证,只是遵循着艺术本身的客观规律,不骄不躁、目标坚定地前行。(王若蛟)

闫勇作品:《云无心已出岫 鸟倦飞而知还》
闫勇,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艺术学院绘画艺术系主任,中央美术学院2013年度青年骨干教师访问学者,天津市美术家协会会员,天津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会员。自少时喜好书画,师蒙孙玉华、田瑞先生;200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受业于范曾、杜滋龄、陈玉圃诸先生;作品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展,在全国各级展览获奖并在多地举办个展,在学术期刊发表多篇专业论文。
- >>相关新闻
- • 民国女画家陆小曼: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 • 美画家拥有罕见4色视觉:可见颜色为常人百倍
- • 万鼎携17米巨幅山水画大秦岭走进大会堂
- • 齐白石笔下最漂亮的虫子
- • “苍劲风华——尹默中国画作品展”亮相北京
- • 《松风婧待》李晓松、鲁婧中国画作品展在京举办
- • 中国传统绘画植物的隐喻——草木有情
- • 画家许翰政:从画者的角度思考绘画
- • 天津美院中国画都创作基地在潍坊揭牌
- • 天津文化旅游周暨东方艺术展在东京开幕
- • 卢延光卢诗韵父女作品首次联袂展出
- • 新中国初期浙美中国画教学钩沉
- • 中国画廊和文物商店的命运
- • 文艺不分家:那些文人和画家之间的传奇故事
- • 组图:中国画家画乌鸦包含着很微妙的用思
- • 画瓷者熙熙攘攘 无外乎利来利往
- • 世界上最早在画上签字的画家顾恺之
- • 齐风鲁韵—当代中青年艺术家学术巡回展圆满成功
- • 翰墨绘江山 老画家杜明岑国庆假期赶制新作
- • 人器如一 朴秀雅正—评陶家元的山水画

- • “画说天津”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研讨会
- • 苍劲恬然凝重朴实—李克玉书画作品评析
- • 水墨计(肆)十二人展将启幕 天津美院薛明入展
- • 王书平:与潘基文谈画的“东方鹰王”
- • 《光环的背后:我与名人》首发签售会11月2日举行
- • 百年书香 艺术精品——《华世奎书法作品集》出版
- • 天津文化旅游周暨东方艺术展在东京开幕
- • 圣地·后素—姚景卿姚铸国画精品展寿光举行
- • 书画家梁旭华的艺术世界:以字入门缘定山水
- • 挖掘传统 借古开今—薛永年谈李毅峰的山水画艺术
- • “荷语—郝跃先个人作品展”在天津空港经济区开展
- • 韩必省书画作品展暨慈善捐赠活动在北京举行
- • 天津美院教授著名画家何延喆80年代山水画课徒稿
- • 天津艺术家张羽:毛笔皴擦掉了当代水墨精神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