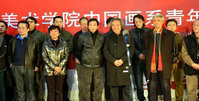陈佩芬先生走了。她走得那么突然,那么匆促。一个月前,她还打电话给我,聊起不久前出版的《中国青铜器辞典》的事,我答应她要写一篇评介文章。过几天,我打电话去她家,连续两三天,白天晚上,电话总是没有人接。我暗自猜想,大概住入医院了。我知道,她从来不用手机,她儿子手机我又不清楚。后来,我问世纪出版集团张晓敏先生,晓敏告诉我,陈佩芬在中山医院抢救!他说,上个月21日,陈佩芬去上海博物馆,同事们见她身体很不好,劝她去医院检查,她不肯。是工会的同志硬把她送去医院的。没有想到,一到医院就发现她有多种严重疾病,经过一番抢救,略有好转,送进重症病房“监控”。我想,她的病总会好的,等她好转才去探望她吧。万万没有想到,11日上午8时35分,我正要与朋友去散步,突然手机响了,是晓敏的电话。他沉痛地说:“陈佩芬走了!今日8时去世的,是她儿子告诉我的。我们下午去她家吊唁吧!”顿时,我悲从中来,久久说不出话来。下午我们到“陈府”吊唁,望着陈佩芬的遗像,心里十分难过。他的儿子小丁告诉我们,她妈妈在医院经医生全力抢救,终因突发病毒性血管炎,回天无术,永远离开了我们。
热爱博物馆 钟情青铜器
陈佩芬是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资深研究员,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她是1952年进入上海博物馆的,那时,她高中还没有毕业,还是个黄毛丫头。一到博物馆,她就觉得博物馆是一所很好的学校,能够学到很多知识,由于勤奋学习,她的业务进步很快。不久,馆领导让她与吴朴堂先生担任征集编目组正副组长。这是文物进入博物馆的第一道关口。一件文物能否入选进入博物馆,都要经过他们会审,然后请文物收购委员会的专家鉴定,什么是真品,什么是赝品。陈佩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一记录,编目存档。现在上博的编目册上还留着许多当年陈佩芬的笔迹。馆领导见陈佩芬是一块从事文博工作的“好料”,又专门指定蒋大沂先生做陈佩芬的老师,教授文化和文物知识。蒋先生博学多才,尤精金石和古代文献。陈佩芬谈起她拜师的情景说:她第一次看到蒋老师,老师说她基础差,干不了青铜器工作。她生性倔强,不服气地说:“不行,就学。”蒋先生看看这小姑娘挺有志气,就叫她先用毛笔临摹容庚先生的《金文篇》,抄录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抄好了才来见他。其实,这是对陈佩芬的一次考试。陈佩芬拜师心切,也想争一口气,每天起早摸黑利用业余时间不停地抄,花了半年多的功夫终于将这两大册抄完,装订了厚厚的三大本,然后恭恭敬敬地向蒋先生交了“作业”。蒋先生看她诚心诚意,收了她为学生。陈佩芬说:“那几年在蒋老师身边,学到了许多历史、文物方面的知识。”“毕业”后,蒋老师语重心长地对陈佩芬说:“你是我开门弟子,也是我的关门弟子,你在我这里主要学的是书本知识,你想研究青铜器,要向马承源学,他有一套鉴定青铜器办法,一定要多看实物。”
青铜器实物,博物馆多得很。马承源先生是中国青铜器鉴定专家,时任上海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主管文物征集和青铜器研究。马先生提倡青铜器研究要从形制、纹饰和铭文入手,进行断代研究。那时,他正在编辑一部《中国青铜器的形制》工具书,指定陈佩芬参加,她在马先生指导下,从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和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以及春秋战国的青铜器图集中整理出照片近2000份。她还向马先生学习青铜器纹饰和铭文的传拓技巧,为了掌握传拓技巧,她几乎每天都要在光素无纹的玻璃板上反复练习。后来,她又与她的同事把当时馆内所藏的绝大部分有铭文的青铜器做了拓本,装裱成六大册,作为当年向国庆献礼的成果。这一切,都为她日后研究青铜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抢救青铜器 保护青铜器
上海博物馆所藏青铜器文物有6000多件。其中许多是从冶炼厂和废铜仓库中抢救出来的。上世纪50年代中期,陈佩芬就经常和同事们到上海冶炼厂和一些废铜仓库中抢救文物。她和我谈起:有一次,一位同事从安徽运来的废杂铜碎片中发现了两条半龙,似乎是器物上的耳,但又找不到器物,只好把它存放起来,她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两条半龙,密切注意安徽运来的铜包,两年后,她从安徽的铜包中发现了两件无耳的青铜大尊,一经核对,果然这一青铜大尊上所缺的龙耳就是两年前的那两条半龙,经过修复,就成了一对造型优美、罕见的青铜器龙耳尊。据统计,历年来,上博从废铜中抢救出来的青铜器达3万多件(不包括古钱币),不少是夏代晚期和商代早、中期的青铜器精品。其中,许多是陈佩芬经手过的。
“文革”浩劫岁月,上海滩大街小巷,一群群红卫兵到处破“四旧”。收藏家被视为“资本家”、“遗老遗少”,他们收藏的东西被称为“四旧”,都在扫除之列。这可是文物,是国宝啊!当时,馆领导马承源和沈之瑜立即以上海博物馆的名义向市政府打报告,主动要求配合红卫兵清点抄家文物,并出具详细清单予以代管。此事得到市政府未复文的口头同意。因为许多业务干部靠边的靠边,批斗的批斗,陈佩芬出身职员家庭,历史清白,业务熟悉,不参加造反派,是普通群众,代管临时组织的任务落在她的头上,她和组里同事24小时值班,一接到消息,不管是清晨还是深夜,都要赶去将文物运回博物馆。红卫兵不仅抄收藏家的文物,还把公共场所中他们认为“四旧”的东西送博物馆。她不止一次向我讲起:有一次,一群红卫兵打来电话,说要送来外滩汇丰银行门口的那对铜狮和在原团市委草坪旁的那座纪念铜马,问博物馆要不要。陈佩芬果断地叫他们保存好,马上送来。她后来回忆说:“如果当时我们说一个"不"字,他们就会立即送到冶炼厂。红卫兵送来的还有寺庙里的佛像、菩萨、香炉、大钟和发掘出来的铜炮等,我们是来者不拒,通通照收照管。”
“文革”是一场灾难。但是,陈佩芬却游离于“斗争”之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管”文物。这一工作一干就是7年,据不完全统计,她经手保管、整理的收藏家有209户、抄家文物15万件。她和同事们将这批文物分户上架,造册、制卡、拍照,做盒子,还为书画做布套。当时一些“解放”了的干部和专家,如马承源、郑为、李鸿业、张公午、沈之瑜等还没有安排工作,也参加了整理抄家文物。陈佩芬佩服他们业务好、有本事,不管有什么问题,都虚心地向他们请教。她最感兴趣的是青铜器,面对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青铜器,陈佩芬向马先生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这段特殊的日子,对陈佩芬来说是终生难忘的,她后来说:“这个时期,上博的许多同志都遭受批判、下放、转业,造反派冲冲杀杀,争权夺利,工作处于瘫痪状态,而我居然还有这么好的条件来整理文物,不仅看到大量的东西,而且学到许多鉴定文物真伪知识。现在看来,中国文博界有这种好运的,大概就非我莫属了。”
研究青铜器 解读青铜器
陈佩芬著作很多。上海博物馆不仅藏有丰富的青铜器,而且有许多纹饰和传统拓片。陈佩芬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收集这些青铜器纹饰的墨拓本,1984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商周青铜器纹饰》。青铜镜是青铜器中的一个重要门类,上博藏有几百件青铜镜珍品,陈佩芬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结合传世品,对中国青铜镜各个时期的特色,在形制、纹饰和铭文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馆内的青铜镜作了全面的断代分期研究,其后又编撰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她的著作还包括《认识古代青铜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国青铜器全集》中的《殷墟以外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和《中国历代铜镜》两册等等。她的著述以文献资料与铭文相结合,资料翔实,立论准确,解读了许多历史疑案,填补了青铜器研究的空白,蜚声国内外学术界。
2004年,陈佩芬的《夏商周青铜器研究》问世,这在青铜器研究领域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马先生主编《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陈佩芬负责收集资料和撰写商代至东周的部分器物说明。可是这部轰动一时的大著,仅收录上博馆藏精品100件。40多年过去了,上博的藏品不断丰富,对青铜器的研究不断深入。陈佩芬在马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从上博所藏的6000多件青铜器藏品中精选出700件珍品,度其形体,称其重量,释其铭文,考其年代,编撰了皇皇六大册的《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这部大著有照片近2000帧,研究文字50万言。马承源馆长生前为其撰写前言,称:“此书的权威性可管今后五十年。”
2005年,陈佩芬退休了,退休,对这位专家型的副馆长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无官一身轻,她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青铜器的研究中。她说:在她的有生之年要做好两件事:一是继续解读“上博战国竹简”;二是继续整理和研究青铜器。
“上博战国竹简”是马承源馆长于2000年从香港购来的。至今已经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九辑。陈佩芬为每一辑都撰写了解读文章。与此同时,她开始构思编撰一部大型工具书《中国青铜器辞典》。辞典是一种工具书,无论综合性辞典,还是专科辞典,都必须具备有广博的知识。一般“辞典”都是集众人之力集体完成的。而这部《中国青铜器辞典》可是陈佩芬在进入古稀之年一人独立承担的。这在中国学术史上是罕见的。《中国青铜器辞典》全书共分青铜器论述、青铜器分类、青铜器器名、青铜器纹饰、青铜器铭文及释文、重要青铜器、青铜器铸造技术、出土青铜器主要遗址、墓葬和窖藏和金石学家,青铜器书目10大门类,涵盖了青铜器研究的方方面面。总计收词2800余条,图片近3000幅,全面展现了中国青铜器的现存状况和研究成果,是目前青铜器领域收录最为完备的一部大型工具书。为了编好这部“辞典”,陈佩芬可谓付出全部的心血和时间,她终日沉醉在青铜器的资料中,埋头披阅,仔细抄录,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她做学问一向认真严谨,一丝不苟。《中国青铜器辞典》参考了大量的资料,对各条目和图片,都经过仔细考证,改了又改,有些改了四五遍。陈佩芬生活极其简朴,饮食从不讲究。今年8月中旬,陈佩芬编撰的《中国青铜器辞典》终于在“上海书展”上与读者见面了。业内人士见到这沉沉的六大册,称《中国青铜器辞典》和《夏商周青铜器研究》是陈佩芬晚年对青铜器研究的重大贡献,是中国青铜器研究中的两座丰碑。《中国青铜器辞典》的权威性和《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一样,也“可管今后五十年”!
陈佩芬的一生是幸运的,她一直是在马承源先生的领导下或指导下工作的。“我今天的青铜器研究成就是同马先生的关心、指导、教诲分不开的。马先生永远是我的老师!”她真诚地说。她和马先生经常出席学术讨论会或参加青铜器鉴定,人们常常将她与马先生相提并论,她总觉得马先生的道德和学问都是她的楷模。马先生和她不知为人鉴定过多少青铜器,人家送他们鉴定费,他们都一概拒绝;他们都是北京保利艺术公司的顾问,保利公司的同志说,他们为保利鉴定了上千件的文物,不仅不拿顾问费,也从来不收取鉴定费。马先生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了陈佩芬。
陈佩芬是个很懂得报恩的人。在马承源先生逝世之后,她就为恩师马承源出版一部70万字的《马承源文博论集》。在《夏周青铜器研究》扉页,她写着“谨将此书献给尊敬的马承源先生”。她与马承源先生一样,一生与国宝为伴,以研究国宝为乐。她一生经手的文物数以千万件,而自己家中却没有一件值钱的文物。她本身就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国宝,她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唯一的女性,是著名的中国青铜器鉴定和研究专家。她为我国青铜器的保护、鉴定和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的名字永远和中国的文博事业连在一起,千古长存! (施宣圆 作者为《文汇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