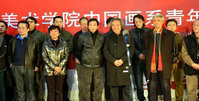(上)
说起沪上淘书的往事,不能不提到邓云乡先生。虽然邓公仙逝已经十多年了,但是在我心里,邓公带着我去上海福州路旧书坊淘书的情形,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那是在1994年金秋时节,我到上海开会。一散会就被邓公接到自己家中,邓公安排我住在他的书房里,一住就是一个星期。我与邓公每日里朝夕相处,或一同散步,或品茗畅谈,或寻幽访古,或遍访名贤。这天早晨,邓公说要带我去上海有名的福州路淘旧书,我当然求之不得。
邓公对这一带是熟门熟路,很多店员见到他都非常客气地打招呼,有几位老者还要凑上来跟他窃窃私语一番。可见,邓公在这个领域是绝对的“大腕儿”,我跟在邓公的身后似乎也提高了几分“身价”,那感觉颇为自得。一边看书,一边听邓公给我讲在上海旧书店淘书的门道——邓公告诉我,上海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出版业中心,你要挑选那个时期的图书,非到上海来不可;还有,上海还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要集散地,出版的新文学书籍比北京、广州都要多,你要淘这方面的书籍,也要到上海来;此外,上海的线装古籍也不少,这是因为周边的江浙一带,都是富庶的鱼米之乡,读书的风气自古就很浓厚,古旧书的流通量自然也是其他地方所没法相比的,而这些古籍善本一般都要拿到上海这个大码头来交易,所以,时常能在这里遇到意外的惊喜……
我们那天在福州路遇到的意外惊喜,是淘到了一册由江阴谢初霆编撰的《汉熹平石经碑录》手稿本。这书是我在一个角落里发现的,粗粗一翻,发现有些页眉页脚处,写着些蝇头小楷,精美异常,便拿给邓公审看。邓公看过也觉得这部书稿单凭这一笔小楷,就值得收藏,更何况书中所讲的汉石经,乃是印刷术发明前,中华文化典籍传承发展的最重要载体。这样一部很有学术性的手稿,不知什么原因,今日竟流落到书肆冷摊了。邓公说,你如果有兴趣,还可以继续研究这门学问。要知道,石经的研究原本就是一门显学,顾炎武、万斯同都写过《石经考》。只是近代以来,西学兴起了,这门学问才冷了下来。既然邓公如此看重这个稿本,那我还有什么犹豫的,当即不讲价钱收入囊中。我见邓公面露喜色,不禁自忖,邓公应该不只是因为帮我淘到好书而高兴吧,他老人家心里或许还有更深一层的欣慰:毕竟这些老祖宗的学问,又有年轻一辈关注并且喜欢了,这当中不正蕴含着“薪尽火传”的象征意味么!(侯军)
(下)
回到邓公的“水流云在书室”,我们都有些兴奋。吃过晚饭,邓公把那稿本要了去,说是再仔细研究一下。我当然很乐意请老人家多过过目。那天晚上,我发现邓公的房间一直亮着灯,直至深夜时分。
第二天一大早,邓公就起床了。他把我叫到自己的房间里,指着摊在桌面上的那册书稿,说他昨夜细读了一下,觉得这位作者很不简单,不光字写得漂亮,学问也做得扎实,对汉代熹平石经残石很有研究,对残石上残存的每一个字,都逐字逐句做出了精审的校订和考证。“你瞧,我刚才已经把我的‘读书心得’给你写在卷尾了,供你回去读书时参考。”我连忙俯下身去观看,只见在书稿的最后一页,邓公以那特有的清秀潇洒的小楷行书,为我题写了这样一段跋语:“侯军兄自深圳来沪,联袂过福州路书坊,以五百番购得此册。归后于灯下细阅,似汉石经制版付印之剪贴校正清样,以线装《辞源》零本翻转面粘贴成册者,应为七十年前之旧物也,弥足可珍。惜不知编者江阴谢初霆生平,唯其所注之蝇头小楷舒展挺秀,一笔不苟,足见前辈学人功力及严谨之态度。晴窗展对,景仰久之。爰志数语于卷末。乙亥重阳于水流云在延吉新屋南窗下。蝠堂邓云乡。”下钦两枚小小私印,跋前也盖上一枚迎首印,为邓公常用的“红楼”二字。
这册手稿不啻是我此次沪上淘书的最大收获。遗憾的是,得到这册珍贵的稿本已经十余年了,虽然也曾数度研读,且又购回几册与汉代石经有关的古籍(如嘉定瞿中溶《汉石经考异补正》),但真正如邓公所期望的投身于对这卷稿本的研究,却始终未能起步。一是因工作繁忙,无暇他顾,二是这门学问确实艰深,我初入门径,难以上手。如今,捧读邓公十多年前的跋语,字迹犹新,声犹在耳,慨叹书存人杳,不禁心生愧怍,怅然久之! (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