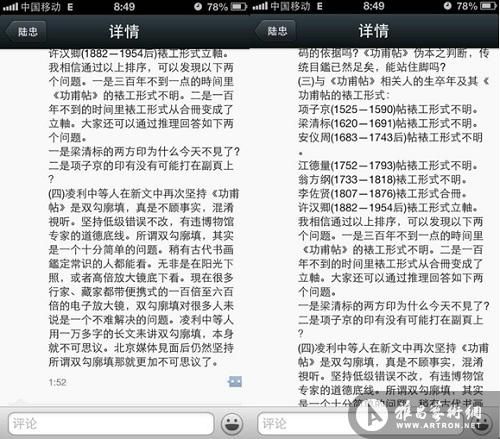文 陆忠
凌利中等人在上海龙美术馆开馆前夕,打着学术辨伪的旗号,又一次向刘氏所藏《功甫帖》发难。大标题叫《功甫帖》辨伪新证(上)。所谓新证就是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的翁方綱《复初斋文集》手稿本第六十七卷有如下记载:安记所谓"前后半钤四印”者(略去对半钤四印的描述)此四印是旧印也。余则张鏐二字白文印,安仪周家珍藏六字红文长方印,梁清标印四字白文印,茞林秘玩四字红文方印,子京两字红文葫芦印,项叔子三字白文方印,携李项氏士家宝玩八字红文长印。据此,因为《功甫帖》本幅上没有梁氏两印和项氏三印,所以翁方纲所見安氏所藏《功甫贴》並刘氏所藏功甫帖。

陆忠微信截图之一
(一)凌利中等人又一次犯下低级错误。什么叫新证?新的证据也。如果翁方纲在手稿中确认项氏三印和梁氏二印都钤上《功甫帖》本幅上,这才叫证据。翁方纲在手稿中根本没有描述十一方印中除四方半印以外七方印的钤印位置。可見,凌利中等人的所谓辨伪新证不是证据。凌利中等人的辨伪应该是根据翁方纲手稿所作的一种推理。同一段文字会产生不同的推理,这是常识。李雪松先生对凌利中先生等人推理的质疑是另一种推理。推理的关键是逻辑。李雪松先生文章的逻辑性很强。凌利中等人在逻辑推理上一再出错。所以同样一段文字,李、凌双方会得出完全不同的推理结果。我相信稍有中国古代书画鑑定常识的人都会赞同李先生的推理。凌利中等人的推理不但不正确,还把推理弄成了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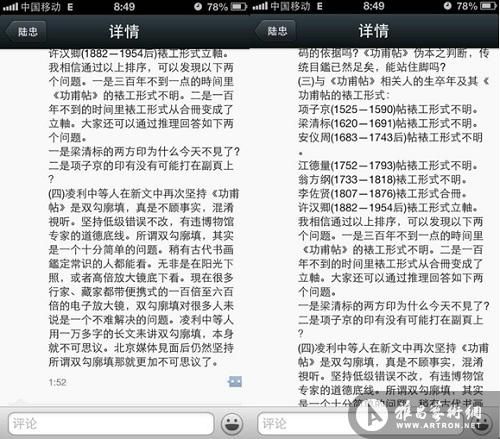
陆忠微信截图之二
(二)凌利中等人在《功甫帖》辨伪新证(上)一文中说:于苏富比《功甫帖》伪本之判断,传统目鑑已然足矣。尽管你们已经在文中公布了许汉卿先生寄存及入藏上海愽物馆文物中均无《功甫帖》的证据。我还是想问钟银兰先生:你到底有没有見过《功甫帖》原作?如果見过,请告诉大家,你在那里見过?如果没有見过,那么你在原作没有上手的情况下,和凌和中先生共发两篇关于《功甫帖》的长文,你认为这样做合适吗?符合古代书画鑑定的一般規律吗?双勾廓填有起码的依据吗?《功甫帖》伪本之判断,传统目鑑已然足矣,能站住脚吗?
(三)与《功甫帖》相关人的生卒年及其《功甫帖》的裱工形式:
项子京(1525—1590)帖裱工形式不明。
梁清标(1620—1691)帖裱工形式不明。
安仪周(1683—1743后)帖裱工形式不明。
江德量(1752—1793)帖裱工形式不明。
翁方纲(1733—1818)裱工形式不明。
李佐贤(1807—1876)裱工形式合冊。
许汉卿(1882—1954后)裱工形式立軸。
我相信通过以上排序,可以发現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三百年不到一点的時间里《功甫帖》的裱工形式不明。二是一百年不到的时间里裱工形式从合冊变成了立軸。大家还可以通过推理回答如下两个问题。
一是梁清标的两方印为什么今天不見了?二是项子京的印有没有可能打在副頁上?
(四)凌利中等人在新文中再次坚持《功甫帖》是双勾廓填,真是不顾事实,混淆視听。坚持低级错误不改,有违博物馆专家的道德底线。所谓双勾廓填,其实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稍有古代书画鑑定常识的人都能看。无非是在阳光下照,或者高倍放大镜底下看。現在很多行家、藏家都带便携式的一百倍至六百倍的电子放大镜,双勾廓填对很多人耒说是一个不难解决的问题。凌利中等人用一万多字的长文耒讲双勾廓填,本身就不可思议。北京媒体見面后仍然坚持所谓双勾廓填那就更加不可思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