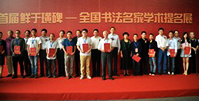-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文物光鲜:遭遇修复尴尬事

修复后的乾隆御稿箱

正在故宫展出的文物保护修复技艺特展。本报记者 和冠欣摄

河南博物院纸质研究室主任甘岚(左)在修复受损书帖。
十天前迎来90岁生日的故宫博物院,着实为艺术爱好者端出好几盘“大菜”。屡屡刷新排队耗时纪录的“石渠宝笈特展”自不必说;陈列于神武门城楼的“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修复技艺特展”,虽然热度逊于前者,却也顶着“第一”的光环——这是故宫首次以“文物保护修复”为主题,举办的综合性修复技艺和成果展。
藉此展览,人们不仅可以清晰看到一件文物“旧貌换新颜”的过程,还能感知到平日里隐身展品背后的“文物医生”的存在。别看他们大多极少露脸,这可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但凡馆藏文物走向展台前,都会由他们过一道手,为文物“疗伤”,然后让“康复者”亮相,更有甚者,近乎“起死回生”。不过,在“鬼斧神工”的独门技艺之外,文物修复还面临不少难度更甚的现状,诸如,不时有人喊着人手不足,却又总处于留不住人的境地;在现有职称评比体系里,处处受制。这些成天与国宝打交道的人们,享有的待遇却与国宝隔着好几条街。
1. 妙手回春的“魔术”圣手“最难的环节就是拼接,就像玩拼图游戏一样,只能用镊子夹着小碎片一点点去尝试。”
驻足故宫神武门展厅,不时能听到诸如“宫里藏品也能毁到这个地步”的唏嘘。这也难怪,人们寻常见到的都是些整饬完毕的光鲜品,冷不丁将“整形”前后作一对照,生发感慨也属正常。
要说修复前后差异最为明显的,当属高4米多、宽近3米的《董诰山水贴落》。据故宫文保科技部书画修复组组长杨泽华介绍,这件原本藏于乾隆花园符望阁的绢本,曾经散落为上千块碎片,有的碎片还不如小拇指甲盖大,经过修复师有如魔术般的圣手,如今再看上去已是裂痕全无。
一堆碎片,加之缺少原作的尺寸信息,要想修复如初,难度不言而喻。作为国内藏有古代书画最多的文博单位,故宫拥有一整套传承下来的传统书画修复技艺,不过,由于这件作品尺幅信息缺失,修复组只得另寻他法。最终拟定的方案是:先加固那些稍加用力就会碾成粉末的碎片,然后再一块块地拼接、压平,最后做全色处理。“最难的环节就是拼接,就像玩拼图游戏一样,只能用镊子夹着小碎片一点点去尝试。”话虽说得轻巧,杨泽华深知背后艰难。因为整个拼接过程相当于将几千块小碎片还原进十多平方米的画作里,而且,并没有明显的规律可循。最终,集数人之功,历经数月,原作终于恢复当初神韵。“要修复一件受损古书画,时间短则一两个月,长则数年之久,如果要细数中间修复过程,可以列出的工序多达六七十道。”在河南博物院从事书画修复三十多年的甘岚,前些天还特意带着部门年轻同事到故宫参观了修复特展。
除了古书画装裱修复,此次集中展示的文物修复技艺还有古书画人工临摹复制,木器类、纺织品类、漆器类、青铜器、古陶瓷、古钟表、百宝镶嵌类修复技术,以及囊匣制作工艺。用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的话讲,这次修复特展是想让更多人认识故宫的“文物医院”,也就是故宫文保科技部。
据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故宫博物院组建了文物修复工厂,直到八十年代扩建为文保部。现如今,这支宫墙内科技含量居前的队伍共有各科“医生”一百多人,负责为院藏一百八十多万件文物延年益寿。这样的人员规模不仅在国内文博系统居首,也组成当之无愧的“文物三甲医院”。如果将传统的文物修复技艺归为“中医”,现代的科学技术就属于“西医”,修复过程中,往往需要中西医结合治疗。此次展出的一件沉香雕罗汉寿字插屏,就是“医生”们通过给插屏做X射线CT照相,才最终探明内部结构,并据此开出“药方”。
2. 两千人面临一千多万件文物“以现有人员规模,要修复全部受损文物需要上千年。”
有这样一组数字真实又残酷地揭示出国内文物修复行业的生存状况。据国家文物局调查显示,全国文物系统三千多万件馆藏文物中,半数以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接近两成属于损毁严重。而国内真正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技术人员,也就两千多人。而文物修复最大特点就是“慢工出细活”,耗时数年修复完成一件文物的例子,比比皆是。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研究员詹长法估算,“以现有人员规模,要修复全部受损文物需要上千年”,这还不包括修复过程中,又产生新的待修品。
四十出头的古陶瓷修复专家李奇在二十年里,主持修复了近千件瓷器,其中就包括国家一级文物、辛亥革命博物馆所藏宝贝——孙中山生前受赠的“索耳八角花盆”,而且,这些物件的修复绝大多数由他独自完成。“不是我不需要帮手,而是实在难以找到得力助手。”在他看来,文物修复不同于普通物件,往往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外行人眼里,文物修复可能就是修修补补,粘粘贴贴,其实学问真不少。”李奇说,一个优秀的修复师如同“全能选手”,既要懂绘画、雕塑,还要掌握化学、物理、材料方面的知识。而如此高要求的综合素养,必然导致人才成长缓慢。据了解,当年和他一道参与学习修复技艺的,大部分已然放弃。
也正因为文物修复专业人才紧缺,一些被修坏的案例频频见诸报端。辽宁沈阳云接寺清代壁画修缮,所用方法竟然是在残损壁画上“重绘”了一幅新作;前些年圆明园首批破损文物遭遇的“试验性修复”,不仅部分文物被无故涂抹上金漆,就连修复出来的纹饰图案也无据可循。有人笑称此等做法“如同文物贩子在作假”。
为了防范出现不可逆的“损毁性”修复,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徐飞认为,关键还在于加强专业人员配置。据他介绍,其所在部门人员共三十多人,实际动手修复的接近20人,而这已经是江苏省规模最大的一支文物修复队伍了。“可以肯定,单单依靠这些人,馆藏文物一辈子也修不完。”
人手紧张是国内每家博物馆都面临的问题,故宫博物院也不例外。据了解,此次故宫推出的“修复特展”,除了本馆修复人员参与外,还从社会上借调了不少非遗传承人和修复高手。“他们中不少人的祖辈,原来就是宫中能工巧匠,此番"进宫"参与修复,颇有点回家的味道。”在国内资深修复专家、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秘书长贾文忠看来,不少国家的文物保护已进入预防性阶段,而国内由于缺人手,依然停留在“快不行了才去救”的应急阶段。
3. 民间修复市场处于无序状态“我买入的价格不到十万元,对方开出的修复价格竟然也是这个数。”
尽管人手不足,馆藏文物尚有专业人员保养、修复,那么,民间藏家手里的残损文物应该找谁修复?近些年,伴随民间收藏的兴起,这成为一个愈发难以回避的问题。“博物馆一般不会承接社会上的文物修复工作,主要原因还是自身的活计都忙不过来。”贾文忠说,近些年市面上陆续出现了民营修复公司,不过,由于水平良莠不齐,并没有与市场需求对接上。
这些天,家住望京阜通西大街的卢志永隔三差五就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跑,他想尝试“聘请”馆内油画修复师给自己帮点忙。原来,他一年前遭遇了一桩倒霉事。家中一幅祖传油画由于保存不善,出现了不少霉点,他特意跑到琉璃厂请来一位民间古画修复师,经过对方一番捯饬,霉点的确不见了,画面也光鲜不少。不成想不出半年,画上就出现大块色块剥落的情形,不仅一万多元的修复费打了水漂儿,画作也难保。
有人担心自己手中的宝贝被生手损毁,还有人被修复公司开出的高额价格所吓退。在圈内小有名气的藏家刘先生在拍场“捡漏”得到民国某书法家的作品,“我买入的价格不到十万元,对方开出的修复价格竟然也是这个数。”为此,他只得放弃修复的想法,坐等新的买家上门了。
“一幅价值百万元的古画,花个几万元修复还能接受,但十几万元的藏品却要数万元修复费,绝大多数人就会打退堂鼓了。”贾文忠介绍说,十多年前他就提出过一个修复费用的计算公式,即根据标的物的估价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不过文物修复的基本模式都差不多,不会因为你的估价低就少收取费用。”他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可以对民间修复机构按照资质等级划分修复范围,可以考虑设立“文物修复大师制度”,“估价高的可以送往那里修,就像在医院挂号一样,你可以选择专家号,也可以选择普通号。”
60岁的于爱平就是上海古陶瓷修复圈的“专家号”,几年前从上海文物商店退休后,她开办了自己的修复工作室。“博物馆可以考虑抽调一部分人力支援民间文物修复,最起码可以组织专家搞一些培训。”她回忆说,二三十年前还经常有各种古陶瓷修复培训班,国内很多从事文物修复的专家都是那时成长起来的。后来由于经费等问题,类似的培训活动已难觅踪影。“现在几乎每家博物馆都拥有近乎相同的专业设备、仪器,事实上,除了极个别藏品丰富的大馆,很多设备是闲置的,完全可以按照某地区出土文物的特色,将某类设备集中一处,建立几个大型修复中心,予以最大化利用。”贾文忠说。
4. 修复师工资曾是院长的两倍“三星堆博物馆有个修复青铜器的小伙子,单位把他当作重点培养对象,可人家偏偏辞职跑去修空调了。”
国内文物修复人才相当稀缺。贾文忠介绍,老一辈专家有的离世,有的退休,绝大部分已经不在岗位;中青年一代不少人中途选择转行,而年轻一代又因为评职称、待遇不高,没什么积极性。据他描述,二十多年前,受国家文物局和中国文物学会委托,文物修复委员会评出过一份“名师榜”,里面囊括了从事文物修复、保护工作工龄30年以上的老专家共80位,如今名单上的绝大多数老师傅已经故去,其中就包括他的父亲贾玉波。
在贾文忠印象里,父亲那一辈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赶上了好时候。那时北京建了十大博物馆,里面很多文物都损坏严重,需要能工巧匠修复,因此全国有名望的修复人员都集中到了各大博物馆,而且享受的待遇相当不错。“故宫当年从上海请了一位裱画师傅,他的工资是当时故宫院长的两倍。”贾文忠说。
相比曾经的辉煌,贾文忠认为修复行业如今的地位与当年还有差距。“主要还是评价体系变了。当年是看谁能把活儿干好,现在基本上是以职称为导向。”在他看来,修复人员在博物馆体系里属于最基层,“从最初设置的"修复工厂"就可以看出来,是"工匠"身份,评职称当然会落在科研人员后面。”他说,“都说新闻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好歹在新闻版面上可以署名吧,你可曾见过修复好的器物与哪位修复人员的名字相关联?”在他看来,那些凭借高超技艺修复好了诸如《清明上河图》这般国宝的,却并不能被当作成果,必须得发表研究文章。为此,文物修复委员会推出了一本名为《文物修复研究》的学术刊物,专门消化同道中人的发稿需求。
原本就人手紧张的修复行业,却一再陷入人才流失的境地。“三星堆博物馆有个修复青铜器的小伙子,单位把他当作重点培养对象,可人家偏偏辞职跑去修空调了。”年过七旬的杨晓邬被誉为四川文物修复“第一人”,三星堆出土的成百上千件青铜器,一大半是他修复的。在他看来,这种现象最直接地反映了行业的无奈。“我们看得见大量国宝,却往往忽略了修国宝的人。”王琛是河南博物院文保中心传统技术研究室主任,尽管修好过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的“云纹铜禁”,只有高中学历的他依然只能被评为中级职称的技师。
北京联合大学是本市较早开设文物修复专业的高等院校,据该校应用文理学院教授顾军介绍,由于缺乏师资,学院设置的多个文化遗产类实验室,利用率很低。他建议,院校聘请人才应当突破以学历为主要依据的规定,以实际需要引进。
“与中国的稀缺状态不同,文物修复在西方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职业。”詹长法建议,中国也应该鼓励更多的能人通过一定准入制度参与到文物修复当中,促成修复师的职业化,或可打破文物修复的人才瓶颈。
延伸阅读
文物“中西医”
话语权之争
秉持传统修复的人就像中医,“望闻问切”一环不能少;倚靠科技手段的人如同西医,需要动用X光手段作检测。由于双方坚守的文物修复理念不同,而让国内外专家长久陷入话语权之争。
西方文物修复理念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可辨识性原则。具体而言,是指修复部分与文物本体应该有所区别,远观不致导致整体不协调,近观则应能肉眼辨别出修复痕迹,因此,在国外看到文物修复品打着“补丁”,当属见怪不怪。而“修旧如旧”的准则,如同悬在国内文物维修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追求的是修复品无限接近原作。
据贾文忠介绍,中国传统修复技艺上的修复,系美术修复、陈列修复和考古修复中的美术修复。比如,书画修复和陶瓷器修复在补全的基础上,还会以做旧、全色作为修复的终结;青铜器修复最终也会以作伪锈而告终,对修复补配好的部位从里到外都要做上锈色,加以掩饰修饰。如此做法,无非是让修补复原之部位与器物本体部位“浑然一体,补处莫辨”,进而让参观者无法识别到修复痕迹。事实上,这一高超技艺历来还被用来衡量传统修复技师的水平高下,往往也是修复技师安身立命的法宝和绝活儿。但是,如此绝活儿在西方修复者眼里,却被认为损坏了文物本身的原真性,会给观者传达错误信息,故而将其称为“过度修复”。
用“谁也瞧不上谁”来形容中西方修复界的现状,并不为过。国内修复界对西方修复中国文物的方式也颇有微词。据贾文忠介绍,西方修复人员对金银器和青铜器进行修复时,习惯将器物表面的绿色锈蚀全部除掉,对青铜文物则实行封护处理,但易使其颜色变深。这些在国内的传统修复界看来,都是无法接受的。
贾文忠认为,在与国外文物修复理念保持交流的同时,还要对咱自己的修复理念有信心。他举例说,青铜的东西去锈,用科技手段先进仪器可以做到,可如果碎成一百多瓣,想要修复如初就必须用传统手段了,“尤其对于青铜器、中国书画等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修复技艺应该尽量用中国传统的方法。我们老祖宗的那套技艺就是建立在他们熟知的材料基础之上的。”

- • “津门七叟”诗联书画印展在楹联博物馆举办
- • 中国楹联书画院女子分院成立 黄雅丽任执行院长
- • 视频:从天津走出去的国际油画大师-程亚杰
- • 第八届全国著名花鸟画家作品展参选作品评审揭晓
- • 翰墨留香—中国画十人邀请展在6号院艺术馆揭幕
- • 丹青新绿—阚传好、刘奋强中国画展甘肃临洮展出
- • 组图:纪念李叔同-弘一大师诞辰135周年书画作品欣赏
- • 墨韵禅心·张佩钢佛像展将在东莞饶宗颐美术馆开幕
- • 天津商大艺术学院陶瓷绘画作品展亮相天津图书馆
- • 纪念弘一大师诞辰135周年书画作品展开展
- • 吴少湘雕塑艺术30年探索文献展在天津美术学院开幕
- • 组图:柴树朴书画展在水上公园今晚人文艺术院开展
- • 天津市美协秘书长李耀春在釜山艺术节做主题演讲
- • 顾志新师生书画印精品展在图书大厦开幕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