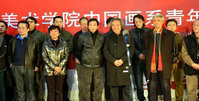这是一个已经扎好的仙鹤骨架,骨架是彩扎的核心

聂方俊扎的骨架追求神似,从这头猪的造型便能看出这点来
聂方俊是凤凰彩扎的国家级传承人,今年80岁了。他出生于一个彩扎的世家,他和父亲学艺,父亲又是和祖父学的。至于他们家族多少代人做彩扎,他就不知道了。
从10岁起和父亲学做彩扎,并且对于彩扎有深沉的热爱。即使是在文革“破四旧”的年代,纸扎被当作陈旧的事物而烧毁,纸扎匠人纷纷改做他行,聂方俊也被下放到农场,但他的脑子依然在想着如何扎出各种生动的事物来。
现在70个年头过去了,长年累月的劳作,使他患上职业病:严重的肩周炎和颈椎炎。加上年岁不小,使得他现在的双手明显的发抖,并且走起路来身子稳。然而他的双眼依然有神发亮,声音依然有力。
在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给一个走马灯裱糊。他双手颤抖地将纸张排好,再颤抖地将浆糊涂上。他的手一路颤抖,神奇的是,当抓起纸张准备裱糊到骨架上时,似乎有某种外力钳住他的双手,使它们不再抖动,而是准确地贴到竹篾上。但是一旦重新回到空手的状态,双手又恢复了高频率的颤抖。他的每一个动作让外人看了都觉得颇为费劲。
一个走马灯的裱糊,现在他要三天的时间,而过去只需要半天时间就足够。一个走马灯从扎骨架到裱糊和完成彩绘,在年轻的时候,他只要用一周的时间就能完成。但现在,他要20多天的时间。疾病和年龄,使得他的效率大打折扣。
他时间宝贵。由于他的地方过于难找,所以我给他打了5个电话问地点。而每次接电话,他都要很慢地到固话旁边,讲完电话再回到骨架边接着裱糊。接了几个电话后,他小半天的时间就没有了。
因此他对于自己的时间规律有严格的界定,在我第一次到他的家里时间太久了,我明显感觉到,他突然希望我赶紧走而不要继续打搅他。在第二次不约而至地再到他家里,他更明显的希望我早点走了。他说,时间就是金钱,而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我其实占用了他的时间,而来访的不仅仅是我一个记者,还有别的记者各路的领导和专家。关键的是,上午11点半一到,他就要休息了。
无论如何,对于一个民间工艺的传承和发展而言,获取金钱上的回报,是一个现实的、不可忽略的问题。他向我提到,有时候,一些领导前来他家来参观,并喜欢他的一些作品。出于人情上的考虑,他免费赠送,但这些手工艺其实他已经付出很多的心血进去。
另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他的徒弟们对于彩扎这个行业并没有多少信心。尽管聂方俊有12个徒弟,但他们无法完全依靠这个手艺来生存。“他们无法纯粹依靠这个来生活。”多数徒弟的情况是,“在家里自己劳动,不是以这个为主业,单独靠这个没法养家糊口。”
徒弟们只是在他接订单比较多、做不过来的时候前来帮忙,平时仅有2个徒弟在身边帮手。不过我见到他的那两天,徒弟都没有出现。他年纪最大的一个徒弟今年60多岁了,那是出于热爱而拜聂为师。但对年轻人来说,热爱就不等于生活了。
聂方俊也给徒弟们报酬。扎一个小狮子头的骨架50元,裱糊一个小狮子头给50元。基本上完成一个工序就给50元,按照计件的方式支付。但一个徒弟一天最多完成一个工序,30天下来也仅能拿到1500元的报酬。这还是因为聂方俊具有一定的名气,使得从他这儿出去的东西具有一定的品牌溢价。“我不到市场卖,都是他们(顾客)登门来买。各地都是这样子,知道我就来了。一个传一个,他会自然来的。昨天北京的,来了。前几天,意大利的客人来看,买小狮子头。”
而若是徒弟们自己做彩扎,他们显然无法招徕到多少外地游客,也没有品牌溢价,能得到的收入就更少了。
聂方俊说,现在彩扎行当比起以前做的少了,所以“你要做得好,做的不好,他(顾客)就不光顾你了。”而徒弟呢,最好“跟着师傅做。师傅在做的时候,他也同样挣到钱。”
当地社会对于彩扎的整体需要也在下降。年轻人大多数外出打工,过年过节也没有舞狮子和耍龙了,于是过去经常需要的大龙头和大狮子头便没有市场。彩扎的前景更紧密地和当地的旅游市场关联。而它们要和凤凰古城里无数的玩意儿展开竞争。(许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