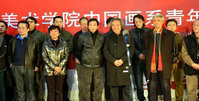追本溯源,曾经的肖像画,更多的是一种记录、一种敬畏、一种教化。事实上,自肖像画滥觞于远古的商周,它所呈现的就不仅仅是一幅描绘人物的作品,反之,肖像画随着岁月的变迁一直承载着不同的语境,反映着不一样的文化内在。譬如,单单的一幅帝王肖像,能从颜色、构图、象征图腾等上透视出不可僭越的阶级;一幅士人肖像则能在人物面容勾画间和山水的背景中蕴含文人所追求的淡泊清远。然而,随着摄影技术的发明、图像的泛滥、科技的进步、图像时代的来临,肖像画已然脱离了传统肖像原有的理论框架。在肖像画纪实性的意义被取代、传统的教化作用也几近消失的前提下,关于肖像画的未来发展引起了种种议论。有人认为,肖像画将会面临着崩塌和瓦解,而过去的90年代可能是肖像画的“最后一次爆发”;又或是认为,当下的图像时代已然将肖像画排除出大众的视野以外,远离了实际生活的肖像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作为时代的推动力的角色,并仅能成为少数精英把玩或研究探索的对象。这些言论不禁让人反思,肖像画作为一种古老的绘画表现内容,是否真如所说般走进仅有少数人能理解、把玩的局面?在当代语境下,肖像的画布背后,应该向人们呈现怎样的内在?
肖像画的内在观念反映
在探讨肖像画的发展之前,或可回溯早期传统肖像画中所传达的观念。事实上,传统的肖像画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可算是互为印证的发展关系。一如不少古老文明,国人自古有对于神灵的信仰,信奉天地万物都有其代表的神,因而中国早期哲学也纳入了“天”(天命)的概念,并由此延伸而出“天道”这象征了囊括君臣、宗族、家庭以及一切自然万物秩序的思想,将“天道”发展成为最早期的伦理纲常。而最早影响到肖像画发展的“气”的哲学观则是从“天”所引发的观念。
按照中国古代哲学看来,“气”所指的是一种无形而流动的能量,它关系着人体肢体结构、主导着一个人观看个体图像时的感官运动,古人相信肖像能传达“气”的力量,因此,肖像画最早被看作拥有“教化”、“事功”、“颂德”、“奉祀”的功能。诸如帝王的肖像能昭君威倡仁德,而先人之像则可示尊颂传扬。但这时候的肖像画,“述其事”往往比“肖其人”更为重要,一是因为肖像所绘的多为如周公、文王等众口相传的历史人物或如《女史箴》等早期的人物画传,绘画的对象仅能是依靠画家自身想象创作;二是因受到上述古代哲学观点的影响,古人认为,人的现实外表容貌只是用以传达美的一个媒介,但人的精神内在是否能和“天”相互应和才是他们所追求和希望传达的观念。所以总括而言,早期的肖像画都以帝王、先人和神灵等为主要题材,希望能够通过肖像造就观者对“天道”秩序乃至道德规范的联想,以训将来。它所传达的是一种“成教化、助人伦”的观念。
无独有偶,这与西方的宗教“圣像”(Icon)是异曲同工。上帝本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西方的宗教肖像画之所以存在,原意并不是为了引发观看者在视觉上的赞美,而是在于唤起信徒对于上帝的记忆,因此西方的宗教肖像画常以归纳而成的固定符号和肖像去讲述圣经的故事以获得信徒内心的共鸣,从而达致布道的目的。
虽说在当下社会,肖像的教化功能几乎消失殆尽,但事实上这种观念依旧能贯穿在肖像画的创作之中。因为肖像画针对的对像是人,换之而言,观众和画作之间,也是人和“人”的一种直观的接触,肖像面容映射出人性品格、内在,也能映像时代特征,其中亦糅合了艺术家的绘画经验和对被描绘者的主观感知。有时候,肖像画能直抵人心,是因人物所刻画的形象触及到观者内心引发共鸣,从而让人动容,这大概就如中国古代哲学论所说的肖像画中“气”的感染。
中国传统肖像审美的嬗变
有人认为,20世纪以前的中国肖像,是具有明显的、清晰的创作动机与表现对象。中国传统的肖像画,在长久以来除了道德教化的作用以外,在其成熟阶段时(魏晋时代)亦被赋予了一种新的美学姿态,随着当时“人物品藻”的审美风尚,人的风度、仪容及气度成为了肖像画所传达的重点,这也可看作是早期一个“个体觉醒”的历程。 当时的肖像画中,多见描绘文人贤士林间纵酒放达、抚琴长啸、褒衣袒胸,而这种避居山林的士人精神和形象则渐渐演变成为中国古代理想社会的生命典范和审美共识。这类题材的肖像,除了透视出属于那个时代的独特精神内涵外,还显示出这个时期的画家他们所追求的,已发展成为具象之外的气质、神韵和人物的品性,而这种审美风格直接影响了往后中国数朝的肖像画,特别是文人肖像画的发展。
迈入近代,随着西学东渐,欧洲传教士等人与当朝官员乃至皇帝的接触令西方的文化得以进入到中国政治的中心地带,亦带来了东西方绘画的初步交流,而那些融合东西方艺术特征的作品则最主要体现在肖像画题材上。虽然时人评价西洋画“虽工亦匠”,但不少中国画家却也从西方的绘画技巧上取得了借鉴和吸收:其一是人物造型吸取了西方绘画的技巧尝试运用色彩晕染表达人物体积感,譬如曾鲸;其二是在构图章法上采用西方的焦点透视,譬如焦秉贞。但这段期间,中国画家对肖像画绘画技巧的变革多数是建基在传统审美品格上,所以肖像画中审美格调和气质内涵上依旧是贴近固有的传统,内容符号也多映像了传统中国美学所推出的理想精神。
真正让中国肖像画的存在方式、表现手法、风格题材均发生深刻变化的是十九、二十世纪的客观各种环境因素。我们且不论当时西方入侵、经济转型等的社会因素,单是19世纪摄影技术的发明,则是一个无论东西方的肖像画都无可避免的转折点。它的发明,打破了肖像的纪实功能,艺术家不能再以“再现具象”而作为根本,而只能从创作根本目的和表达手法等等上作出改变。西方的画家这时转而从肖像中更多的发掘自我、表现自我,如弗罗伊德、如培根,他们的肖像作品无论对像是何人,观者都似乎都能从画中窥探到属于艺术家自身的形象和内在;而中国传统画家此时面对的,则是随着社会与时代种种急剧变化而为艺术带来的根本改变。
迈入当代的肖像画
建国初期,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肖像画被赋予了沉重的意识形态使命,有着独特的艺术语境。肖像画的高度统一体现在这些作品当中无论是所选取的人物对象,或是画面的节奏背景、色调构图等,都成了某种“约定俗成”的模式,彼时的肖像画,俨然是政治符号的载体。然而,改革开放以后的,随着大量西方的美学观念和影像观念涌入,西方美学大大刺激着中国艺术的发展。由于传统中西视觉文化艺术存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在对待肖像画而言,东西方伏关于美感本质的思考亦不相同,所以这似乎也划分了中国艺术中“当代”和“传统”的视觉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在过去当代艺术蓬勃发展的30年中,当西方的审美标准介入中国的艺术创作时,传统的审美标准也渐渐褪色。
八十年代起,中国当代艺术以蓬勃得惊人的趋势发展,从“星星画会”、“现实主义”、“伤痕艺术”、“乡土热”、“新生代”、“政治波普”、“卡通一代”、“女性主义”、“玩世主义”等思潮和流派的出现,足可见证在这短短30年间,中国飞速地在学习甚至模仿的过程中经历了西方当代艺术数百年的历程。曾经,肖像画试图在现实主义的叙事框架内努力地贴近客观对象。但跨入90年代,西方现代艺术的价值观,驱使当代艺术家都不约而同地反叛传统,放弃了肖像写实的原则,将创作的视角更多地放在当代国人的精神与生活状态上,画面表现方式日益多元,观念和主题也显得个性和多样。
这个时代也为肖像画造就了一种“内容和精神上的变化”——现代化的题材中,作品更迈向个人性的表现思维或者是日常的生活记录又或是借助画面语言投射出的不安、躁动的感受,于是作品逐渐出现了传统古典美学中没有的世俗内容,例如中国的新文人画中出现的裸体仕女、或偏向西方艺术审美的扭曲、分离、变和具符号性的人物等等。此时的肖像已经不是反映肖像的本身,更多的是去反映一件事、或透过肖像去反映一种状态,肖像画中的着力点或许不再是描绘人物的本身,而是人物所指向的那种存在。其中充斥着独特的艺术符号——呆滞冷漠的神情、夸张的大笑,一个个彰显个人的符号和图像挪用的政治波普等几乎主宰了90年代的肖像画。传统的肖像画中所内涵无形的教化、道德宣扬与文人气质,似乎与在代艺术的语境早已流于无形,西方艺术的崛起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甚至造成了艺术文化发展的失衡和审美体系上的失语。
肖像的新变化
随着岁月的变迁,在全球化的进程里,经济发展所带动了各种新媒介、讯息膨胀泛滥,人们的观点和视野在不断地开阔和被改变。若说过去的中国文人艺术,是艺术家与自然的关系;那当代的中国艺术家,面对的则是人性与世界的关系。肖像的背后,往往是人的精神。但在当下这个图像泛滥的时代,制图技术越益逼真的时候,人们越易倾向关注的只是事物的形象而非本质。经过90年代肖像的蓬勃,有人质疑当下的肖像画有意地逃避写实具象,但却也不再具有深度和内涵,而反而是可悲地退回到了符号学的阶段。同样的,在西方审美的话语权下,作品中也似乎缺失了一种在地的人文关怀。此时,肖像画这个传统的命题需面临的是一次对自身定位、创作对象的重新探索。
眼观当下,若论对人的生活产生最大影响的,莫过于是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在这个信息爆炸、图像泛滥的时代,网络的便捷让一个按键就能成为获取信息及图像记录的管道。这促就了各类装置艺术、新媒体艺术的出现,它们冲击着传统的架上艺术但也令艺术家的创作跳跃出传统的架上绘画的界限。不过,科技的最大影响之一还在于它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不再仅仅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实体而存在。当下,人不仅生存与现实世界中,甚至是在科技架构的“虚幻空间”里也存在着被赋予了特定身份的“我们”。在这样的情况里,人的精神和肉体就如可分裂的一样——譬如日常生活中,当我们面对网络世界、运用各式各样通信软件的时候,我们的思辨过程、我们某一瞬间的内心感想,都能通过各种管道在网络的虚空间被人所知。而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那些代表着“我们”的肖像更是四处皆是,我们赋予这些肖像多重的含义,包括身份的判断、性格的特征,精神的承载。从这个角度说,肖像犹变成了不在场的描绘对象的代言。
这是时代所造就的变化,诸如当代这种科技对于人的相互作用的状态是传统肖像画时代所无法体现和作出表述的,在观念、科技的变迁中,肖像画的发展也应有更多的思考维度、探寻更多的可能性。诚然,艺术作品不一定是要受“反映论”的影响,判断一件作品的好坏并不见得过多分析作品背后的含义。有的作品,创作中,画家赋予了作品中的人物一种重新读解或情感,通过肖像描绘出一代人在特定的时期的思考或心理或状态,捕捉人性转瞬即逝的瞬间,关注表现了肖像本体的生活痕迹反而能让观者产生共鸣而发现画面背后内在性的思考。
结语:“人,肖像永恒的主题”
是次展览选择以“再肖像”为主题,而“再”字如何在肖像题材中体现,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议题。肖像画在中国而言,存在它自身独特的文化历史意涵——它曾经作为彰显道德规范的媒介、曾是民间生活、身份的一种记录或单纯地作为对个人的怀缅。但时移世易,当下,肖像画的创作除了对象依旧是人物以外,几乎没有了界限,所描绘的对象表达形式多样,可写实、可抽象、可写意、可模糊,甚至可没有五官。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进入美术馆仿佛走进思想迷宫,却没有一本关于艺术的“十万个为什么”可以为他们解释这些变得不太“肖像”的肖像画所表达的内在,曾经“可识别”的肖像画似乎被捧上了无法意会的高台,就如有的是画面一片虚无而有的肖像画却是只有下半身。虽然,诠释被认为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艺术评论也不应去论说作品背后的意义,但它至少应该叙述的是艺术如何成为这样子,而让观众有全方位解读的可能性。[8] 谁也无法否认,肖像创作上的思考和创新是必要的,即使是群众表示难以理解的作品这也是艺术家的一个反思过程。只是,若过于追求呈现画面表像的“特殊性”、太过拘泥在表现方式的创新,则反而容易忽略了“人”这一个真正描绘的对象。
事实上,在众多关于肖像画发展归途的议论中,最后的侧重点都不一而同地落在了“人”的身上。无可否认,人永远是肖像画的主题,但“人”却不是亘古不变的,这一肖像画描绘的主体必然地会跟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肖像的创作注定是要顺应其描绘的主体的变化而作出回应和思考。 从上述肖像画的发展历程也可看出,无论是其内在曾经的“成教化”或“显个性”、无论是创作的观念形态、媒材样式或是风格语言,它都需要跟随着“人”去不断重新定位自身在新的文化与社会中的存在意义。如今的肖像画早已不再是过去简单的再现,也并非执泥于教化人伦或自省,而社会的审美需求也发生了改变,如此一来,艺术家在创作中更需揉入对“人”这主体的更深入认识和理解,了解“人”背后的时代发展、需求、生存现实等等,从肖像画中传递出思考的力量,塑造能让观者触发共鸣、属于当代人的形象,这也是“再肖像”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