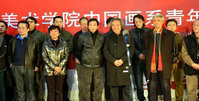隋建国
99艺术网:您2006年之后的作品,我看到您有一个概括:复仇与存在。“复仇”指向自己以前的作品,“存在”是对新的问题的关注,如果说“复仇”的话,怎样来解释这个针对性?
隋建国:也不是说“复仇”,就是说我每一次选择一种方法的时候,总会丢掉一些东西,然后我会慢慢寻找机会把丢掉的东西找回来,但找回来的同时又丢掉了另外的东西,那就再想办法过几年把它找回来。算不了“复仇”,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又报了一仇。
99艺术网:这个再找回来的东西肯定跟您新关注的东西是有关系的。
隋建国:对。

隋建国《地罣》
99艺术网:比如说《我的体重石》。
隋建国:这个其实不算是典型,我1989年后第一次真正进入当代艺术就做了《结构系列》,《地罣》、《殛》这些东西,这部分作品大概持续了6、7年时间,它确立了我在当代艺术圈里面的地位和面貌,但同时又留下了一个遗憾,我在学院里面当老师,我天天教学生,大多时候是教写实雕塑,我的遗憾就是我没法用写实雕塑的语言系统来表达我的情感,就好像今天学京剧的人也不能用自己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情感一样,他只能利用京剧本身的曲牌,只能借古人的方法来自我表达,当然这个社会多数人还是能理解这套表达。但是当我想用我自己的方法来表达自我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学院写实的方法放弃了?放弃的同时我又不能放弃学院老师的身份。后来我想总得找到一个办法去应对这个东西,整个从1997年一直到2004年我找到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其实算比较波普的方法,找到一个形象、一个对象把它强化,甚至强化到一个符号的强度。因为它有成为符号的这种能量,别人会把它当做一个社会文化符号来接受,它自然就在艺术这个场域里面发生了作用。我觉得这算是报了一仇。我把艺术家抛弃掉,让观众自己不自觉地进入作品进行对话,不让我自己的情绪影响到观众,为了达到这一点,我甚至整个作品基本上都不用自己动手,让学生和助手来做,甚至我会跟别人合作,有时候我会借别人的作品放到展览里去做我的作品,这时候“我”其实不重要,只要这个作品本身有成为符号的可能性就行。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作为雕塑家退出作品,这种退出产生了新的工作方法,但它同时也留下了遗憾,就是雕塑家总想在作品里面留下自己的东西,那么我留不下,我也没法留,如果留就打破了规则,一直到2008年我才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就是让我的痕迹最纯粹的留在作品里面,但是什么也不表达,我就闭着眼来捏一块泥,这个痕迹是最纯粹的。一直到现在我还在延续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方法里面有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在报了《中山装》的仇的同时,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方法。

隋建国《衣钵》
99艺术网:这个方法是让“身体”在起作用。
隋建国:对,我现在也不一定闭眼睛,我们聊着天也可以做,无意识地去工作,作品不是我用脑子创作出来的,是我的“身体”自己创作出来的。
99艺术网:这个方法除了针对以前创作中遗留下来的遗憾,还有什么动因?跟雕塑的根本问题是否有关?因为你的“身体”成了一个核心。
隋建国:我的动因就是一定要找一个方法把我的痕迹留在雕塑上,而且这个痕迹应该是主要的东西。《盲人肖像》是帮我实现了这个,但随着我对这个方法的继续探索,我发现它其实有更深的含义。它实现了艺术家原始性的、原发性的创造。柏拉图有一个“山洞”理论,就是作为人你是看不透这个世界的,就像一个人在山洞里面,背后是这个世界的存在,但人所能看到的就是背后绝对存在的光芒照在墙上的影子,这个影子就是周围的现实世界,每一个现实物体都是不完美的,因为它不是绝对存在的,就像我们看到的自然的或者人工的所有的圆都是有缺陷的,纯粹的圆只是在理念里面。所以艺术家的工作其实产生的是影子的影子。当然后来出现了艺术家的不满足,想直接去再现这个“理念”的存在,希望像数学、音乐一样纯粹,所以后来出现了抽象艺术,它的驱动还是再现。
我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说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系,中国人不太善于像柏拉图那样逻辑地思考,为这个世界设定一套规则,我想回到先秦去看看中国人是怎么想的,对世界是怎么看的。我的理解就是虽然中国的儒家也是说得天花乱坠,但到了王阳明就慢慢趋向清晰,我觉得是因为吸取了很多佛教的东西,整个印度文化是长于逻辑的,这导致了中国的理学的出现。它把“心”作为一个核心理念,它指的既不是脑子,也不是纯粹的身体,而是合一的东西,它没有把灵与肉分开。这样来看,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变了,就不是先有“椅子”的理念才有作为实体的“椅子”,然后才有可能产生其他的图像等等,我看“椅子”的产生是由于人的身体的构造产生了对“椅子”这种工具的需求,在这里面“身体”是最重要的角色,这个身体不是纯粹的肉体,是跟脑子、灵魂不分开的整体。其实它是否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倒不重要,我觉得这是整个人类都应该有的思维。“身体”是在概念之先的,当我用眼睛去看、去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永远做不好,你总想这儿再加一点,那儿再减一点,总觉得它不完美。当你在无意识的状态中去做的时候,怎么做都是对的,不是眼睛,也不是我受过的训练和知识,而是“心”和“身体”让作品成立。
99艺术网:“身体”的概念,我觉得它指向的是人的“自由感”,现代性以来对人的的探求存在一个悖论:越自由越不自由,越想建立主体就越丧失主体。
隋建国:自由,或者说是创造。我觉得“身体”或者是人本身是有创造性的。如果说今天的人没有创造性可能是我们的教育、过多的知识限制了人的创造性。
99艺术网:所以在您的雕塑里面,在“身体”之外还有两个概念:空间和时间。这是两个先验的概念,跟身体之间我不知道存在什么关联?
隋建国:空间、时间是这样的,空间时间的存在确实是先于主体的“我”的存在,所以对这种先验的存在你不得不产生敬畏,但是时间和空间又是人把握世界的一个方式,当你出生的时候,把握时间的方式已经随着遗传基因被输入到了你的系统里去了,这就意味着你的身体本身是可以认识时间、空间的,只不过是我们的知识会有意识地让时间和空间成为我们身体里的对象。其实我觉得时间、空间可能根本不是一个对象,它就是身体存在的一个证明。

隋建国《盲人肖像》
99艺术网:这种创作方式跟雕塑之间是什么关系?
隋建国:从《盲人肖像》以后我就不限制什么方法,无意识地“捏”,就是让自己做错,结果就做对。但是要通过雕塑的方法把它确认下来,我的手的尺度是有限的,所谓通过雕塑确认下来就是把这团泥用精确雕塑或者是雕塑写生的方法把它放大,先放大成一米,然后再放大成三米,要把每一个空间关系、形体关系做对,甚至我留在表面的肌理、痕迹、手纹都要呈现出来。放大以后别人自然就觉得这是一个雕塑,不然会认为这是谁捏的一块泥。
我觉得这里面要重新考虑“身体”存在的方式,甚至“身体”工作的方式。这样的创作过程是我的“身体”在工作,当然我也没有完全排除我的“脑子”,我的“脑子”是在选择,但我选择的这个方法本身是在跟整个艺术系统对话。我记得我在深圳做讲座讲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有一个60多岁的热爱艺术创作的老人站起来问我一个问题:你的作品我有的时候很喜欢,你说的也感觉很对,但是我怎么觉得你这样做就像一只鸡用爪子刨土、一个猫用爪子挖洞?我说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我的手由于它的关节、肌肉系统只能这样做,这是我的肉体本身决定的,但是我“选择”这样做,就证明了我是一个人。他说“总之我觉得人是应该要靠脑子来工作的”,我说我也有脑子,但我的脑子在手后面,不在手前面。

隋建国《时间的形状》
99艺术网: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脑子的因素还是不能放,它构成对身体的一个限度,就是身体探索的自由、无限是有限度的、有困难的,不然这个“无限”就变得……
隋建国: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有限的,就像杜尚当时发现了“现成品”,他马上就知道这个东西必须是有限的,他也就选了20件作品之后就停了。我觉得我让“身体”自己工作的方法,只是在针对整个艺术系统越来越强调脑子的参与、越来越放弃身体的时候,我强调一下,它就会产生作用。但它是不是要无边无际的强调下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99艺术网:您觉得会吗?
隋建国:我觉得我要先把这一段工作告一段落看看。
99艺术网:我觉得以您这几次复仇以及发现的新思路,可能还会往前推。您现在的创作中有我觉得一点很明确,就是对身体的确认,我认为它是对人的“主体性”、“自由感”的一个追寻,类似于抽象回归到纯粹的语言层面或者杜尚的“现成品”方式,其实也就是对现代性的推进及反思过程。但是人的主体毕竟是有限的,相对于时间、空间,相对于柏拉图的理念或者上帝(诸如此类),那么如何回答人的“有限”的“可能性”是一个新的课题。
隋建国:可能会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展开,我要先把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证明一下,做成雕塑。假如说对人的“身体”的确认最后变成了“无限”,这里面还有问题,还会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我觉得就像禅宗的顿悟一样,不是顿悟一次就完事了,你要不停地进入不同的层面。其实我还是基于雕塑的出发点来面对这个问题,要谈“身体”的话,整个观念艺术以来对“身体”的强调已经多的不能再多了,但是作为行为或者是表演的“身体”,它是自身对象化了,它没有“对象”。它其实是更趋近于戏剧表演那些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它大多时候要通过摄影、录像记录下来。那从雕塑出发来考虑“身体”的话,其实就是身体跟其他物体的接触产生的创造性,你要先用“身体”进入,你先接触了,你有了体验,然后才会产生意识,我觉得这是雕塑家的一个基础和出发点。(赵成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