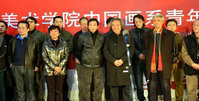宋庄美术馆
宋庄,中国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区。1993年,以方力钧为代表的第一批艺术家开始入住宋庄,此后历经近20年的发展,宋庄艺术家的确切人数已无从考证。小堡村目前已成为整个宋庄艺术区的中心,这里有最多的艺术家、最有名的艺术家、最大的工作室和最贵的房产。艺术家为这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据统计,小堡村每年可得租房收益800万元,带动消费资金流约2,000万元,作品成交2亿元,安置就业和家政服务150万元。在某种程度上,宋庄20年来的变化也折射出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更是艺术家工作室变迁的缩影。
与方力钧一样,有着“中国当代艺术教父”之称的栗宪庭和艺术家高慧君也是最早一批入住宋庄的人,他们是宋庄20年发展变化的亲历者。
来宋庄以前,栗宪庭还有公职在身,住在后海近20年,高惠君仍在部队。上世纪90年代初,政府有意取缔圆明园画家村,警察频繁造访艺术家住所,画家们终于决定离开圆明园,纷纷找地方搬家。栗宪庭希望搬到宋庄仅仅出于想要安静下来住农家小院的冲动,高惠君则希望走出部队寻找自由,二人同当时居住在圆明园的方力钧、丁方、刘炜等人经过考察,最后找到了小堡村,成为了第一批入驻宋庄的艺术家,开始了宋庄艺术区历史的书写。
如今,圆明园画家村早已荡然无存,而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这里曾是流浪在北京的画家聚居地。毕业于专业院校的一批艺术家主动放弃国家分配,以“盲流”身份寄住在圆明园娄斗桥一带,自由创作、生活,成为当时一大文化象征。1992年以后,圆明园开始变得很热闹,例如方力钧,几乎每隔15分钟就被警察敲一次门,画家们常常把门反锁起来再跳进屋里画画,大家纷纷升起离开的念头。艺术家的自由使得画家村成为治安监控的重点,最终被政府强制取缔。
入驻小堡村
1993年起,栗宪庭开始和方力钧、高惠君等人找地方搬家。高惠君当时还在部队,不方便外出,就将选址、选房的事全权委托给方力钧几人。栗宪庭参与了选址过程,找遍了北京所有郊区,最后来到宋庄。宋庄是当时离北京最近的郊区,公共汽车可以直达 ,虽然只有从国贸桥出发的一条公车线路,这在当时已经可以称得上交通便利了。栗宪庭回忆第一次来宋庄时天气很冷,村子都破破落落,三分之一的房子都已倒塌。那时很多村民都进城了,放眼望去,村里一个沙丘上几座房子,又一个沙丘上几座房子,坑下还有几座房子,简直像一片荒漠。
较之当年,宋庄已生巨大变化,尤其是公共交通,几条公交线路来往于国贸和宋庄之间。20年前要来一趟小堡村,需要到国贸乘坐322路公车到东关或是北苑,然后打车(通常打不到)或是坐“三蹦子”;要么就坐从北苑到燕郊的长途车,长途车路过小堡村,不过四个半小时才发一趟。要是想从小堡村回城里就更麻烦了,高惠君说自己有时就沿路边走边拦车,常常一走就是两个小时,索性直接到东关坐322。据说曾经有两个客人从方力钧家出来一直等不到车,最后跟了辆拉煤的车才回到城里。
村子里空闲的房子虽然简陋、破旧,前后院的布局和低廉的价格却引了画家。虽说当时农民之间互相买卖房屋只有三千多元的价格,卖给画家们却一道道附加,价钱翻了三倍之多。当时,刘炜买了两个院子,前院送给了栗宪庭,后院自己住。栗宪庭把房子收拾到半截就没钱了,又必须要去美国,就把剩下的摊子交给方力钧打理。几年间,院子一直借给别的画家住,栗宪庭只是偶尔过去住一两天,其余时间都在城里或国外。
据高惠君回忆,当年买农村房大家都没有经验,胆子小,没人敢用真名,第一批入驻宋庄的6名艺术家都是用别人的名字买房,每家付1,500元的保险费(也相当于手续费或介绍费)给对方。直到后面来的人才渐渐开始写自己的名字买房,第一批到了1997、98年前后才把名字改回来。
直到2000年初,栗宪庭开始准备迎接女儿的降生,城里的房子太小,根本住不下,一家人这才搬到宋庄,对房子重新做了装修和改造,栗家女儿就是在宋庄小堡村那间院子里出生的。当时栗宪庭也不想再参与热门话题,希望沉寂下来,把20多年来的经历回忆、反思一下。结果,由于宋庄的人越聚越多,最终成为新闻热点时,很多画家又找到栗宪庭,每天拉着他去看工作室,根本不得喘息、不能安静下来。栗宪庭这时才觉得也只能再出来做事,于是他开始思考艺术区的生态问题,开始和地方政府接触。政府也找到栗宪庭一同规划这块地并提出创作生态问题。
由于高校扩招,越来越多学生流落在社会上,能够找到工作的人很少,大多还是改行了。也有一些热爱艺术、专心艺术的人越来没有出路,他们便聚集在各个城市的艺术区域,如重庆的黄桷坪,成都的蓝顶。每个城市大概都有这样的地方,但宋庄是最早、最大的。
与农民的磨合
起初,人们对自由艺术家没有了解,一些官员也采取拒绝的态度。栗宪庭回忆说:“当时从圆明园来宋庄其实是把警察给带来了,警察跟着这些艺术家、突然闯进来东西。据说当时上面的领导找村书记谈话,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些艺术家撵出北京。村官崔大柏本人在与艺术家接触的过程中发现这些人其实都挺好的,有时候我们还会帮助村里面的建设提提建议,像方力钧他们都会出一些钱,帮村里修路灯什么的。崔大柏就不停找上级,把艺术家们保护下来了。这个举动让我觉得我们改变一个体制是不可能的,但是能够说服一些地方官员,获得他某种程度上的理解和认可,这就形成了一定缓冲。”
宋庄的村民开始对艺术家做的事还不是很能理解,但慢慢都在改变。农民里也有艺术家出来,他们受到艺术家的影响,也开始自己动手工作。例如村里有一个乡镇企业的工人就自己动手用各种铁器拼接,好像60年代的集合主义。平日里,艺术家跟村民的相处中也难免有些磕磕碰碰,有时打起来了,村里管不了,他们就找栗宪庭出面管。栗宪庭有过插队经历,对农民比较了解。“其实农民只要你尊重他,他觉得你看得起他就够了。我的邻居,所有过年过节都送东西,然后他们也送给我东西,这样关系就搞得很好。我跟每个艺术家都说,跟农民邻居一定要搞好关系。其实很好搞,比如说你开车,农民站在你车前就不走,你下来很客气,他就很高兴,马上就回家了。千万不要呛呛起来,这不好。”
与政府的合作
2004年,栗宪庭建议宋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做艺术园区。当时宋庄交给栗宪庭400亩地规划:盖美术馆、化工区、艺术加工区。由于宋庄几个很有名的艺术家画卖得不错,招来很多人聚集。宋庄有淘金的可能性,但发展是很困难的。栗宪庭想做的是一个学术交流平台——美术馆、画廊区。宋庄美术馆建成于2006年,第一个展览就吸引了各路人前来观看,人们都要来见识见识世界上行政级别最低的美术馆——村级美术馆。宋庄美术馆盖的时候北京市两次下令指定要拆除。其间,栗宪庭接待过一位市长,谈了艺术生毕业后的出路问题:“这个出路就像一滩水,你要怎么流动出去,怎么有新鲜的水补进来?现在美术馆是在替社会在解决问题。”此时的栗宪庭角色已发生变化,他称自己是个乡绅,帮地方政府调节农民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他还说服了一些人来盖画廊,周围是艺术家的工作室。盖得起房子的人来建大型工作室,同时还改造了几个旧工厂。当时改造了一个饲料厂,首先用来给女艺术家建工作室,名嫘苑,只给女艺术家住,保障安全。这之后盖的工作室基本都参照这样的模式,即建筑改造模式。
从艺术到地产
在宋庄小堡村,几乎每一家都有房子租给艺术家。艺术家的入驻促成了新型经济结构的产生,解决了农民的生活问题。那么谁来解决艺术家的生存问题?栗宪庭跟地方政府沟通,希望建起画廊区,号召画廊进驻宋庄,希望宋庄美术馆与其他民营美术馆能够有一些学术交流,在宋庄建起利于创作和交流的生态环境,甚至是一个艺术市场。但是在后来的发展当中,越来越多人借发展艺术之名搞地产,这就是栗宪庭曾在文章中提出的“私地产”。
“房地产是国家挂牌的,小产权是集体的商品开发,私地产的概念是说比如一个领导或者一个商人,以艺术家的名义买了一块地,盖了很多工作室出租,这实际上是地产性质,拿的是中间房租的费用。这使得宋庄的房价不断增长,越来越多艺术区都在趋向于这种地产形式。”
在2009年政府某艺术节上,栗宪庭在演讲中提出了宋庄艺术区的三个问题,即硬件、软件问题,当代艺术和其他艺术的关系问题以及艺术家和日常生态问题。宋庄的开发逐渐成为地产业,私人美术馆、画廊、工作室足够多,但艺术管理落后。很多画廊空着,如上上美术馆,一年到头也没有几个展览。宋庄火了,尤其2008年《三联周刊》报道以后,吸引了大批艺术家、官员前来考察。栗宪庭不停接待各地市委、市长,大家都看准艺术区带来的经济效应,希望建立起同样模式的艺术区。然而艺术火了,三教九流的人就都进来了,卖石头的,画行画、卖字画的等等。甚至还有学院里的教授也来建工作室,如此的发展实际违背了栗宪庭的初衷,“这些人是在跟自由艺术家、毕了业没工作又热爱艺术的年轻人抢饭碗!”宋庄的小产权房盖了很多,地产商的加入导致房价上涨,最后反倒是艺术家进不来了。文化产业变成借文化搞地产。一些地被封了,地产商就借文化产业之名申请解禁。栗宪庭认为当下的美术馆热实际只是新一轮的地产热,与艺术和文化都没有关系。
小产权房被查封一事曾闹得沸沸扬扬,高惠君认为小产权房针对的不是地皮也不是艺术区而是买卖。一座楼从设计在图纸上那天起到施工、建成都没有违法,直到楼盘开市起成了违法建筑。从违法到不违法,价格从20万到400万,楼没有变,只是多了几个公章。这和户籍是一个道理,制度如此。
拆?不拆?
宋庄之外几处艺术家聚居区拆迁风波也让宋庄一些艺术家忐忑不安。有人来找高惠君合计究竟会不会拆?拆了怎么办?高惠君轻描淡写:“他们真要拆我就只能帮着拆”。他认为个体是无力抵抗潮流的,在一个局部上的反抗是没有意义,不反抗也不代表投降。高惠君自己也做了分析,他认为如果真有人来拆房,不论是开发商还是政府,或者是双方联手,非要搞清楚他拆了房准备干什么才能想明白到底会不会拆。假设拆了是要盖商品楼,征文必须是国有出让土地,这不是普通开发商做得到的,需要政府权力介入。而政府希望的是在这里建立艺术区。“他把你拆了,把你搞成一个困难户,一个到处去告状的人,然后他再盖艺术区,这个艺术区他要给谁住?”
又一个798?
宋庄向艺术区发展会不会成为第二个798,第二个艺术观光区?高惠君和栗宪庭都认为这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宋庄只会是一个艺术家聚集区。高慧君解释聚集的概念是既可以有艺术机构,也可以有很多人住,同时有很多艺术家工作室。一些国外艺术机构、学院校区都会慢慢入驻宋庄。
谈到其他国家的艺术区发展,栗宪庭介绍说其实都是相似的模式和处境,艺术家把这个区域带动起来之后繁荣的是其他产业。798的例子跟SOHO是一样的,SOHO在1960年代是很廉价的纺织品仓库,当时的前卫艺术家、极简主义艺术家以低价在SOHO买工作室。慢慢SOHO火了,品牌店就跟着入驻,房价就被抬高了。这样一来艺术家又租不起了,只能往外走,搬到伯克林、到西村去。
栗宪庭认为宋庄很难发展成为798,因为宋庄实在太大了,租不起小堡村的艺术家就去周边更便宜的村庄,那里还不像小堡村有这么多投机商人,房价还能承受。
自由和保障
不论讲到宋庄还是从前的圆明园,栗宪庭都在“艺术区”前上“自由”二字,至于“自由”的含义,栗宪庭开玩笑说,自由是指生活方式自由,不用开会,不用上班,随便可以睡到什么时候。
当年在圆明园艺术区的聚集作为对户籍制度呼应的艺术家们如今在宋庄仍旧因户籍问题为子女上学、个人养老等社会保障欠缺所困扰。在宋庄上学大概要交1万到3万元赞助费,据说,到通县则要10到15万;至于养老更是没有丝毫保障。尽管艺术家为宋庄带来了经济效益,却没有人愿意出一点钱做艺术家养老基金。人们看到的只是谁谁的作品卖了怎样的大价钱,却不知道那只是少数中的少数。
冬季取暖一直是宋庄的难题。曾有一部分人靠烧锅炉取暖,今年起宋庄又开始了天然气管道建设,锅炉不能再烧了,天然气的建设费也摊在艺术家头上,让人费解。
高惠君说自己的工作室因为地基问题想通天然气也通不上,现在锅炉也不能烧,冬天就只能去南方,等春暖花开的季节再回来。栗宪庭则解释说:“因为这里的地不是正规国家建设开发的。正规开发当然是商家出这个钱,算基建三通一平,但是那个房价又不一样。我们折腾了很久,一直在斗争,只希望村里和天然气开发商财务透明,希望他们合理,希望知道哪些钱是我们应该付出的。”
宋庄的官司
2007年,宋庄有过一场官司,里面有个传奇人物叫王笠泽,他在法制报做过美编,后来又去学习法律,成为主编。王笠泽在宋庄画画待了快十年,宋庄的艺术家火了以后,农民就开始告艺术家,想把卖出去的房子再收回来,当时被告的王笠泽就是第一例,从此他便开始研究此类案例。当时,艺术家李玉兰的官司轰动了法律界,成为当年的十大案件之一。王笠泽去为李玉兰当了辩护律师,打赢了官司,在法律界名声鹊起,写了一本书《宋庄房讼纪实》,栗宪庭为书作序《梦魇宋庄》。
“艺术家和农民成为一对被告和原告,完全源于一个假象,即在于2000年以来艺术市场的活跃和少量艺术家的富裕,它成为一个貌似经济关系的不平衡——“画家发了”造成的,既然“画家发了”,当年卖房子的农民觉得“亏”了,就把艺术家告上法庭,要求索回当年卖给艺术家的房子。事实上,只有极少数艺术家在艺术市场获得成功,而这种“成功”却变成了一种“神话”,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到艺术区聚集,其结果是大多数的艺术家并没有获得“成功”,反而引发了宋庄和所有艺术区房租的一路飙升。就目前宋庄艺术区农民和艺术家所得到的利益看,农民作为房东的收入稳定并逐年增加,而绝大多数艺术家生活得非常艰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承受着精神压抑和生活窘迫的双重压力。”(节选自《梦魇宋庄》)
栗宪庭回忆说:“此后又有一大批艺术家被告,包括方力钧。我们最后争取到的是可以要回去,但当时买1万块钱,改造花了九万,再加上区位补偿,一个房子到了20多万甚至50多万。农民有能力就买回去,但一般没有能力买,也没有能力搁置。将来如果拆迁,有些区位补偿和原来的地主有一个分红比例,这也算是保护了把艺术家的利益。”
宋庄的浮躁和艰难
宋庄的艺术家流动性非常大,有一批人是常驻的,还有一些零零星星待上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就走人的。这些艺术家以为来到宋庄就能卖画,结果待了半年了一张画没有卖,满怀着怨气就走了。还有些艺术家不卖画是因为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有别的谋生渠道,比如画画广告或是搞设计。
“宋庄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很浮躁的,是中国北京最烂的艺术区,什么烂的艺术家都有。但另一方面,有一大批真正热爱艺术、做得很不错的艺术家沉在下面。宋庄的艺术家类别是最丰富的,除了画家,独立电影人、音乐家、诗人、摄影师,甚至建筑师这里都有。艺术就是艺术,艺术创造的是艺术,但艺术在商品社会创造出来的是商品。商品、经济是另外一个行当,我们不懂。如果它的发生是按照正常渠道走的,艺术家还是可以找到出路,这是一种生活来源。在中国没有赞助艺术的机构,像西方、像日本、韩国都是有赞助艺术家的基金会,中国没有。那你靠什么,就靠多多少少能卖掉一幅画。所以艺术家一定得用副业来养艺术。在国外看到的年轻艺术家生活也很艰难,他们基本都打工,没有年轻艺术家能靠卖画活着的,大部分都要打工。”(沈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