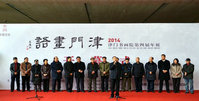我是1992年正式“北漂”的,其实在此前几年我一直来来往往在北京与山西之间,为那个年月的中国梦——文学梦在奔波。那几年结识过的文学青年,如今很多都是文坛的大腕了,但是那个时候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那时真的是只有梦和追逐。
此前,我已经在《北京文学》(1988年第5期)、《诗刊》(刊授版《未名诗人》)等刊发过一些诗歌作品,而且正在与诗友苏志强编一套《女娲诗丛》,虽说后来一直没有正式出版,但是我们在《诗刊》买版面发了几次“女娲组诗”,都是来自底层诗友的诗歌。那时,在北京“发诗”的民间组织有好几个,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很有改革开放初期的特色,都在挖空心思打擦边球。
有一次,丁慨然老师给我说有个四川来的诗人要到他那里当编辑,还没有住处,问能不能与我合住,我说可以,没几天就来了,那时我住在北京五棵松附近的青塔村,那时的青塔村还是一片民房,不像现在乌压压一片楼房。
那个跟我合住的四川诗人是现在的美术类期刊《荣宝斋》的常务副主编徐鼎一,那时他还不叫徐鼎一,而叫徐亢,是四川万县人。徐亢之前,在丁慨然那做编辑的是俞心焦,就是现在的俞心樵,俞心樵是当时小有名气的诗人。
那年冬天,丁慨然组织了一次诗歌笔会,在玉泉路一个招待所。因为徐亢在丁慨然那当编辑,所以就约我那天也去,对他们的诗歌笔会什么内容我也不清楚,但是我很愿意去,答应第二天跟他一起去。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郭沫若也去参加这个笔会,梦里的郭沫若夹一个皮包直接走到主席台上,说看人家(苏联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开会前这几分钟就能写出一首诗。
早上起来,我还纳闷怎么会梦见郭沫若?因为那时我们的青年诗人都在追逐朦胧诗,早都不提郭沫若了,觉得他已经老土了。但就是梦见他了,真的很纳闷,我还给徐亢说,怎么会梦见他?还给他讲了梦里的细节。徐亢用他的招牌微笑回应了我,也没觉得如何。
没想到,那天一到会场,当时在《工人日报》当编辑的著名诗人王恩宇也到会,他讲话时提到当天是郭沫若诞辰的日子,我当时就愣了,还傻乎乎的站起来说我昨晚梦见郭沫若了,没准到会的诗人都以为我是瞎说的呢。那天参会的著名诗人有那么七八个,都是耳熟能详的,多是中年诗人,只有丁慨然的父亲丁力是真正的老诗人。因为老参加他们活动,跟丁力老先生接触较多,后来就研究他的作品,专门给他写过一篇评论,忘了发表在哪了。
其实,那天俞心焦也去了,似乎晚了一点。但那天俞心焦在开幕式后念了一篇关于诗人的稿件,其中一句提到希腊诗人荷马我还记得,因为与俞心焦第一次见面,才发现他一只眼睛有问题。后来吃完饭后,我就跟俞心焦走了,他说要到中科院还是社科院的研究生院找个熟人,我们就一起去了,地点就在玉泉路附近,记得一进大门就看见一座郭沫若的巨型雕塑。
其实说来我与郭沫若还是很有缘的,尽管现在很多人在骂他。记得在上高中时,我喜欢抄书,几乎把我们班里所有同学课桌里的课外书里的诗歌都抄了个遍,其中就抄过郭沫若早期所有的诗歌。后来跟黄纪苏熟后,知道他父亲曾是郭沫若的学术秘书,为此我还写了篇《黄纪苏家事一二三》。好玩的是,有一次偶然被一个朋友带到一个地方,进去一看是郭沫若诞辰120周年的书画展,总觉得与他有点缘分。
后来跟俞心焦从那出来后,就跟他跑到北京大学,因为没工作,所以很自由,想去哪就去哪。跟俞心焦在北大一个教师宿舍聊了会天,都是他的熟人。当天晚上就混到学生宿舍住了一夜,记得到北大的食堂吃了顿饭,是肉包子,至今还觉得那味道真香。
第二天,从北大出来,我们就跑到圆明园的福缘门村——就是后来的圆明园画家村,在几个画家的工作室逛了一天,还混了顿饭吃,那时我对画家不是很感兴趣,所以很多画家的名字没记住,只记得贵州诗人王强的名字,但是很多工作室的画我还记得,给我印象很深刻。后来认识上海画家王秋人,我没问过他1992年的冬天他到没到那。
那天吃完饭出来,俞心焦要在那租间房子,就跟他跑了几家看房子,记得当时他就交了几百元押金。我那时穷的很,几百元对我已经是天文数字了,不会像他那么阔气。也很羡慕那些画家能自己租房子天天画自己的画。
我这个人比较笨,很晚才开悟,一直不知道如何在北京找生活,只会写几行诗,因为阅历不丰富、人也胆小,所以想写小说一直也没写好,好在一门心思天天读书,笔耕不停。
后来,徐亢在丁慨然那边的办公室附近找到住处,我也在没有任何生活费、交不起房租的情况下,投奔到旧鼓楼大街一个地下室旅馆的李阿姨处,他们收留了我。后来我在那个地下室旅馆先后接待了不少于上千人次的诗人、画家、作家、编剧等等。大多数的人名记不住。虽说那时我经常身无分文,但一直以中国诗歌教育研究会这个我自立门户非法组织的名义在活动。记得那时从也是住在前马厂的一个安徽青年画家那里借过一本西方画论的书,开始慢慢学着写美术评论。我在北京经常因为交不起房租,而一再搬家,经常是把东西寄存在别人那,而且因为没钱常不好意思回去拿东西,几千本藏书因此丢失,但那本借朋友的画论却阴差阳错的还保存着。那时徐亢也开始学画画,好多年后知道俞心焦也在画画。
一晃二十多年就过去了,现在经常听一些画家在回忆圆明园画家村的旧事,今天我也记下那年冬天寻访圆明园画家村的一瞥,顺便也致下我们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