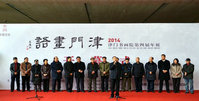具有价值判断的独立策展人?艺术机构中专人专岗的职业策展人?撺掇一批作品、找个地方挂起来就能开幕的“策展人”?在任何人都能成为策展人的国内环境中,“策展人”的概念逐渐被消解,这个行业在今天似乎已经没有了门槛。
尽管各式各样的人充斥着这个行业,尽管今天当我们谈“策展人”的时候,谈的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策展人,但在中国,还有这样一批策展人,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独立策展人”,却是当下策展行业中的主流核心,这批中流砥柱的策展人兼着批评家的身份,带着对当代艺术的批评和研究,将策划展览视为个人作品,他们的价值判断值得市场关注,他们的前瞻或成下一个趋势。
为“策展人”做足准备
盛葳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考入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史系那年,川美美术史系还没有大四,刚有三届的美术史系到处都是激情。在批评家、策展人岛子、王林、王小箭等老师围绕的学习环境中,川美的美术史系主要侧重当代艺术研究。盛葳笑谈:“当时老师加学生才50人,每天晚上大家一起在酒吧吵架,学术争论很激烈。”自然,这种热烈的气氛激发了年轻人最初、也最坚定的兴趣,从那时候起,盛葳知道自己以后一定要从事当代艺术相关的工作。
当同学正为老师布置的策划作业凑合对付时,大一的盛葳很认真地上街为自己摇滚乐唱片封面的展览拉赞助,尽管经验不足的“策展人”最后在花掉1000块赞助后还赔了钱,但人生第一个展览或许让盛葳看到自己兴趣变成现实的可能。
学习过程中,意识到当代艺术需要调动很多领域和其他行业的知识,盛葳在大学毕业后考入了清华大学艺术批评历史与理论专业,不过,在清华读书期间,盛葳出入最多的并不是美术学院,“那时候更多去建筑和历史系,还有社会学系,因为可以学到很多其他的东西。”
硕士学位对一心想进行当代艺术研究的盛葳来说还是不够,在重当代弱传统的川美,和跨领域学习的清华学习过后,盛葳最终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西方现代艺术研究,“因为当时发现想做当代这块,没有美术史的研究很难深入,下一步很难进行。”
“独立策展人”
还是“具有独立精神的策展人”?
和大多数人一样,尽管博士毕业的盛葳看上去已经万事俱备,但他仍然没有走上西方意义上“独立策展人”的路子。不过,无论是从事媒体行业,还是个人学术研究,盛葳倒是一直都致力在当代艺术的研究中。
这总会涉及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为什么中国难有独立策展人?盛葳称:“我一直在做其他事情,但是策展一直都没放弃,职业化策展人是靠策展生活,只要靠策展生活他的展览就会跟利益挂钩,独立策展人并不靠策展生活,是一种思想上独立的价值判断,经济、学术各方面都保持独立。”
靠策展为生,总会在生存和学术坚持中两难。但在盛葳看来,他所理解的“独立策展人”并不是我们单纯以为靠策展为生的人。
“中国不是缺独立策展人,而是缺有独立精神的策展人,而越来越多的独立策展人又在面临一种全球化的批判,全球都在反独立策展人,因为他们觉得独立策展人最后也是一个权力集中的结果,他们对艺术家、作品的选择,甚至还向藏家、美术馆推荐作品,权力过于集中,一个人的判断是否能代表大众?这种论调在今天已经被怀疑,所以很多大型展览采取的都是团队策展的机制。”
在强调独立精神而多过形式上“独立”的时候,身兼数职的身份并没有对盛葳的策展工作带来多大的限制。相反,持乐观态度的盛葳认为,多元身份让策展人的角色更立体,当策展不会成为策展人唯一的生存依靠时,策展人在自己的学术研究前就不会轻易妥协,保持多元性才会对社会和艺术的各个层面保持敏锐的观察,也不会局限在固定的视角中。
展览策划就像一首歌
策展人对一个展览好坏的掌控能占到80%-90%,甚至对策展人而言,从计划到多方统筹才成的一个展览,就是他们的作品。盛葳感慨道:“策展人做的工作跟艺术家还不一样,艺术家只用考虑他自己,但是策展人的工作之一就是考虑观众,一个展览的呈现往往是需要设计的,这种设计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审美,而是展陈逻辑,观众在看的时候或许没法发现一个让人震惊的东西,但在观看过程中,观众的观看是已经被设计的。”
传统的展览方式或是将作品等距挂起来,但对策展人而言,前后逻辑等都是迫切需要考虑的,“整个展览的策划就像一首歌,有前奏有高潮,有起伏跌宕,有结尾,不能像敲木鱼一样。”
在关山月美术馆展出的“在路上·2013”,如果粗略一看或许会以为是一个70后、80后年龄简单划分的展览,但如若细看会发现,即便在选择的同时代艺术家里,也有成就不一,作品新旧不一。
作为策展人之一的盛葳道出背后的策划逻辑:“年龄不是标准,只是一个范围,我们并不试图去总结归纳特点,因为他们之间各有不同。我们只是在归类现象,比如我们有五个主题,像对历史的总结,是带有前瞻性的总结。还有个体性的讨论,比如尹朝阳,比较有代表性的70后艺术家,但展出作品是新作。比如语言批判的,用大直线切割,过往少见而现在成为某种趋势。再比如关于图像,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从语言变成了图像,图像不是在讲述别的故事,而是通过自身来表示。”
从一个展览的好坏或许能窥探策展人能力的高低。作为资源枢纽的策展人,从研究一个展览是否对学术有建构性意义,到如何被实施、选择艺术家和作品、如何组织排序、如何观看,展览策划的方方面面都在考验着他们的能力。
盛葳用经验告诉我们,策展人有的时候像“保姆”,有的时候就是“和事佬”,“展览的策划只是考验策展人专业能力的一部分,只需要一个策展人或策展团队进行前期规划,但是在后期,更多是实际操作,考验的都是策展人的沟通协调能力,有的时候会碰到很多矛盾,学术矛盾、人和人的矛盾,如何解决问题,如何把展览所有相关方协调好,如何维持进程,这些都是问题。”
而在这个权利转移的社会,资本的浓厚兴趣和强势介入,对策展人而言,是一个最好又最坏的时代。尽管学术和商业总被放在两个极端,但事实上,资本的介入对一个需要掌控全局的策展人而言终究是利大于弊的事情。
“一个中型的展览预算就得上百万,做展览的成本在那,但不能为了拿到那些钱而突破自己的原则,在不突破原则的前提下,可以折中。有矛盾的时候不太重要的问题我都会妥协,涉及学术原则的问题不会,有可能就不做这个展览了,其实我们和投资方的关系特别像导演和制片方的关系。”但盛葳也强调,资本的硬推并不能对艺术的发展产生作用,它的作用是临时性的,一段时间过后,历史终究会平衡波澜。
艺术发展的GPS
尽管策展人经常被戏称为“超级奶爸”,但在近几年,资本越来越重视学术的力量时,一些多做学术展览的策展人也经常被形容为“GPS”,他们的学术研究或以著作面世,有的或更适合用展览的方式呈现,大多商业机构会盯着具有学术研究策展人在做什么,他们的判断或许会成为两三年后发展的导向,这也就是策展人一直追求的前瞻性。
在盛葳的研究方向中,美术史中被遗漏或曲解的课题,以及能推动新的艺术趋势的课题是他一直着重关注的点。具有独立精神的策展人,除了让他们策划的展览具有学术前瞻性外,同时强调的还有展览所传递的个人价值判断,也就是批判性。
“批判并不是找一些不好的作品来批判,批判实际上是作出某种价值判断。”盛葳最近一直在关注当下火热的新水墨,但还未对此作出结论,“批判性的展览或许不像拍卖行所做的水墨展览,他们会更注重市场效应,但是我或许会从社会学的角度做,选择的是和市场不一样的作品,或许选择一样的作品但组织方式不一样,会找到不一样的价值地位。展览是对某种现象构成一种新的叙事结构,也许有人觉得新水墨就是新的,也许我觉得新水墨和传统之间构成了某种关系,也许有的展览生拉抢扯说某个艺术家继承了一些传统,但是我觉得没有。”
带有长期学术研究的眼光让盛葳对当下火热的新水墨有自己的判断,在他看来,2012年年初开始的新水墨热,市场的确是它的第一推动力,但它并不意味着没有学术上的可能性,“新水墨以写实为主,经济危机以后,当代艺术市场一直没有恢复,国画市场却在前两年有所回升,所以新水墨的崛起自然跟宏观经济有关,一方面传统国画的藏家能接受写实的、水墨材质的新水墨,一方面当代艺术的藏家在当代艺术低迷的时候觉得新的水墨也可以接受,而且这批人都很年轻,有预期,增值潜力还是很大。”盛葳认为新水墨的发展还未到头,所以还在观察中的他今年没有做任何新水墨的展览,他希望未来这股热潮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能做出一个体现自己学术判断的好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