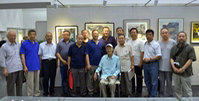-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像眨眼皮一样记录日常的刘小东

30年前,北京电影学院宿舍里,导演王小帅还是个清瘦的少年,平头,白衬衫,脸颊两侧的青春痘清晰可见。30年后,京郊的麻将桌上,少年成了大叔,圆滚滚的脸上笑纹尽显,当年秀逸的模样已随岁月流逝消失。
小溪边光着身子的男学生,货车斗篷里憨笑的农民工,还有在三峡、和田、国外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这些日常生活中零零碎碎的片段连同发福的朋友和家人……都被打包进了画家刘小东最近的影像展里。1984年到2014年的千余张照片次第陈列,一个展厅一个展厅地往里铺排,迂回的过道好似时空穿越器。
像急于抓住某个稍纵即逝的瞬间,使劲按下快门,这些照片并不都是美的。相反,虚晃,无厘头,构图也不完整,跟“艺术”看似搭不上边。画家艾民说,“刘小东用他特有的但是并非总是类型化的语言和介质记载着生活方式的变迁,不仅是他自己的,还有他所见的,而这构成了他在不同的物质点的迁移方式,其实就是中国在这过去的三十年的生活方式的变迁。”
“儿时朋友都胖了”,对这个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展览,刘小东自己倒更愿意这样总结。“但胖得更快的,是这个社会。”
像眨眼皮一样记录日常
和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喻红的恋爱,是刘小东影像展柔情的开端。1984年,两人刚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跑到北戴河“约会”,刘小东拿着花25块钱买来的旧相机,在海边偷偷抓拍了几张心上人的照片。一会儿曝光过度,一会儿对焦不准,却是他对那段日子最强烈的记忆,“当时我心里还有些害怕,担心一切不是真的,都不敢相信我们真的是在恋爱。”
而后,抓拍这个习惯,就这么一直保留了下来。宴会上叼起烟蒂的小男孩,血淋淋倒在路边的鸭子,三峡光膀子打牌的工人—刘小东的视角从喻红和亲友身上,延展到生活和社会的每一个细节。
画面大多不美,也毫无构图可言。陈丹青评价刘小东的禀赋,在于“如动物般观看世界”:“动物的目光,无明、无辜、无情、无差别,不存意见,不附带所谓文化。他永远是在看,亦如动物般敏于被看。”
对这个说法,刘小东笑呵呵地接住。 “(摄影)对我来讲就像眨眼皮一样,如此而已。但对哪个方向眨眼皮是自己的选择,这些跟我的绘画有很深的关系。”
照片里的现实在他的画里叠映,如他所言,拍照和画画并不是孤立的两件事,熟悉刘小东的观众在这次展览里找到不少他画作的影子。
街头一辆呼啸而过的卡车后斗里,挤满了进城的务工人员,赤裸着上身,四下张望—贾樟柯还记得这幅画带给他的冲击,“看到这一车人,你能想象它是开过了北京的三环路,在那样的一个城市化的空间,农业社会的痕迹跟城市的发展融合。”
这张画的原型,就躺在刘小东的千余张照片中间。不同的是,照片里,一车人穿着灰突突的粗布衣服,直视镜头,咧嘴憨笑,而在画画时,刘小东想了想,还是把那衣服抠了,一车人的面目也模糊起来。
没有相机的时候,刘小东画油画前先用素描;有了相机后,这些零零散散的照片之于他,就像绘画的速写本。“有时候墨汁洒上来还留着呢,有时候弄得很精细,胡说八道、乱涂,都在里面。”
照片看似平凡无奇,但他显然不是随意地拍。有个着魔似的场景被陈丹青记了下来:“那年他带我出游京郊,中途停车,着急撒尿般奔向路边,拍了几个穿过田埂的村民,随即回车继续驾驶,日后这幅平淡无奇的照片被植入他画中的生动背景。”
每一张都是稍纵即逝的瞬间,一旦错过,也就回不来了。刘小东觉得,对着照片画画这种方式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场”。
有时候在户外写生,一幅画没有画完整,拍了照,回去还可以补救。虽不是每一笔都对着真人真物,但现场的气息和意义都在。“现场性很重要。我的想象力是有限的,但客观会给你很多气息,启发你,会让你变得更开放。更有意想不到的事情,意想不到的意思,在画面里出现。”
刘小东说,他的照片和绘画,气质都是相通的,“一看就是一个人的东西”。像照片传达的一样,日常的细碎生活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落入他的画里。
这些细碎的日常,被贾樟柯收入眼底,并为此激动很久。上世纪90年代初的文艺青年贾樟柯,在电影学院考完试后,没事就往美院里溜达,看到刘小东绘画的第一眼,就被震撼到了。因为当时能看到的国内油画,不是风景画就是开国大典之类的历史题材,没想到有这样一个青年画家,画着自己非常熟悉又陌生的东西—火车站、雪碧、夏日的教室、大学的走廊,都跟生活如此贴近。印象最深的那张《烧耗子》,在护城河边,几个外来的年轻人穿着大一号的西装,站着看一只被烧焦的、乱窜的耗子。
“那就是我们的日常,或者说我们那个时代。那样的焦灼、混乱,但又那样的充满生命力,跟这种浪漫。”
贾樟柯也是从那时起,成了画家刘小东的“粉丝”,他说,那些画打破了中国绘画的某种常规。
这为二人的合作埋下伏笔。2005年,贾樟柯追随刘小东西行到三峡库区,那时刘小东正在三峡画他的《温床》,他画,贾樟柯就拍他。“他当时要是在新疆或者山西,我也都会去,所以去哪里不是我的选择,刘小东才是我的兴趣点。”由此产生的纪录片《东》,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由意大利艺术协会和意大利纪录片协会颁发的“2006开放奖”和纪录片奖。
彼时,在瓦砾堆中,刘小东正在画当地的拆迁工人,他疯狂地画,把“拍片”这件事晾在一边。有时候,刘小东兀自在那儿画着,任由贾樟柯随意地拍。有天正拍着,突然“轰”的一声,一栋楼塌了下来,拆楼工人被埋在里面,没再站起来。
溜在社会边上管闲事
挺着啤酒肚的男人,酒桌上慵懒的人群,在长11米、高1.5米的巨幅画里神情涣散。此次影像展也沿用了这幅画的名字:“儿时朋友都胖了”。刘小东叹一口气,“社会变胖的速度比人还快。”
2006年,刘小东曾回故乡辽宁金城写生,画曾经的小伙伴,画台球厅闲着的女郎、田埂上研究X光片的男子、废弃飞机边的牌局,故乡在他的画布上有了温度。然而短短4年,小镇金城变得太快,彼时的平楼被拆个精光。影展最后一张照片,是刘小东站在自家门前画画时照的,那栋房子,如今也已灰飞烟灭。朋友们却照旧各奔东西,明明快到退休的年纪,稳定的生活仍好似远在天边。
“不仅仅是焦虑,真的是很没有办法。”刘小东说,那么大片的耕地变成楼房,那么多自然村落变成新农村,这个社会的转型、大发展带来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一触及此,他的声音立刻急促起来,“我们都会变成没有故乡的城里人,每个人拼命地往前奔,退路却被斩掉了。原来也许还有一个温情的小镇、一片田野让你去瞎奔,去抒怀,但是现在,都变成一片楼房和城市,你可能只能去卡拉OK抒怀了。”
同时,一些不可思议的恶性事件发生,社会快速发展也带来人性的变化。“我改变不了现状,但可以凝视这种变化,去捅开这种异化和变态、臃肿的东西。”作为艺术家,刘小东自嘲,他总是怨天尤人、自作多情,为这些事情忧虑,创作也都围绕这些主题,“毕竟不是社会实践的真正参与者,还是溜在边上的人,没事儿干的人,精神上管闲事的人。”
陈丹青说他生猛,阿城说他鲜活,他全盘接受。“我可以说是老愤青吧”,刘小东笑。他曾说,画画时常怀怨恨。这些年来,从成名作《三峡大移民》、《三峡新移民》,到后来去新疆和田、青海等地完成各种绘画项目,对现实的批判始终不曾从他的画布上挪开。
第一次到重庆奉节是在2002年,彼时为了建三峡大坝,那里河流已经断流,剩下拆迁后的废墟。当天天色已晚,满目的疮痍让他心里一震—“画下来”,他想,可是,怎么画?回北京后,有天路过工地,他看到两个人抬着沉重的钢筋从沙尘暴里走过,“像一根绳上的蚂蚱”。那一刻,他突然想到人的命运。把工地场景和三峡的背景融到一起,第一张《三峡大移民》就这样跳脱了出来。
此后,他不停地画,试图给这个社会提醒点什么。
在金城,他画城市化进程中被遗忘的一群人。组画里,自己最满意的那张《肋骨弯了》,两个男人在田埂上旁若无人地审视自己的身体,“被遗忘的气息”。
在青海,他画戈壁滩上吐着浓烟的化工厂,画青藏铁路,画牵马走过的牧民。
在和田,他画不停挖玉的老少人群,千疮百孔的河道。
刘小东说自己痛恨旅行,但为了画画,这些年马不停蹄地走了很多地方。从北京走到三峡,走到故乡,又走出中国。这次30年影像展搭配展出了5幅画作,其中有一幅就是2008年的罗马写生,10米宽、2.5米高的画布上,尽是一群人倚坐餐桌兴致盎然吃饭的情景,题目是:“吃完了再说”。他说,这是一个隐喻,我们做什么事都不管未来,眼睛只盯着现下,一切吃完了再说。但如果把所有麻烦都推给子孙后代,以后的他们怎么办?“有的事情吃前就要解决,画里有这样一些焦虑和忧患。”
“我就是精神上管闲事,溜着边儿,说点不阴不阳的话。能做什么呢?”刘小东重复这句话,垂下眼睑,停顿了好一阵。
现实在刘小东那里变得沉重,但他也不是沉重到不可接近。
30年影像展里,喻红始终是最醒目的主角。沙滩上的女孩,成了妻子、母亲,30年后依旧窈窕美丽。刘小东没有把对社会的愤怒带入生活,按他自己的说法,“艺术上该亮见识就得亮,在生活中倒是挺随和的。”30年来,他画画、教书,没离婚,有老婆有孩子,日子看似波澜不惊倒也平稳幸福。他说,家庭对他的意义,跟艺术是一样的。
回头看这30年,刘小东觉得,只要过去了的在记忆里就都是好的,都值得怀念。“我是个悲观的人”,他补充道,人总归一死,最后无声无息还给了当初的虚无。悲观来自于这个社会,而正因为悲观,才会珍视一些事情,这点让他感激,“你会有更多的爱,更多的灵感。”
- >>相关新闻
- • 中国首个专注于艺术影像的国际博览会上海闭幕
- • 艺术8奖得主苏菲兰的中国之旅——出神·入画
- • Jeffery Shaw:新媒体艺术旧的、新的与未来
- • 2014横滨三年展——审视艺术和作为文献的艺术
- • 尤伦斯夫妇抛售亿元当代艺术品 或致多米诺效应
- • 珍珠:何迟个展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举办
- • 艺术不一定得喜闻乐见:但要确保真善美
- • "祼视时空的绘画:实验非辨别性的心与眼"开幕
- • 今日换帅一周年观察:高鹏与今日美术馆的性格之变
- • 长卷:世界寓言当代艺术展将在天津举办
- • 刘小东写实作品《违章》上拍香港苏富比
- • 刘小东:活生生的生命是怎么滚过来的
- • 民生现代美术馆推出"儿时朋友都胖了"刘小东影像展
- • 油画家刘小东两本图书获评“世界最美的书”
- • 自称"小混混"的刘小东是中国的弗洛伊德?

- • 陈之海山水小品展在天津图书大厦开展
- • 韩必省:笔墨当属时代 画作雅俗共赏
- • 姜金军、陈丙利等博士画家走进滨海画美景
- • 视频:王俊生大写意画展亮相天津群艺馆
- • 孙其峰艺术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津举行
- • 尤里·博罗罗维茨基版画藏书票展在滨海新区开幕
- • 陈少梅国画艺术研讨会在津举办
- • 全国楹联大赛优秀作品联墨展在津开幕
- • 境由心生:陈丙利山水画展将在天津开幕
- • 天津:创意产业蓬勃兴起 做好文化这篇文章
- • 一墨一世界 一笔一乾坤—走进写意人物画家田娟
- • 中国楹联书画院实践基地—问津阁在古文化街亮相
- • 长卷:世界寓言当代艺术展将在天津举办
- • 别有黛色·张福义 康国林 马孟杰三人书法展将举行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