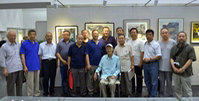-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蔡国强和他的大作品时代

作品《静墨》里,蔡国强挖了一个大坑,注入三十吨墨汁,再让一道“墨汁瀑布”从天而降。“这其实和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很像,先挖一个大坑,然后再想怎么办。”蔡国强解读。
“你知道点烟花的钥匙在谁手里吗?”2014年8月6日下午,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为男孩蔡创作焰火壁画》的活动中,蔡国强俯身问一个正在画画的小孩。“你点烟花的钥匙在你父亲手里,蔡叔叔点焰火的钥匙在政府手里。”
挖个大坑,再想办法
此时距离8月8日《蔡国强:九级浪》展览的开幕式已经不到48小时。蔡国强将在黄浦江上燃放焰火作为展览的开幕式,这也是蔡国强第一次在国内燃放白日焰火,但一切准备就绪的焰火表演尚未拿到批文。
蔡国强甚至已经想好了万不得已时的替代方案——在美术馆门外的小广场上燃放一场小型的焰火。“老祖宗的《易经》就学会了一个‘易’字,学会变化。”蔡国强对记者说。
但是他的心里始终没有放弃。当天傍晚,蔡国强接到公安局的电话,立刻赶去陈述详情。在等待上级批复时,他和同伴们一直守在公安局长的办公室里,与局长面对面坐着,到了饭点也不离开,唯恐再生波澜。拿到批文已经是晚上八点,焰火燃放的管理非常严格,运输证必须原件与运输车辆同行,蔡国强立刻派人接力赶往虹桥机场坐最后一班飞机将批文带到长沙。浏阳的焰火工厂连夜开车将焰火运往上海,抵达后剩下的安装调试时间只有16个小时,而平时的安装和调试时间是36个小时。
8日零时刚过,焰火安装团队在岸边平台船上争分夺秒地工作,突然到来的水上巡逻船举起手电,要求立即停工,并将现场负责人员带去属地派出所,理由是私自安装易燃易爆物品。蔡国强即刻与同事带着相关批文赶往派出所解释情况。水上公安表示,白天没有收到上级部门的任何指示与说明,在情况不明朗前暂时停工,等天亮后市消防局到现场确认后再继续开工。
如果等到早上7点再开工,安装时间已经不够,等于放弃了“白日焰火”。蔡国强一边和工程队伍商量作品呈现的新方案,一边由同事向水上公安解释斡旋……僵持4小时后,蔡国强在凌晨4点收到同事的短信:已经开工!
8月8日下午,在观众的欢呼和惊叹声中,蔡国强实施了这件名为“Elegy(挽歌)”的焰火作品。
蔡国强的弟弟蔡国盛说:“他哪一次不是这样的?”蔡国强早已习惯了走钢丝,很多时候遇到的困难都是他给自己出的难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能不能先死后生”。
《九级浪》展览中的《静墨》就是如此。蔡国强原来想把去年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制作的大型装置《遗产》借到上海展出,那是99只仿真动物围绕着注有170吨水的池塘,展现艺术家心中“最后的天堂”。但蔡国强修改了这件作品在上海展出的方案,让动物们不再身处由黄金海岸的沙子堆出的景致,而是放进中国的时代背景。澳方没有接受这一方案。而此时蔡国强已经决定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掘地三尺,挖一个大坑。
于是《静墨》替代了《遗产》。从地下挖出的水泥块和裸露的钢筋堆积在墨池周围,象征着大兴土木的建设工地和中国的山水。蔡国强在大坑里注入了三十吨墨汁,展厅里弥漫着浓郁的墨香,一道墨汁的瀑布从天而降,激荡着平静的墨池表面。“这其实和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很像,先挖一个大坑,然后再想怎么办。”
蔡国强在从家乡泉州带到上海的渔船上安置了99只动物,这件影射黄浦江死猪事件、名为《九级浪》的作品安放在美术馆的大厅里。渔船没有行驶执照,无法直接开进黄浦江,蔡国强就把渔船放在平底船上运来。渔船太大,进不了美术馆的大门,就把渔船上下锯开分成两部分,又拆了美术馆大门。
布展时,蔡国强请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将船上的动物做旧。学生们为了让这些动物看上去更奄奄一息,用黑色丙烯颜料把它们都涂了一遍。“结果动物都像从泥水里面给拉起来的,都涂成一个动物,都是一样的颜色。我三十几年艺术生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打击。”好在颜料没干透,赶快用潮湿的毛巾擦,用吹风机吹,干后用手搓。补救及时,调整后的动物颜色终于和整艘船的沧桑感比较协调。
个展的十一件作品,除了《撞墙》《巴西花鸟画》和《国王的马房》之外,其余均在上海新创作完成。另有手稿展厅展示蔡国强构思此次展览作品时的创意过程。他还用大量的原作、生活照片、文献实物,以“大事记”的方式串联起了自己的创作历程,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以不同媒介材料创作完成的成功作品之外,也有不少失败的个案。蔡国强希望年轻艺术家从自己的成长、转变和遇到的挫折中受到启发和激励。
“达•芬奇当初也是接受订单的”
记者:最近对你的议论和批评特别多,有一种说法是老蔡很会变身,他在“农民达•芬奇”的时候,自称农民,在现在的“九级浪”又变成男孩蔡。你怎么看?
蔡国强:因为我本来就是农民,也是男孩,只是他们把男孩和农民分开了。以后他们又骂说,老蔡这作品说自己是艺术家。可是我本来就是艺术家。非议的层次有高有低,稍微高一点,我们还会想一想,低了就是看起来很轻松,不会让我们有一点点“硌一下”的思考。

记者:你有一个说法,全世界的当代艺术都是被金钱、被大约一千个藏家左右的。
蔡国强:一千个藏家,是西方流行的说法,我也是用“据说”。过去的艺术也是依靠了贵族和收藏家,或者利益集团,当然包括政府,创作那些教堂壁画和大型公共性艺术。经过了现代艺术的大众化,走到和中产阶级的结合;随着中产阶级的民主开放和现代艺术的普及,带来了现代城市和现代设计、现在的生活方式。这种中产阶级的普及又形成一个新贵收藏集团。在这个过程里面,现代艺术就可以为一个城市创造财富和价值。我自己的事情就很典型,2013年给澳洲做一个展览,就给昆士兰州创造一千四百多万澳元的经济效益。这是直接创汇,间接的就更多了,文化上很多是间接的。
现代艺术变成一个产业,对于城市来说,政府的支持力度也比以前大了,这种事情有它的好处,同时也带来弊端——现代艺术被系统化和功能化。现代艺术功能化的结果就是从1990年代以来的双年展、三年展这种大型的城市项目,到城市形象产业和城市文化产业的诞生,以及大型美术馆的诞生。为什么美术馆要建得比较大呢?因为需要夺人眼球的作品,夺人眼球的作品就要大空间。这里面没有好坏之分,这个时代产生了我们这样的艺术家做出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给这个时代留下了它的风格和特点。
但它本身也是这个时代的问题所在。一个美术馆把自己的展厅冲得很大,先别说建馆的钱就要收藏家支持,之后你要运营,就更离不开收藏家了,因为美术馆的难度在于支撑下去。所以美术馆的董事会很少学术专家,都是有钱人居多,学术专家进入董事会没有多少用处。喜欢当代艺术的有钱人说话就影响了美术馆的方向,影响美术馆要做的事情,虽然不是主导,但确实是影响了。这些人也在拍卖会和收藏市场上十分活跃,这个世界就这样连在了一起。
但是,这并不等于西方的当代艺术就很糟糕,它还是有学术机构并行,尊重策展的独立思想,还有报纸、电视,它有一个队伍是能批评发声的。《纽约时报》就会批评说:这几年纽约就没有那么多有价值的作品,做的都是哪儿都能看到的东西,年轻人没空间,刚来闯荡江湖的不同文化的艺术家没空间,这个城市没有勇气去担当。
记者:所以你会警惕地对待美术馆的委托?
蔡国强:警惕是需要有的,但是不是有必要那么地在意?我自己的工作本来就不是商业化的思路。我这样说,并不是评判艺术经济的好坏,而只是我的一个观点。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当初也是接受订单的,但是人家的订单回答得好啊,不是没有价值的创作。
记者:你曾说过媒体就是不同的镜子。
蔡国强:其实我在全世界常常是依赖着媒体成长的,各国媒体跟我在讨论我的艺术的时候,其实像一个不同的镜子。有时候是镜子,有时候是水影。我给你讲过水影的故事没有?我奶奶不到三十岁就死了丈夫,是她把我爸爸他们带大的。但她不是那么地痛苦,她定期都会去池塘对着水面哭,跟我爷爷对话,她能看到我爷爷在池塘的水面出现。她看到的不光我爷爷,还看到我爷爷在的那个世界。我们有时候也会陪她去看水影。
记者:你们能看到吗?
蔡国强:我们啥都没看到,只看到水面上的云彩。
澳洲的那些动物不来了,我就写信给昆士兰美术馆馆长,说明我的思路。本来我想澳洲这些动物来不了,咱们就不要有那些动物,但是可以有水影。只要有池塘,就有水面,有水面就能够看到影子。水影的空间更大,镜子照出自己的脸,看到越来越多皱纹,有白头发了。这次啥都没照到,都是沉默的黑镜子。
记者:从你的“大事记”里看到,很多作品的完成过程中其实都有各种困难,还有失败的个案。
蔡国强:我是故意把那些东西拿出来,坦白从宽,好好汇报。那些部分的目标是年轻艺术家,我想让年轻艺术家可以看到我在中国、在日本和美国是如何出发的,中间有哪些挫折,转变的过程是怎样的。对年轻人,就是挫折和成功两面都要讲一点。
记者:你近年的作品很多,这次挑了多哈的《海市蜃楼》和巴黎的《一夜情》用视频和图片来展示,这两个作品是否你比较满意的、比较有特点的?
蔡国强:这几年我最大的特点,是把在不同文化里面如何去工作的方法,拿出来给大家知道。以前一直也是在不同的文化、在全世界做展览,但不是那么明确。现在,不同文化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变得更重要。整个国际经济正在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政治的价值观在统一,可是人们也在呼唤文化必须有所不同,不然就没意思了,全世界的文化都一样有什么意思?
《一夜情》是跟老牌的欧洲文化对话。你出的牌是什么?在多哈是什么?在乌克兰是什么?在巴西、阿根廷、澳洲你是什么?都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面去对话。
记者:2014年12月你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创作的作品只是焰火吗?
蔡国强:会有五万支焰火,也有火药画和展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有个美术馆,他们本来是想请我做个展,我要做火药作品,他们也很欢迎。但是人家没想到我要做一个和探戈有关的作品,现在把这个城市都给忽悠起来了。本来他们要开发港口所在的博卡区,那里有著名的博卡青年队,但是这个地方犯罪率、失业率很高,当地人不愿去。不多的收入来自那些去探戈诞生地观光的游客。我在那里做作品,他们当然是很欢迎的,会促进当地的经济向上。开始我说能不能有两千观众来陪着焰火跳探戈,后来他们预计会有七十万至一百万,当地希望我做三场,我说不行。
要有更多人的参与,但又不会在艺术问题上太危险,那么做什么?这也是很俗的事情,能不能先死后生?我自己从探戈身上学习,他们给我请来探戈的专家,又请来很好的舞者,其中的一男一女会成为我作品里的探戈舞主跳,中间穿插各种各样风格的舞者,我会看到他们是如何调侃、如何对谈。主跳的这一对年纪稍微大,动作比较小,跳的是比较传统的探戈。我们租下一个剧场,电影队拍下整个过程。探戈有很多种乐器,我最迷恋小手风琴,我要把小手风琴编成焰火晚会的背景,它张张合合、停停顿顿,非常合适这种感觉。一个来自遥远地方的艺术家,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叙述探戈。
他们太相信我会做得很了不起,但只有我自己知道太难了。探戈的感觉很微妙,舞步也很复杂,如果去抠这些细节是没有前途的,但是我执意要让焰火像真实的舞者,有时候我要追求探戈舞步的造型,有时候要追求音乐的情绪,有时候要追求焰火象征的这个国家当时的命运。(王寅)
- >>相关新闻
- • 詹皓:艺术圈为何“大师”层出不穷?
- • 徐江:伟大的观念艺术
- • 李安源:个体画家创作观念多元的陷阱
- • 罗丹给青年艺术家的一封信:"自然"永远是美的
- • 中国首个专注于艺术影像的国际博览会上海闭幕
- • 连接街头文化与波普艺术:纽约菲尔组合访谈
- • 艺术8奖得主苏菲兰的中国之旅——出神·入画
- • Jeffery Shaw:新媒体艺术旧的、新的与未来
- • “一战” 杜尚与悄然转变的艺术风向
- • 2014横滨三年展——审视艺术和作为文献的艺术
- • 一战中丧生的十位艺术天才
- • 西班牙梦中之岛首次举办世上最大规模街头艺术展
- • 尤伦斯夫妇抛售亿元当代艺术品 或致多米诺效应
- • 珍珠:何迟个展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举办
- • 艺术不一定得喜闻乐见:但要确保真善美
- • "祼视时空的绘画:实验非辨别性的心与眼"开幕
- • 今日换帅一周年观察:高鹏与今日美术馆的性格之变
- • 长卷:世界寓言当代艺术展将在天津举办
- • 文夏:重新选择认知当代艺术的方法
- • 当代艺术家手稿展出:看手稿 读艺术家的心

- • 陈之海山水小品展在天津图书大厦开展
- • 韩必省:笔墨当属时代 画作雅俗共赏
- • 姜金军、陈丙利等博士画家走进滨海画美景
- • 视频:王俊生大写意画展亮相天津群艺馆
- • 孙其峰艺术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津举行
- • 尤里·博罗罗维茨基版画藏书票展在滨海新区开幕
- • 陈少梅国画艺术研讨会在津举办
- • 全国楹联大赛优秀作品联墨展在津开幕
- • 境由心生:陈丙利山水画展将在天津开幕
- • 天津:创意产业蓬勃兴起 做好文化这篇文章
- • 一墨一世界 一笔一乾坤—走进写意人物画家田娟
- • 中国楹联书画院实践基地—问津阁在古文化街亮相
- • 长卷:世界寓言当代艺术展将在天津举办
- • 别有黛色·张福义 康国林 马孟杰三人书法展将举行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