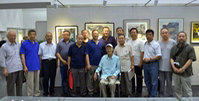-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走进艺术家颜磊:以态度论艺术

艺术家颜磊

北京谈判大楼/CAAW收藏

红灯区/2000年

泰康方案与洪浩合作/2006

艺术客7、8月合刊封面
颜磊,并不是一个特别容易被读懂的艺术家,而他,确是中国艺术界最频繁受邀参加国际大型双年展、文献展的艺术家。他曾经与艺术家洪浩一起,因为伪造国际大展邀请信,让国内外都记住了这位挑动了艺术界敏感神经的艺术家。他声称自己不再致力于创造新的图像,宣告了他向传统的艺术家角色的告别。颜磊擅长从展览系统的历史和机制中找寻与作品思路的关联,就地取材成为他的作品始终针对语境生效的密钥。最有名的《北京的礼物》更像是送给未来的一个礼物,是他设下的一个伏笔,与杜尚等艺术家在艺术机制上的变革不同(现成品成为艺术),颜磊的工作不仅仅增加了艺术的可能性,也为未来的文化格局和现象,提供了基础。在颜磊的众多作品中,时常让人感觉他的情感里混杂着的一种莫名的“爱恨交集”的情绪,他善于在散淡中透出机锋,并在其中呈现着多重矛盾和冲突的价值观,自己与国际展览焦虑而矛盾的关系,以及由此涉及的与“全球艺术体制”关系进行反思的“心路历程”,交织出他对自我身份的确立和对“操纵”艺术的权利的思考。
在颜磊看来,今夏已翻滚而去的巴西世界杯热浪只是一个表象,吸引他的重点落在足球所带来的经济、政治、话语权的魅力狂欢。足球带给人们奔放、自由和掌控快感的同时,也组合成了一个波及全球的利益共同体,成为当下社会生活中最大的政治。这些让颜磊联想到了艺术,只是艺术的政治化更加隐蔽而不易察觉,因为受众(精英阶层)的优越感,足以使利益显得冠冕堂皇。颜磊多年来的创作之路,一直在隐隐地指涉各类由社会政治而构建的利益共同体,以他一贯的玩笑式的黑色幽默方式。
上世纪90年代,经过“85新潮”、柏林墙倒塌、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大地魔术师”展览等标志性事件之后,中国的当代艺术开始有了针对“体制”的对话。这里的体制并非惯常意义上的国家体制,而是代表一种霸权和文化优势的想象,以及这种优越感所带来的虚无的文化精英主义。而中国艺术家对于巴塞尔、威尼斯双年展等强有力的西方文化“权利”符号,一直抱有极高的幻想和渴望。
1997年,大家都视自己为当代艺术体制内部一份子,并努力地为其添砖加瓦,试图建构一个以西方艺术话语为原点的利益共同体,大批的艺术家收到来自IeInay Oahgnoh寄来的卡塞尔文献展邀请信,“IeInay Oahgnoh”正是颜磊与洪浩名字的拼音逆写。而炮制信件事件发生之后出奇的缄默,意味着颜磊被孤立于当代艺术江湖之外。当然颜磊也曾承认孤独对于艺术家来说是必然的,然而孤立于任何群体之外,也促使了他对于群体政治的思考。
由此我们也能够看到另一条线索,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出国未遂的颜磊也像收到《邀请信》的艺术家一样,对西方文化语境有着特别的想象。没过多久,颜磊的文化身份就得以转变,从之前单纯对艺术“高地”的意淫和怀疑的矛盾心理,转变为对于艺术文化权利的揶揄。1998年-1999年已经移居香港的颜磊在作品“红灯区”中,将红灯区标志性的粉灯挂满了位于粗鄙的油街一间刻意打造的艺术中心内。颜磊伪造了一间让人遐想无限的暧昧空间,并且因为整洁的环境,而招徕了众多香港蓝领顾客上门消费,造成了一时的拥堵,但很快人们意识到这里并不做生意。
这种对于艺术空间文化权力的调侃,打破了香港当时沉闷缺乏交流的艺术氛围,并且也用“艺术是桩生意”的语气,暗讽了艺术背后所隐藏的巨大政治、利益、以及交易。2000年的“Cover系列”,颜磊凭借VIP身份免费得到了一些画册后,再将其转手卖出,并将这些画册的封面转化为绘画,随后将这些封面作品再次出售。这种带有黑色幽默的调侃艺术的行为, 被掩盖在一张张封面的绘画背后。而这种将“权利”转化并循环利用的方式,最终消解了权力的价值。2002年在上海双年展上展出的“国际运气”,颜磊用台球桌上代表最后一球的黑8,告诉我们,他听到了的来自国际艺术彼岸的召唤。2004年的深圳双年展上,颜磊说服当地政府,在黄金地段圈出一个足球场(本来希望是高尔夫球场)大小的地皮长达两年的时间。而这个“交易”正是代表了地权关系的链条:政府-开发商-土地所有人三方的买卖,而这个名为“第五系统”的作品也呈现了颜磊对于各种体制的试探,无论是艺术领域还是政治领域。
颜磊的创作之所以能够跳脱出中国当代艺术的语境,并不仅限于他身体的旅行与出走,而更多的是因为他对于创作方式的“觉醒”。他从一开始就从未将创作限于平面的二维画布,而是不断试探着自我与体制、主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而如何有效地传播作品是颜磊非常在意的,因为传播意味着“消费”和游刃有余地与体制周旋。
2006年《泰康计划》中,颜磊和洪浩篡改了梵高的画作“阿尔勒医院的病房”(Ward in The Hospital in Arles),头裹纱布的两位艺术家“隐藏”在画中;同一画布上,还贴着两张保险单原件,受益人为两位艺术家,保额为700万人民币。从合约签订起一年内,艺术家如果因艺术创作而罹患精神或肉体疾病,泰康保险将全额支付保险金。而最有意思的是为了强调作品的象征力量,颜磊和洪浩原本希望依据梵•高的病症,针对耳朵或精神疾患投保。但当时国内没有这样的保险产品,如果为此单独申请一个新的保险产品,需要经过保险公司和国家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惊动保险体制里的每一个环节,时间至少需要一年,而且可能性极小。于是,他们只得从现有的产品中挑选了“意外伤害”和“住院医疗”两种保险。根据体检结果,颜磊500万人民币的“意外伤害”险和20多万人民币的“住院医疗”险都通过批准。洪浩只有150万人民币的“意外伤害”险获得批准。之后,又因他们所购保险额度太高,还必须要由泰康人寿向中国再保险和瑞士再保险分保以共同承担风险,几经周折后该保险单才最终生效。对于商业体制的试探和周旋也在颜磊的“试验”范围内。
从一开始,颜磊关心的并不是艺术本体的问题,而是关于艺术方法论的多种可能。颜磊和当代艺术江湖的矛盾在于其讨论的对象和层面不同,而这种话语上的差异并不代表对艺术本身的质疑和智商优越感,只不过是一种态度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颜磊更像是一个思辨者而不是艺术家。
2012年已经第二次受邀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的颜磊,将300多幅画作密密麻麻地铺满展厅的墙壁、天花板等平面,展期中艺术家80%的作品在大众汽车的喷漆车间漆成了色块,只留下作品背面的签名还能分辨此前的内容。而这些“消失”的作品本身也来自现成图像,颜磊将这些既有的图像再次利用,并宣告了图像本身的虚无和脆弱,让人联想到图示本身的意义所在。同时也回应了自己“绘画就是占领美术馆墙面的东西”的调侃。
确实,颜磊从不创造图示,对于既有图像的利用被视作颜磊的标志,如果将颜磊的作品归于任何艺术流派则嫌狭隘。因为颜磊的重点并不在于如何创造图像,而是如何解读甚至如何“消费”图像。
颜磊著名的“彩轮系列”用工业化的方式表明他希望尽可能地摆脱艺术本体的束缚,进而更加“自由”地创作。这种自由是对于艺术方法论的自由尝试,也是对思想自由的向往,没有什么能够束缚我们的思维,同样,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的实践。这样来说,我们也就更加明白颜磊貌似保持对一切权威的抵抗态度,其实只是表象,真正的目的在于保持自由思想和独立的人格,不盲从。
如果说颜磊的创作延续着一个内在逻辑的话,那就是从对现实事物的质疑转变为直接改变或作用于现实本身。他用自己的行动提醒我们如何看待周围的世界,如何从另外的维度反观我们的生活。在传达从各个方向涌来的声音的同时,他也在试探着集体权利与个体之间的距离。颜磊要说的绝不仅限于确切的“政治”、“体制”“交易”或者“艺术”范畴,而是一种从独立的自我意识出发的自觉性。如果从这个层面来探讨的话,“艺术”这个载体则显得有些局限了。目前颜磊只能假借艺术的名义作用于现实,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合作方式的时候,暂且用艺术作为语言,好像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总有艺术装不下的东西。(李逦)
- >>相关新闻
- • 詹皓:艺术圈为何“大师”层出不穷?
- • 徐江:伟大的观念艺术
- • 李安源:个体画家创作观念多元的陷阱
- • 罗丹给青年艺术家的一封信:"自然"永远是美的
- • 中国首个专注于艺术影像的国际博览会上海闭幕
- • 连接街头文化与波普艺术:纽约菲尔组合访谈
- • 艺术8奖得主苏菲兰的中国之旅——出神·入画
- • Jeffery Shaw:新媒体艺术旧的、新的与未来
- • “一战” 杜尚与悄然转变的艺术风向
- • 2014横滨三年展——审视艺术和作为文献的艺术
- • 一战中丧生的十位艺术天才
- • 西班牙梦中之岛首次举办世上最大规模街头艺术展
- • 尤伦斯夫妇抛售亿元当代艺术品 或致多米诺效应
- • 珍珠:何迟个展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举办
- • 梵高等11位艺术家的极品遗言
- • 画家杨明义的传奇收藏:囊括诸多名家名作
- • 艺术不一定得喜闻乐见:但要确保真善美
- • "祼视时空的绘画:实验非辨别性的心与眼"开幕
- • 今日换帅一周年观察:高鹏与今日美术馆的性格之变
- • 长卷:世界寓言当代艺术展将在天津举办

- • 陈之海山水小品展在天津图书大厦开展
- • 韩必省:笔墨当属时代 画作雅俗共赏
- • 姜金军、陈丙利等博士画家走进滨海画美景
- • 视频:王俊生大写意画展亮相天津群艺馆
- • 孙其峰艺术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津举行
- • 尤里·博罗罗维茨基版画藏书票展在滨海新区开幕
- • 陈少梅国画艺术研讨会在津举办
- • 全国楹联大赛优秀作品联墨展在津开幕
- • 境由心生:陈丙利山水画展将在天津开幕
- • 天津:创意产业蓬勃兴起 做好文化这篇文章
- • 一墨一世界 一笔一乾坤—走进写意人物画家田娟
- • 中国楹联书画院实践基地—问津阁在古文化街亮相
- • 长卷:世界寓言当代艺术展将在天津举办
- • 别有黛色·张福义 康国林 马孟杰三人书法展将举行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