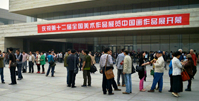-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新朦胧主义学术研讨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

2014年10月11日下午2点,新朦胧主义学术研讨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行。研讨会主持人有策展人兼评论家皮道坚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发言嘉宾包括海南大学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教授、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张志扬,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吴洪亮,中国美术馆馆员、中国绘画史博士魏祥奇,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彦伶,东京画廊+BTAP总监田畑幸人。
研讨会开始,皮道坚首先阐明了本次研讨会的三个议题:第一,从“朦胧主义”到“新朦胧主义”——本土和全球文化张力关系中传统绘画语言及其相关媒介的转换;第二,在本土和全球的文化张力关系中,艺术变革的可能性和东方绘画的世界性价值;第三,作为文化概念的“新朦胧主义”与当下东亚艺术创作的文化面向。
王璜生作为主办方代表表示,新朦胧主义的课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探讨的,“朦胧”这个研究课题会涉及到古典东方的哲学和美学,在学术界极具影响力。在当下,“朦胧”的课题不仅关于古典美学,还涉及到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学对人的感知、主客体之间的双重性、感知世界的多样性,还有我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之间的特殊关系所构成的对这个课题的多重理解。
田畑幸人:新朦胧主义的由来与寄望
第一个发言是来自东京的田畑幸人,他表示自己并非学者,本次是以策展人身份谈谈策划新朦胧主义展的原因。“朦胧”一词体现亚洲与西方对自然理解的不同,在西方观念,人类对自然是支配和控制的,而对亚洲人来说,人与自然是一种共存的关系。西方画家对自然进行描述的时候,称为“写生”——即把他们看到的自然忠实的反应在画布上,亚洲画家更加热衷去反映自然更深层次的内容。他认为,“朦胧”这个词语十分贴切的表达出了这种不同。“朦胧”出自于中国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对日本神道思想也是有着很大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中国传到日本的思想在这次展览中也会得到充分的体现。田畑幸人在最后说到,他希望本次研讨会能提供一种契机,让我们的思想达到共通性以后向西方进行传播。
王彦伶:新朦胧主义之吾见
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董事长王彦伶围绕着主题谈论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亚洲的崛起。二十一世纪是亚洲的世界,王彦伶认为用艺术文化作为指标来探讨亚洲地位是最合适的,如今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用货币来衡量顶层文化与艺术;其次谈到对“朦胧主义”的理解,王彦伶认为,任何一个作品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评价——语言性、文化性、社会性和主观性。从这“四性”维度去体会“朦胧主义”,它包容、内敛、具有东方文化的唯美,这是带有明确中华文化内核的艺术发展方向;至于798为何支持这个项目,王彦伶说到,这与798“要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艺术中心”这样的定位是相关的,这就要求798在国际艺术交流、在传播中华文化这个维度要做得更加深入。王彦伶说,“我认为‘朦胧主义’是我现在所遇到所有不同艺术理念中最能够代表中华精神、亚洲文化精神的概念和方向,所以我们特别真诚去支持它。”
魏祥奇:新绘画的理想——“朦胧”的历史语境
美术史博士魏祥奇用系统的理论知识探讨“朦胧”一词的历史语境。日本著名理论家峰村敏明提出关于“新朦胧主义”的几个概念:“朦胧体”绘画中存在一种语言的请调,“作为绘画的朦胧”远重要于“作为图像的朦胧”。因为唤起绘画语言本身的朦胧性,即通过笔触显现绘画的生命意象,是摆脱既有再现性绘画程式的有效方式。“新朦胧主义”就是要求笔触既避免自身被客体化,也要克服画家主观性的干涉——像中国传统绘画的书法,就是书法在书写的过程里面呈现人的心性,笔触的展现在东方的文化里面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而提出这个“新朦胧主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笔触太过于主观化。魏祥奇认为在“新朦胧主义”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是时间和空间。东方绘画“间”的概念在于“和”的概念,即两者不是对立,而是相互尊重的关系,这实际是东方人对自然的关系的体会。
吴洪亮:天游故静——对周思聪荷花创作的再探求
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吴洪亮针对女艺术家周思聪的荷花创作去探讨“新朦胧主义”的语境构成。高居翰曾评价周思聪艺术创作的两条主线,一条是充盈而又干预世事的人物画,另一条是协观者一同超凡远尘的荷花系列,似乎她执自己生活与艺术中对立的两端而和谐之,借以诠释她的艺格与人格。周思聪说过,“荷花本身给人一种沉静的感觉,它不像牡丹那样雍容,不像野花那样活泼,更特别的是一两朵荷花残枝败叶,也和我的心境比较吻合”,在她笔下会看到一种轻轻柔柔的、像李叔同书法那样“出纸三分”一样的荷花,而不是追求那种强悍的入木三分。吴洪亮最后表示,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再回望上个世纪八五新潮前艺术家对于水墨试验的再探讨,也许会对我们今天探讨的朦胧有新感受。
张志扬:走出西方“‘东方学’之‘东方’”而回复东方自身的几点建议——兼评“新朦胧主义”
哲学家张志扬从西学的角度对“新朦胧主义”概念进行研究。他认为,中国从1840年便受西学非常深的影响。关于“西方‘东方学’之‘东方’”,张志扬做出解释:今天大部分知识分子虽身在本土,但他所受的西方教育,使他不仅离开了西方概念、范畴、逻辑等思维方式,几乎不能感觉、思维与表达,而且还无意识地深陷中心与边缘的定位模式形成人格乃至心理倾斜。他已经习惯地把西方思想当作启蒙而自觉为主体意识运用的殖民人一一这就叫作西方东方学的东方人。如何走出这种情况?张志扬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还原西方思想为地中海区域古希腊罗马本土人类学之延伸,澄清“西方皆真理”的意识形态迷梦;二是警惕西方人以用代体物化人性,复兴东方用拨乱反正使其人之为人;三是不能以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尺度为世界尺度,只能各民族文化自主参照以复兴民族文化之本位。张志扬强调,“西方思想可以作为东方思想的参照,但绝对不能拿来作为检查东方现实的尺度。”
皮道坚:作为文化概念的“新朦胧主义”
皮道坚认为“新朦胧主义”对应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明治时代,由冈仓天心倡导、以菱田春草和横山大观为代表的朦胧体绘画。“朦胧主义”实际是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其本土艺术家试图在本土绘画中寻找新的资源以与当时流行的西方绘画融合,从而让本土艺术获得新的生命力的艺术革新运动。“朦胧主义”和“新朦胧主义”、本质上都是东方绘画面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反映,也是面对全球化压力自然的条件反射,这种张力关系一百年来没有改变。皮道坚说,“我们今天的艺术媒介革命已经开始了数十年,绘画的纯粹性不再存在,艺术开始强调文化政治立场和社会介入,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张力关系的复杂性,所以我们要考察这种张力关系中艺术变革的可能性和东方绘画的世界性价值在今天似乎有着特别的意义。”
本次研讨会邀请的几位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学者,用世界历史性的视野对现代艺术表现中的“新朦胧主义”现象进行重新审视并深入探讨。王璜生最后总结道:“这样一个研讨、学术是远远不够的,这应该只是一个起点,我们非常愿意在学术上进行专题的研究项目做一个系统性的展开,这是特别有意义去探讨的。”
- >>相关新闻
- • 天津画院举办“画说天津”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研讨会
- • 以艺术之名 向时计致敬
- • 萌萌哒:故宫推出《皇帝的一天》儿童iPad版应用
- • 美画家拥有罕见4色视觉:可见颜色为常人百倍
- • 我们究竟走了多远——反省中国当代艺术
- • 画家许翰政:从画者的角度思考绘画
- • 《百岁图》源于传统锦灰堆绘画 技艺至今为谜
- • 别让艺术沦为金钱的奴隶
- • 罗曼·西格纳:富有幽默和诗意的影像作品展
- • 广东20世纪以来被遗忘的艺术弄潮儿:梁锡鸿与赵兽
- • 飞鸟与鱼的若即若离:艺术家手绘的玻璃装置艺术
- • 文艺不分家:那些文人和画家之间的传奇故事
- • Jim Cogswell央美讲座:"镶满宝石的浩瀚无形之网"
- • 汉斯·德·沃尔夫——“破门而出:失传与模仿”
- • 光景常新:唐寅油画展北京798圣之空间展出
- • 王颖生:画壁——走进中国传统壁画
- • 自然之中——杨春当代图像艺术展在草场地开幕
- • "未来的回归: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展"座谈会
- • 女艺术家桐溪小蝉个展在798艺术中心展出
- • 潘公凯:做一个具有大视野和全局观的人

- • “画说天津”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研讨会
- • 苍劲恬然凝重朴实—李克玉书画作品评析
- • 水墨计(肆)十二人展将启幕 天津美院薛明入展
- • 王书平:与潘基文谈画的“东方鹰王”
- • 《光环的背后:我与名人》首发签售会11月2日举行
- • 百年书香 艺术精品——《华世奎书法作品集》出版
- • 天津文化旅游周暨东方艺术展在东京开幕
- • 圣地·后素—姚景卿姚铸国画精品展寿光举行
- • 书画家梁旭华的艺术世界:以字入门缘定山水
- • 挖掘传统 借古开今—薛永年谈李毅峰的山水画艺术
- • “荷语—郝跃先个人作品展”在天津空港经济区开展
- • 韩必省书画作品展暨慈善捐赠活动在北京举行
- • 天津美院教授著名画家何延喆80年代山水画课徒稿
- • 天津艺术家张羽:毛笔皴擦掉了当代水墨精神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