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迈克尔·克雷格-马丁:为什么一杯水是一棵橡树

“多年来,我的创作始终围绕身边日常、平凡之物。这些东西的发明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和欲望,因此,它们生动地体现了当代生活的复杂性,成为一种既不受语言、文化差异所限制,又不为其所湮没的沟通方式。”
天津美术网讯 近日,为个展“此时”来到上海的艺术家迈克尔·克雷格-马丁(Michael Craig-Martin)总是被人误称为“马丁先生”。其实他姓“克雷格-马丁”,然而这个姓又并非来自家族,也不是他父母姓氏的结合。“是我祖父创造的,他觉得克雷格-马丁听上去比马丁重要得多。”看来命名还是很关键的,现如今克雷格-马丁的确是当代艺术史绕不过的重要艺术家。克雷格-马丁的艺术生涯中名气最响的那件作品也有个不寻常的名字。作品展出于 1973 年,他把一玻璃杯的水放在钉在画廊墙面的一个架子上,展签上则是对“为什么这是一棵橡树”的严肃论述。结果有一次,这件作品被澳大利亚海关认为是植物而拒绝入境,他才不得不解释说这真的只是一杯水而已。1977 年,《橡树》被澳大利亚国立美术馆买下收藏。这件与杜尚的《泉》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作品令克雷格-马丁作为观念艺术家声名鹊起,然而他很快不再用现成品进行创作,而转向了用画笔描绘日常事物。

“多年来,我的创作始终围绕身边日常、平凡之物。这些东西的发明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和欲望,因此,它们生动地体现了当代生活的复杂性,成为一种既不受语言、文化差异所限制,又不为其所湮没的沟通方式。”
克雷格-马丁很喜欢喜玛拉雅美术馆的建筑空间,因为它宽敞、简单又具有现代感。他的作品被稀疏地挂在墙上,却不显得空旷,因为即便画幅很小,也因为清晰的轮廓和强烈的色彩对比而充满紧张感。画中的日常物品,易拉罐、开瓶器、卷筒纸、足球等等由于被填充了毫无变化的大色块而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招贴画,非常平面,但也非常深入人心。为了给这些能量巨大的物品腾出足够的空间,他决定撤下原本打算展出的 8 幅作品。
克雷格-马丁出生于爱尔兰,在美国长大,如今生活在英国。他进入学院开始正式学习艺术的上世纪 60 年代,正是当代艺术发展迅速的时期,当时的他与大部分活跃的艺术家一样是激进的,进行各种尝试、想要与众不同。“我的早期创作理念,是使用传统的创作手法,如绘画,我强调概念,而不是历史。”但这些激进的想法他早已不感兴趣了,他觉得人们在艺术创作中总是过于关注主题而不是内容,而事实上同一个主题,内容却可以千差万别。

某种程度上,克雷格-马丁的作品和波普艺术有相似之处,但安迪·沃霍尔关注商标、图像,而他认为自己关注的是物品本身:“我画的是物品,不是图像,尽管我把易拉罐画成红色,大家都会理解成可口可乐,但我并没有画商标。”实际上,他试图做的是与安迪·沃霍尔相反的事情,突破大家将流水线产品视为消费主义象征或设计符号的普遍看法,更深入地捕捉到它们的本质。为此,克雷格-马丁坚持不懈地使用线条(轮廓)这在绘画中被“发明”出来的东西,事实上轮廓并不存在,只是人们需要依靠它认识物品并把它们的图像固定下来。人类如何认识事物和认识世界,这才是他想要通过绘画探讨的东西。
年逾 70 的克雷格-马丁在现居地英国和祖国爱尔兰都已办过回顾展,但他将此次的新作展,也是首个中国个展取名为“此时”,是因为他觉得“当下更有意义”。他以前会在画面中表现多个物品,使用的线条也纷繁复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倾向于做纯粹的事情,因此画面也越来越简洁。他选择了一些不断更新换代的产品,比如 iPhone、X记者ox,也有多年来变化甚微的物件,比如书、椅子:“每个人看到我画的游戏手柄,都会联想到 X记者ox,但可能十几年后就没人知道它是什么了,就像十几年前,也没人知道这个薄薄的长方体是 iPhone。这不是很有趣吗,当代世界,事物出现,又消失,变化很快,但也有一些相对恒久的东西。我想 20 年后,如果人们看到这个展览的图册,很可能会发出‘那是多少年前啊’之类的感叹,同时也会了解到我们现在的生活。”

克雷格-马丁的生活和想法也在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发生变化。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个颇具隐喻性的故事:大约 15 年前的一天晚上,他在伦敦边开车边听广播,节目里有一个人正在谈论对艺术的看法,他对这个人的大部分观点都不能同意。然而听了 10 分钟之后,他突然意识到,那个说话的人正是他自己!如今回忆起这件事,克雷格-马丁还心有余悸:“当时我震惊得心跳加速,不得不停下车来缓解情绪,我记起那是5年前的一次采访,那时候我说话还带着美国口音。不过话说回来,能够改变和承认改变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记者:如果不会太冒犯的话,我想告诉你,如果在电脑上看你的作品,我会以为它们是打印的。
CM:是的,当你看复制品时,它们有点像计算机图表,不过现场看,又是有形的、现实的。
记者:你用丙烯画在铝板上,也是为了获得类似电脑制图的效果?
CM:我以前是画在布面上的,但是因为这些作品要用胶带勾画轮廓,用滚轮涂颜色,所以最好用硬的底板,而且铝板很稳定,画布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而开裂或扭曲,没法保持这种图表效果。
记者:你是怎么选择颜色的?虽然你使用的颜色不多,可是每一种都挺特别的。
CM:实际上它们都是很平常的颜色,虽然我用的是很好的颜料,但也只是很容易买到的商用颜料而已。我喜欢饱和度高、有紧张感的颜色,而且我不混合颜料,只把能形成强烈对比的单色组合在一张画里。但是这样的组合使每种颜色在不同的画里会显得不太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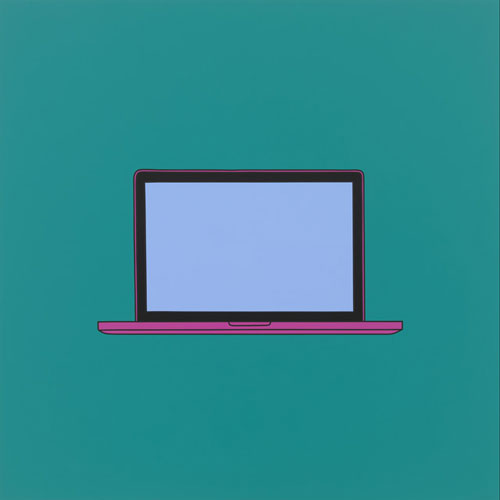
记者:你小时候就读于宗教学校,宗教艺术对你的创作产生过影响吗?你作品中那些黑色的勾边和教堂花窗玻璃上的图案还挺像的。
CM:花窗玻璃确实和我的画有点类似,西方艺术曾经大多是宗教艺术,我喜欢过去的艺术。虽然宗教艺术对我的创作没有直接影响,但是有一个牧师对我进行了艺术启蒙。他在学校里教的是法语,可他对所有艺术形式都感兴趣,当你还小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你什么是好东西,那是会产生很大影响的,因为它会就此伴随着你。那大概是上世纪 50 年代吧,在美国还不是很容易找到关于当代艺术的信息,所以对我来说像是展开了一个我根本不知道它存在的世界,可惜现在人人都知道了!当它还是个隐秘世界时,乐趣也比较多。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自己可以试着成为艺术家?
CM:我 14 岁时遇到一个法国的艺术老师,遇到一个真的活着的艺术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信息:成为艺术家是可能的。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有这个天分。我爸爸是个经济学家,我看着他的生活,再看看我老师的生活,觉得艺术家的生活比我爸爸的好多了。19 岁时,我去耶鲁大学学习绘画,决定试试看。作为一个想要成为艺术家的人,我不能更幸运了,当时正是艺术蓬勃发展的时代,耶鲁有美国最好的艺术课程,一个非常真实的当代艺术世界在我面前展开了,我现在的世界和我作为学生被介绍的世界是一样的。

记者:对观念艺术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你的成名作《橡树》(A Oak Tree),也知道你通过作品想传达什么观念,可是我不知道这个作品的名字是从哪里来的。
CM: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做这件作品时,我的想法是让一个东西变成另一个东西,但是不改变它。我立刻想到了玻璃瓶里的水,因为它是透明的,能一眼看穿,很美、很简单,我们很熟悉,但又是个谜团。而这两种材料,一种是坚硬的,一种是流动的,都是很棒的材料。我肯定不想把它命名为“榔头”之类的,太普通了,也不想叫它“太平洋”,联想太直接,我希望有门类上的跨越,所以它最好是有生命的。提起橡树,人们脑子里很难有一个固定的画面,它包括很多品种,可以是巨大的,也可以是一棵小树,它冬天夏天不一样,你也可能想到它的果实是松鼠爱吃的坚果,总之很难明确,这和我的创作初衷很匹配。
- >>相关新闻
- • 金善作品释读:感性冲动和生命的本真性表达
- • 肖恩·斯库利回顾展开幕在中央美院美术馆开幕
- • TEFAF2015:血拼当代艺术
- • 著名篆刻家林尔个展将亮相西泠印社美术馆
- • 另存为:缪晓春个展3月12日在京开幕
- • 欧阳春:怀疑过自己,没有怀疑过艺术
- • 缪晓春"另存为" 借用技术呈现的艺术新视界
- • 朱金石大型宣纸装置作品展即将在香港开幕
- • 798艺术区全艺社将举办澳门女艺术家陈慧雯作品展
- • 徐冰的装置《凤凰》:从MassMoca到圣约翰大教堂
- • 不在现场:当代艺术群展将亮相南艺美术馆
- • 艺术家曾梵志个展另类开幕:门口架炉子烤串
- • 长征空间举办朱昱个展 在"隔离"中找寻绘画本质
- • 张书笺个展《费拉》开幕 老者形象反思社会
- • 艺术门开幕个展任日:元塑方案将呈献独特蜂巢作品
- • 肖映梅个人作品展将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举办
- • 徐冰2015香港巴塞尔艺术个展:从天书到地书
- • “沉默”河原温首个大型回顾展纽约举办
- • 当代艺术家曾宏同名个展将于北京798杨画廊开幕
- • 奈良美智大型个展"无常人生"将在香港举行

- •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记王印强和他的写意人物画
- • 组图:著名书画家尹沧海赴韩国首尔东国大学讲学
- • 孟昭丽、萧慧珠、李澜绘画小品精粹展
- • 孟昭丽 萧慧珠 李澜小品精粹羊年绘画展前言
- • 霍岩:中国画的笔墨之美
- • 国画名家八人展在宝坻举行 孟庆占吕大江参展
- • 水墨语境·书法国画十人展将在西洋美术馆开展
- • 向中林山水画展在“集真阁”开幕
- • 组图:庆“三·八”西青女书画家深入警营送书画
- • 尹默 李振华 王文元 杨建岭等书画家在沧州开展
- • 天津著名书法家刘光焱:读帖临池终有得
- • “翰墨传承 学院力量”中国当代书法展开幕
- • 姜维群:首创“蜀山嘉陵派”的山水画家向中林
- • 第七届“津门女书画家佳作邀请展”举行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