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烟火映雪—寄枯木、古铁之墨水艺术展《烬介》
天津美术网讯 先前,我读本次展览引言中句,“画之既焚,余烬存焉”。明白人当一眼看出模式:“焚”=“存”。而余烬较之于画,孰重?这样的题目仍是有待议榷的。
塞尚曰:“如果我确知我的画将破坏,我将不再画画。”不难看出,保罗看重画作本身的分量。另有一语若此时加在后头,更有意思:“如果我确知我的画将被烧掉,我将拼命的画”。主张与之相反。
大家问,观点相反而已,有什么意思?还是有意思的。因为话,出自勃拉克之口。
勃拉克的立体主义曾受塞尚影响,先受影响而后又有突破又有新创。他在后半句话上的“逆反”,我以为是天才的机巧。两段之差别更似昭告,将“焚”当作更善的“存”,是跨了“现代”的槛。(未来主义、表现主义、野兽派)
千载过隙,中国却好似只有一个古典主义。五绝七律四六骈俪是汉语诗文的主菜,近现代的闻一多学波德莱尔,郭沫若学歌德,郁达夫学卢梭,都没学成大气候。徐志摩的新月诗,永远只是新月,今日未见盈满。况脱胎文人阶层的中国水墨艺术,一介“附属品”又能行将安处?
三人今次烧了画,正若杨之所言,是在惯常水墨展的沉闷气氛上“破它一破”。这发心是不坏的,但观者要搞清主次,不要揪着开胃小菜不放。有人问曰“为何‘烧’画,碎纸机也可以”;又或问曰“烧画的想法,从曷来,又是否烧出意义”。
我以为所列问题痛痒无干,祝成其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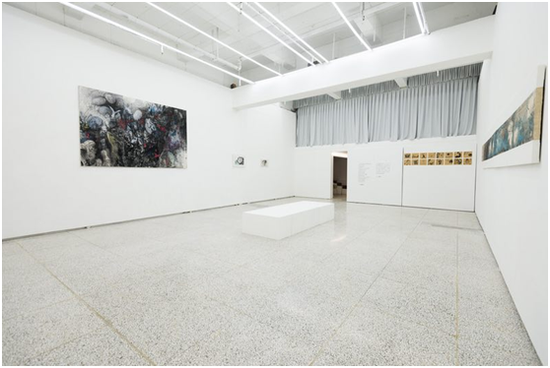
交流会当天,我丢古铁前辈一个题目:如果中国画作为一个门类,它要发展它要自由发挥,可怎么发挥大家还能继续认可,它依旧是一副中国画?(或换言之“槛”是什么,跨过了它便不再称为中国画)古铁讲,是修心,是精神。不禁想再问:把持好这个精神,今日用丙烯颜料再画,大家认可它是中国画吗?存疑了。
古铁所言之精神,是梵乐、庞德凭直觉捉摸中国,是克洛岱尔眷恋上的中国。到底,还是不中国。要“很中国”私以为一个前提,仍要事印象。事印象当然是一种“虚构”,一般重点在“构”。有言曰“青春是不自觉的浪漫主义,文学的浪漫主义是自觉的青春”讲文学,也讲创作与梦之殊。可弗洛伊德拿梦与艺术作比,还是意在“虚”上,当此,虚有了某种特定成分,中国印象便纷至沓来。
当场有作品《默生的世界》,大致讲述了古铁之“破”(杨引言所提的“破上一破”)。初看还以为关于拉尔夫?爱默生的哪种戏谑(又独把“爱”字当姓氏省掉,显得多么中国),再结合画面一看,到底不会与那位老牧师有哪里干系。有观者言,这画看了着实害怕,晚上要噩梦的。复问哪里可怕?不得。其实水墨的一种特定气韵,与局部那似牛鬼类魍魉的某样意向,调和出了这样的印象。叠加上浓重的堆积感,使它更远似一幅山水画。我以为如上叠加,“看山不是山”,使得一切吊诡都加倍了,大大增加作品的容量。
那么回到老问题,它中国吗?古铁的作品有先锋性的,但一个姑妄的看法:作品对如何“现代地水墨”,更胜过他口头的解释。他的反复皴染,重点是立足水与墨的特性这个原则上,不使“破”脱离了自觉。对于推崇一气呵成的中国画,这即非韪,又非大不韪,是大韪。既然大韪,想必中国得很。这一点,是我尤心欣赏,佩服的。

可作品的思想面多少显得有点急不可耐了一些。尤其作品名称,观者瞬间就能捉到重点(关于“人间炼狱”之种种,欲望、异化等等),仿佛先前那些吊诡的圈套也统统束手。明显的一点,所有的意象都开始服侍起思想来。
切忌服侍。意象和思想的关系是相融的关系,并没有主次,往更甚说,最好多题甚至无题。当主题是一个高高在上带着王冠的胖皇帝时,这间宫殿便低庸了,俗了。
如何才高级?我答:希腊神庙里并不住神,维纳斯没有手,罗马斗兽场里没有角斗士和野兽。可人们仍然能模糊感觉到,这间穹顶下的主人是神;那女人的手一定好看;而彼处的圆形建筑里,四野皆声音。此时感怀,才更彰了艺术的绵长味道。
当场苦木、古铁作品不少,大家想必各有各的看法。若拉开讲,以在下之文笔真是又臭又烦冗。万万原宥。今次以且仅以《默生的世界》为代表简单议述。
一个遗憾,苦木并没有去到交流会现场,不使我对策展得到一个全面的观察。左右询之,或答曰“有疾”,或答曰“积郁成疾”。那幅两人协同创作的大画,是个如何乾坤究竟才能让苦木先生罹恙?
要关心这个问题,得先把注意力放在画的毁灭上。“画之既焚”的另一重点,“焚”的字面含义——焚毁——它是很“用力”的。一件事情毁灭得如此用力时,就见它的硬度。我们把所烧之画当做一个英雄,它才配合了这样一个语境。女人自杀割腕,男人自杀子弹穿胸(原谅我的男性沙文主义,它是善意的),只有哥白尼的真理才般配施以耶稣式的死去。当我们见到枯木古铁二人的画作受刑,就仿佛置身在丹特士枪声中,为普希金掩面哭泣——而见证人一多,历史便定了性
现在,我们还有“丹特士的子弹”躺在琉璃柜子里,还有“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在被大家谈论。“麦子不死,焉有金色的麦田”。苦木的抱恙,是作为《哈罗德游记》精彩细节,永远地存了。
苦木先生次日缺位,容或并非憾事,亦非坏事或好事,是一件有趣的事(不含生病本身,祝康复)。至少我们多了一分敬意性的猜测。一幅《芦获寒禽图》与《人物花鸟小品》无声伫立,令观者对其欲言之语,也能有所遐设吧。


踅看旧旨,余烬与画孰重?我答,烈火或者英雄,都不重,重的是“烈火烧死英雄”。
不过,当代艺术还是有通病的,解剖太多,重构不足,现象不太好。社会变迁、人类异化、心理波动一览无遗,统统解剖:大声说,这是心,那是肺。这就高级了吗?我答:包起来再说。包扎好了,把手术剪也丢一边,开服药吧。
杨想要打破的沉闷气氛,尽负之一炬尔。这炬不是手里,更不在火盆,得是“目光如炬”的炬。水墨画的形式是一个被研究了几千年的形式,在古铁先生追寻水墨现当代的过程里,有诸多可以参考的故实,在那样的界范当中,或可以寻得医治当代西方艺术舶来主义的病。
等到“英雄之死”有了晔舛的叙事辞调,遥想取代谣言,虚荣变得光荣。如此下来,烟火映雪有所收获。策展人的那些纷纷忧悒,定然能孟夏开轩了。(王子禅)

- • 天津美院国际工作坊《铜版画的艺术创作》即将举行
- • 天津博物馆将陆续推出多个系列主题展览
- • 范扬中国人物画作品展在咸阳开幕
- • 申世辉泼墨散锋大写意山水画讲座在河南焦作举行
- • 贾广健、刘泉义等中国画全国巡展在北京荣宝斋开幕
- • 《唐云来师生迎春联墨展作品集》在天津首发
- • 天津著名画家姚景卿热心为师 助轮椅女孩放飞梦想
- • 董方印中国画人物精品展浓缩50年创作精华
- • 李旺个展述说Art Teller在鼎天中国空间开幕
- • 希望·展望-天津政协水彩研究院青年画家作品展开幕
- • 著名诗词家王焕墉先生追思会在天津市楹联学会举行
- • “李小可师生作品展”在天津展出 备受关注广受好评
- • “姚家班”携天津艺术界名流为姚景卿七十华诞送祝福
- • 天津市政协水彩画艺术研究院青年画家作品展7日开幕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