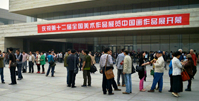-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广东20世纪以来被遗忘的艺术弄潮儿:梁锡鸿与赵兽

1948年合照(后排左为梁锡鸿,右为赵兽)。
“艺术运动应有如脱光了蔽着身的衣裳的裸体一样的心,把一切都撇开来,诚意地向着艺术的路途上前进……”这是1935年“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小品展座谈会上,前卫艺术家赵兽的一段表白。
置身于20世纪中国沧桑时运之中,梁锡鸿、赵兽等来自广东的前卫艺术青年在上世纪30年代提前引领了一场现代艺术的风潮。与19世纪末以来,不断谋求中国现代化方案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希望向中国引进西方的前卫艺术、先进文化,其目的是探讨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调和生成,让中国在世界文化新潮流的翻腾滚动中跟上时代脚步。
因有了他们,在20世纪广东美术的版图中,我们得以窥见色彩斑斓的一页,除了学院派艺术之外,我们得以见到野兽主义、超现实主义、木刻运动、新国画运动等等流派,这批前卫艺术的“弄潮儿”力图在广州建立一个现代艺术的多元景观,构建起现代都市的文化气场。然而,他们的纵情演绎似朝霜尘露,在20世纪风云动荡的中国历史中转瞬即逝,一度被无情遮蔽。而今,时过境迁,他们早年的前卫果敢、先知先觉,越来越散发出耐人寻味的魅力。就他们在百年美术史上的意义,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院副研究员蔡涛。
■专家访谈
谈历史
“他们参照的是巴黎的艺术理念”
南方日报:您如何评价这批来自广东的前卫艺术青年,上世纪30年代在日本成立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的举措?
蔡涛:当年,梁锡鸿、赵兽这批年轻人想在国内介绍超现实主义运动,他们标榜的是一种另类的、“在野”的方式,看起来要和学院的方式不太一样。在视觉风格、艺术理念、组织形态、宣传模式等方面,他们却又是向东京和巴黎看齐的,这是一股席卷全球的求新求异、求个性发展的艺术潮流。
1884年,巴黎成立了独立美术协会,引发了近代欧洲画坛天翻地覆的变化,继而向全世界传播扩散。上世纪30年代,独立美术协会旅行到了东亚地区。1930年,日本的独立美术协会成立。1935年,留学东京的一批中国前卫艺术青年也效仿了这一组织模式,这构成了“独立美术协会”全球旅行的现象。
无论是发起决澜社的倪贻德,还是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的梁锡鸿,他们当时在东京留学,对艺术的理解,包括对都市文化的体验却是巴黎化的。他们在内心都普遍有这种诉求:在东京上野公园挤满了看展览的人群,中国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一个繁华的现代文明景观?中国如何才能赶上西方先进国家?他们看到,正因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都云集在巴黎,才导致了巴黎成为世界艺术之都。他们深感作为现代中国艺术家,必须对这样的时代潮流有所回应。
谈价值
“他们对艺术有独创性的追求”
南方日报:你怎么看待他们在那个时代不合时宜的艺术追求?
蔡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潮下,他们所倡导的超现实主义的艺术运动,在当时是一种激进的青年文化的产物。上世纪30年代,他们是前卫艺术运动的弄潮儿。
在他们的内心,东京、尤其是巴黎,是个无法回避的参照系,但回到中国的现场,他们发现建立现代艺术是非常困难的。1935年他们从日本回国后,在广州举办的展览几乎无人问津,后来不得不移师上海,在中华学艺社办了一场也就匆匆结束了。他们面临的是这样一个窘境:他们由衷希望在中国建立起类似巴黎派那样的精英型的现代艺术,希望建立一种绝对自由的创作精神,但抗日战争的爆发,他们的梦想很难延续下去了。
但即便是在战争时期,他们也还是做出过一些努力。例如1939年,梁锡鸿与何铁华、倪贻德在香港岭英中学进行过合作,也就是在今天最豪华的铜锣湾购物中心这一带,创作过两幅超现实主义的大壁画,反映抗战这个主题。赵兽抗战时期也画了一些宣传画,但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早年追求的超现实主义已经不合时宜。
赵兽在文革时期还秘密地创作了一批前卫风格的油画作品,在几乎没人知道的情况下完成,堪称奇迹。他的创作很长一段时间是无人知晓的,他在被下放的偏僻农村仍然以超现实主义的风格秉笔直画。
经历了抗战、文革阶段这两位艺术家,虽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被遮蔽了,但是他们的实验性创作、在孤寂的创作环境中与内心的对话,都彰显出可贵的品质。这些在那个特定年代里完全没有展示机会的作品,却具备了他们早年所向往的现代艺术价值——高度的独创性和针对当下社会的批判意识。在欧洲,超现实主义正是在一战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带有社会批判的维度,而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的成员们,在1930年代的现场,是缺少这种意识的,但他们反而在之后半个多世纪的变迁里升华了对艺术的认知和表达,当然,这是个无比艰涩压抑的跋涉过程。大家在1970年代末期都知道有星星画会,无名画会,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在广州,还有这两位被淡忘的老牌前卫艺术家。
谈评价
“要考量艺术家的历史超越性”
南方日报:对比上世纪80年代国内兴起的现代主义美术运动,梁锡鸿、赵兽早年的探索有何意义?
蔡涛:有意思的是,赵兽在梁锡鸿去世之后为梁锡鸿画了一个肖像,也为自己画了一幅,两个人在画中都身披大衣,画面中有“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几个大字,如同为这场现代派艺术运动中的两个领袖人物树碑立传。
在外人眼里,赵兽可能有点疯癫,但赵兽在那么长的残酷岁月之中,早已经形成了自我循环系统,他画画并不是为了更开放的环境,早已经不在乎名利和外人眼光,他是为了自己的内心创作——因为他是一个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现在涉及到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评价1949年至1979年间中国现代艺术的形态?比如“无名画会”,有人做研究时就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前卫美术团体,其实是无知的说法。民国时期就出现过前卫美术团体,如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在上世纪30年代,留学东京的那一批广东艺术青年已经拥有了美术的新思维,拥有了和世界对话的格局和行为方式,他们身处东京,眺望着巴黎。
当然我们也不禁要发问,我们的当代美术史写作应该把梁锡鸿、赵兽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在那段思想禁锢时期出现的这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的价值?我们需要提出新的评价标准,把一个艺术家在某一社会阶段所具备的超越性纳入这个评价体系。因为这样的超越性,对于学习美术史的人来说,构成了相当的魅力,值得我们反复咀嚼。
- >>相关新闻
- • 以艺术之名 向时计致敬
- • 萌萌哒:故宫推出《皇帝的一天》儿童iPad版应用
- • 美画家拥有罕见4色视觉:可见颜色为常人百倍
- • 我们究竟走了多远——反省中国当代艺术
- • 画家许翰政:从画者的角度思考绘画
- • 《百岁图》源于传统锦灰堆绘画 技艺至今为谜
- • 别让艺术沦为金钱的奴隶
- • 飞鸟与鱼的若即若离:艺术家手绘的玻璃装置艺术
- • 文艺不分家:那些文人和画家之间的传奇故事
- • 文化艺术政府奖动漫奖颁奖 天津动漫摘四项大奖
- • 白鹅画会创始人陈秋草与业余美术教育
- • 2014美术报年度人物候选人名单
- • 西安美院庆祝建校65周年 刘大为刘文西等出席庆典
- • 中国美协副主席许江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 • 日本近代公立艺术学校女裸体模特一号诞生记
- • 第二批国家重点美术馆评估工作即将启动
- • 首届北京“大艺博”思考:学生作品缘何被抢购
- • 民国美术史的再发现:孙佩苍及其收藏展举办
- • 记录三十年 开发区美术书法摄影获奖作品展开展
- • 高淘汰率的背后:美术生离画家有多远

- • “画说天津”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研讨会
- • 苍劲恬然凝重朴实—李克玉书画作品评析
- • 水墨计(肆)十二人展将启幕 天津美院薛明入展
- • 王书平:与潘基文谈画的“东方鹰王”
- • 《光环的背后:我与名人》首发签售会11月2日举行
- • 百年书香 艺术精品——《华世奎书法作品集》出版
- • 天津文化旅游周暨东方艺术展在东京开幕
- • 圣地·后素—姚景卿姚铸国画精品展寿光举行
- • 书画家梁旭华的艺术世界:以字入门缘定山水
- • 挖掘传统 借古开今—薛永年谈李毅峰的山水画艺术
- • “荷语—郝跃先个人作品展”在天津空港经济区开展
- • 韩必省书画作品展暨慈善捐赠活动在北京举行
- • 天津美院教授著名画家何延喆80年代山水画课徒稿
- • 天津艺术家张羽:毛笔皴擦掉了当代水墨精神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