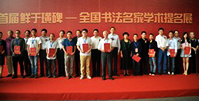-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学生眼中李叔同:气质高雅不怒自威朴实无华

李叔同油画自画像
1912年起,李叔同在位于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浙一师)任图画、音乐教师,1918年出家为僧,即弘一大师。弘一大师后致函在天津的 俗侄李圣章时,总结过自己的教学生涯:“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
杭州人吕伯攸1913年入浙一师就读时才16岁。在他的眼里,“穿一身漂亮的西装、微微地有些髭须”的李叔同就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艺术家”,而“蒙先生另眼相看,却是因为在课外曾经请先生教过诗词的缘故”。“我和先生,也是比较接近的学生中的一个。”
吕伯攸1918年毕业后成为作家。在此后三十余年的为文生涯中,他对业师李叔同的恩谊念念不忘。笔者已发现吕伯攸发表的相关回忆文章6篇,且所述内容大多鲜为人知,值得披露。
气质高雅不怒自威
吕伯攸《绰号》一文记载,在浙一师“读书的时候,上有校长,下至清洁厕所的粪夫,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绰号的———如果一定要说出一个没有绰号的人来,那便是后来出家为高僧的弘一法师,也就是当时教我们音乐的李叔同先生。”
“他是我们最敬仰的先生。我们对于他,自己也不知道为甚么,总觉得是高不可攀似的。我们虽然从来没有受过他的调责,可是,对于他教的功课,谁都诚心诚意地只想做得好。目的并不在分数,仅仅希望他,不要为了自己的功课荒废使他感到一些不快。”
吕伯攸《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一书记载:“个子是修长的,面貌是清癯的,态度是温温穆穆的。当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伟大人物的时候,会把一切贪鄙、欺妄、嗔怒……完全消减。”
“先生的服饰,不久便由西装改为布袍布褂,上面除了几条应有的折痕以外,没有一丝皱纹,穿了数年,终于也找不出一点尘垢来。到现在,我仿佛还看 得见他一进教室,便把那件黑布马褂脱下来,谨谨慎慎地折起来,搁在那架钢琴上的神气。”“他的容止气度,不知道为甚么真有那样的力量,使个个人都胁服于 他,谁也不敢发出一些声息来。虽然他是那么和悦的对待我们。”也许这就是因气质高雅而不怒自威吧。
和蔼可亲朴实无华
李叔同任教时,总是亲切和蔼的,从不拒人千里。吕伯攸《李叔同先生诗词》中载,同学们经常“从先生学诗,每遇休沐,辄同听啼莺于西泠,或共赏明月于苏堤。‘六桥三竺’之间,时有余辈足迹。”
李叔同指导学生也总是认真负责、无微不至的。吕伯攸又写道:“那时候,我曾发起组织过一个‘嘤鸣吟社’,导师就请先生担任。有一个时期,我竟至 把各种功课丢在一边,专门躲在自修室里作诗填词的。先生也乐于指导,常常在一个清晨,就差校役来把我叫了去,拿出我隔夜缴去的诗词,当面用朱笔替我改削, 并且随时给我说明要这样改削的原因。”
吕伯攸1944年撰《黉舍忆语》回忆,他曾多次到过李叔同的居室:“我因为常常到他那里去请益,对于他居室中的一切,比较一般同学是相当地熟识 的。在那里,除了明窗净几、洁无纤尘以外,最使我注目的是书架上高供着的一个花雕酒坛。坛上绘着金碧辉煌的粗线条图案,在常人看来,觉得非常平庸,先生却 以为包涵着无上的美。坛中插芦花三四枝,美点何在?更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书架中格,陈列着一排江北人所制的泥人,当然较诸无锡惠泉山的要拙劣得多。壁 上饰着的,并不是中西名画,却是从中外各国的火柴盒上剪下来的图案。这是先生卧室中的情形。隔壁还有一间同样的房间,布置却简单得多了———中央仅置长桌 一张,桌上有笔砚画具等等,旁边杂置几椅数事。那是先生写字作画的地方。”
居室摆设竟然如此朴实无华,颇令吕伯攸惊讶。而在这个环境中,吕伯攸一下子就沉静了下来。返璞归真的确不是一种容易达到的境界。透过吕伯攸的回忆,或可品味李叔同对艺术的理解。
李叔同出家前,赠给吕伯攸的“一幅横披,却是先生写的‘至诚’两个字”。这让吕伯攸如获至宝,遂将“至诚”奉为圭臬。
不仅是书法,李叔同对茶亦有研究。吕伯攸在《秋长在室茶话》忆及:“虎跑寺有泉水,清冽而稠……戊午仲夏,业师李叔同(即弘一法师)先生披剃于 该寺。余曾偕学友数人,一度往访。师出龙井茶,汲该寺泉水,烹以饷余等。”可见在学生眼中,李叔同的确是一位从形象气质到知识学问,均能对人产生影响的老 师。
- >>相关新闻
- • 记《弘一大师李叔同篆刻集》新编增补本编辑出版
- • 《弘一大师李叔同篆刻集》新编增补本一书在津首发
- • 其观清华:王家训人物画的艺术精神
- • 笔古墨润夺天工--《唐静岩司马真迹》再版有感
- • 悲欣交集:天津已无李叔同,世上已无李叔同!
- • 文人与蟹:齐白石画螃蟹讽日军横行
- • 中国写意画一代宗师李苦禅
- • 李叔同徐悲鸿都曾参加过民国第一届全国美展
- • 采花大盗美籍华人画家丁雄泉之花犹盛放
- • 梅兰芳:京剧大师里最会画画
- • 从马一浮书法感悟文化高度与孤神独诣
- • 朱万章:人文关怀与关山月人物画
- • 李叔同作品《半裸女像》亮相南京 曾消失近百年
- • 纪念李叔同-弘一大师诞辰135周年书画作品展开展
- • 吴瀛:故宫博物院的忠实守护者
- • 看岭南画派巨子赵少昂的艺术足迹
- • 丰子恺:最怕的是叔同先生那回头一顾
- • 感恩西泠印社的篆刻才子傅其伦
- • 600岁太庙造出艺术馆 李叔同名作亮相开馆展

- • 张善军书法作品展11月28日在中国书法展览馆开展
- • “劳作”马树青个展将于11月28日在798艺术区开展
- • 天地成经纬 水墨筑“大家”—我所了解的庞黎明
- • 溪山流韵-天津山水画南京邀请展12月13日开展
- • 范敏版画作品展12月5日在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
- • 飒韵叠翠-陆福林个展将于11月28日亮相乾庄书画院
- • “丹青映和”肖映梅中国画展在扬州八怪纪念馆举行
- • 张志连丙申年台历欣赏:月月嗅花香 日日闻啼鸟
- • 第九届和平·枫叶杯全国连环画创作大赛评选揭晓
- • 天津南阳友谊长青—天津百中国画院赴南阳采风侧记
- • 组图:悠悠的心灵牧歌——观高建章油画有感
- • 盛世芳华—民进成立70周年书画摄影展开幕
- • 刘玉社小幅水墨新疆山水画作品展在津开幕
- • 第八届全国著名花鸟画家作品展开展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