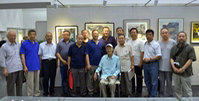-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大芬村调查报告:美国众议院“博弈”深圳大芬村

深圳大芬油画村
美国众议院“博弈”深圳大芬村
2014年8月6日上午,一辆载着18位美国众议院成员的大巴停靠在深圳大芬村大芬美术馆前面的停车场,从车上走下的这些美国人的注意力显然不在正在展出“可见之诗——中国油画风景作品展”的大芬美术馆,而是在拒绝中方任何人员陪同带领的情况下,分头走遍了大芬油画村各个街区的每一处角落。从抵达大芬村,再到离开,仅仅在半个早上完成,这些美国众议院成员单独行动,也不向其他人透露此行的目的,显得十分神秘。

曾经的油画生产
在大芬村所属区政府的对外宣称中,将美众议院成员的“到来”视作正常的外宾访问,因为他们也并未向中方说明此次大芬之行的真实目的,但据雅昌艺术网记者们接下来数天的走访发现,美众议院的这次行为虽然是临时确定,但绝非单纯的旅游观光,一些略微知情的人士也透露出他们的可能目的——“他们到来可能别有目的,或许是在考察大芬村目前是否依旧存在作品侵权的问题”;从走访的一些店家口中也证实了起码深圳政府单方面存在着这方面的担忧——在美国人到来的数日前,五组“有关部门”人员对大芬村进行了地毯式排查。
美国众议院成员最终的“检查”结果可能出乎作为旁观者的我们或许存在的期待爆炸新闻的预料,最起码在现场,他们没有找到涉嫌侵犯版权的油画,甚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乐呵呵地购买了”一些在大芬美术产业协会的管理人员视作“原创”的油画。“检查”结果如此,却仍然让我们颇感惊诧,这种惊诧不在于大芬村惊动了美国众议院,而是对我们“大芬村油画=复制、模仿的行画”这一既定印象的颠覆,让我们有兴趣探索大芬村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后都有了哪些变化,是何种原因促成了它的转型,它曾经又是如何形成我们记忆里的那种面貌的?

大芬油画村入口处宣传黄江的海报
点燃大芬油画的星星之火
“大芬”一词,首次出现在嘉庆二十三年编纂的《新安县志》中,一个边缘而又古老的客家村落,那里的居民,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如今的大芬村会通过文化与市场的力量,奇迹般的成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版权兴业示范基地”、“美术产业示范基地”。
据大芬美术产业协会秘书长周峰介绍,大芬油画村的形成与一位名叫黄江的香港画商密不可分,我们现在仍可以在大芬村的主入口处右侧见到黄江的宣传海报,他被大芬村冠以“大芬人的骄傲”,大芬油画的“创始人”、“第一人”、“奠基人”等称号,如果能够给大芬油画村的发展转变进行分期的话,起码在头十年,即大芬油画村的自发发展阶段,则可以被称作“黄江的时代”。
黄江的徒弟黄通介绍,黄江生于广东四会、长于广州,“文革”期间因其艺术方面的功力而被领导委以文艺宣传工作,1970年移居香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工经历如做焊工、当调酒师之后,心有不甘而重拾画笔,做起了商品油画生意和开班授徒。1986年开始因商品油画订单而应接不暇,并且为全球零售业巨头沃尔玛供应油画,加上他发现深圳作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有着很多政策上的优惠,于是,黄江来到了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罗湖区的黄贝岭召集画工,开办油画工厂。1989年因为二线海关的阻隔,内地画家难以进入市区,以及黄贝岭租金的上涨,黄江把油画工厂搬至如今的大芬村。

今天的大芬油画村
就在那一年,黄江带着自己招募来的26位画工进入了大芬村,“那时候大芬很荒凉,像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那样荒芜。村民连300人都不到,到处是芦苇。但是租金很低,200平方米每个月才1500元”,黄江回忆说。正是在这种情形下,黄江开始了国内当时少有的油画加工、收购、出口的业务。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一些绘画爱好者、美术学院学生,甚至小有名气的画家纷至沓来,行业逐渐兴盛,开启了大芬油画的第一页。
之后,大芬村的发展十分迅猛,在黄江进驻大芬的三年后,就有不少香港和内地的商人陆续来到大芬村,而那时候的黄江已经发展成为最大的商品画经销商了。到了十年前的2004年,据周峰介绍,“整个大芬村,包括茂业书画交易市场,共有书画、工艺等经营门店243家,其中从事油画生产和销售的有145家,从事国画、书法创作和销售的有55家。”如今,大芬村则拥有40多家企业和1200多家画廊、工作室及画框、画材等经营门店,村内从业人员8000人,加上散居周边的从业人员,总人数则超过20000人,创造的年总产值(2013年)高达42.6亿元。

曾经大芬村的绘画生产
效益孕育下的自发发展模式
最初,大芬村“生产”出来的油画绝大部分经香港转销国外,走俏欧美、中东、非洲十多个国家的艺术市场,“国外的订单不出村也能够自我消化,出口的油画占据了市场的百分之六七十之多”,黄通说。而据大芬美术产业协会的介绍,到2004年,大芬油画村全年的销售额首次突破了亿元大关,达1.26亿元,全年行画的制作总量更是达百万幅之巨。
在黄江本人接单的历程中,最辉煌的时候,“大概是在1992年4月,25cm*23cm的油画一个半月要完成36万张!”而为了在一个半月内完成这个订单,黄江聘请了2000人作画,并且“把订单分散开,一部分给广州,一部分给东莞,当然大芬还是最多的”。为了加快生产速度,黄江所采取的是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方式,把作品的题材元素拆解,并将之分配至善于绘制某一题材的画工手中——擅画天空的只画天空,擅画水的只画水,每一位画工完成他的内容后,再传至给下一位画工。“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行画成本比较低廉,质量比较稳定,出货、数量、时间都还比较靠得住。它们基本上是成批量的,一个货柜、一个货柜的生产”,深圳大芬艺海拍卖行有限公司董事长贺克说。
贺克也是较早来到大芬村打拼的一位,先后有着画工、画廊经营者、企业家、大芬美术产业协会会长的多样身份。据他介绍,大芬油画发展到世纪末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的小作坊,“由一个带头人,到深圳罗湖商业城、博雅画廊等地方接单,因为罗湖商业城靠近关口,很多外国人专门在那里下单,他接好了单以后我们来画。如果下单者卖300元一张画,带头人接单的价格只有一百多了,到我们画工手里高的才60元钱”,贺克说,“像我这种比较不安分的,就自己单干了。因为之前要交老板伙食费、住宿费、佣金,一个月画下来赚的一点钱全部交给他了。那时候在大芬村租一个小店面并不贵,我记得是400元还是600元一个月,40多平米。开始一两个月没有什么生意,之后就不同了,罗湖商业城开始有商家直接找到我,一传十,十传百,他们就直接找我们下单了,很多人都是这么做起来的”。
大芬村规模的自然膨胀逐渐引来了海内外一些媒体的关注,随着媒体的传播,大芬村的名声开始远扬,很多人开始慕名而来,价格很低的行画在较富有人的手中逐渐抬高,本来百元级别的行画被抬高至千元,太多买家因为满意大芬画工的制作,甚至还会主动抬高价格作为奖励,两种主要行画的生产模式,都逐渐站稳了脚跟,与油画相关的产业逐渐多了起来,正是在大芬油画村名声享誉世界的同时,也招来了前所未有的批评。

大芬油画村
市场转移带来的大芬危机
这种批评即大村油画村在过去广泛存在的“艺术品”复制、盗版情况以及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也可能是由于这种批评的缘故,大芬村才引起了美国众议院的关注,“企图在这里找些茬”,大芬村一位店面经营者说。
第二届大芬美术家协会名誉会长蒋庆北认为“那些做文化产业的,他们所生产的画很容易被模仿,尤其在小作坊的油画生产及大芬村的画廊行业里,一件好卖的艺术作品或者一个畅销的艺术风格会很快的被同行抄袭”,这种抄袭导致的是绘画商品的同质化竞争,同质化竞争产生的结果是商品价格的不断恶性拉低,导致利润的逐渐缩水。然而,大芬村的现状及消费水平已经不允许过低利润行画的存在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大芬村的原始产业模式是从欧美地区转移而来。因为欧美的人工成本、生活成本的逐渐高升,以及发展战略的调整,使得这种手工产业发生转移,而代之以高新科技。周峰说:“这种手工产业首先转移到第三世界中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最先转移到的地方如‘亚洲四小龙’,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改革开放,与‘亚洲四小龙’间还有一个巨大的落差,这种产业就落地到了韩国和中国的香港地区”。
随着‘亚洲四小龙’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看到,那里的这类产业也已经完成了这种转移,也就是经由黄江,从香港转移到了深圳的大芬村。而目前,国内由深圳转移到福建,国外则正在朝着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转移。
转移意味着曾经所在地此类文化产业的彻底消失,而与此共时的继续得以生存的方式则是转型,但这种转型是需要条件的,周峰说:“像曾经香港的皇后大道,现在已经是商业区,即便在当时转型成功也不会取得如今的商业价值,所以就直接转移了;而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这些地方是没有时间转型,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得太过迅猛,如果它们有时间可能也会转型升级,像纽约的SOHO,法国的左岸,英国的南岸艺术区,在这些地方,艺术跟商业、旅游结合做得很好,尤其是法国的旅游产业。”
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吸引力太大了,随着我们进一步发展,大芬再不转型升级也会面临着同样的处境,现在越南已经有类似的画家村存在,他们的成本比我们要低很多,就商业利益而言,购买者在选取相同产品时往往会选择价格较低的一方,单就这一点,大芬村不再具有优势。周峰认为,现在的大芬村还是有机会的,并且已经开始了转型的进程,“如果拼最低价格,你就没得玩了,未来非洲更低。我们的转型一定要做别人做不了的,一定是以原创为核心、以原创的‘版权’为核心,唯有这样才能把大芬很好的发展下去。”

- • 天津杂项藏家张耀庭:藏天地间那杆良心秤
- • 刘曦林谈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中国画评审工作
- • 法外求化—王俊生大写意画展于11日举行
- • 《王俊生画集》由天津人美出版社出版
- • 第五届国际文化创意展交会闭幕 文化创意改变生活
- • 天津五大道疙瘩楼:可以吃的博物馆
- • 南开大学诗词楹联学会、南开大学书画社慰问交警
- • 著名书法家封俊虎走进《中国正能量》解读学术观点
- • 组图:天津画马名家蔡长奎收康柏林为徒
- • 天津民间艺术精品博览会展位全部售出
- • 全套漫画版中国四大名著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发行
- • 张映雪家人向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捐赠珍贵年画
- • 画家马寒松畅谈作画心路:真情使然 水到渠成
- • 刘奎龄画派艺术作品展今开幕 汇集20多位画家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