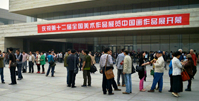-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侯宝川——大凉山的描绘者 凉山风景的守望者

“以心观境”——侯宝川油画作品展将于本月31日在四川博物馆举办,此次展览是侯宝川三十多年来风景创作的中型回顾展。大凉山一直是侯宝川风景创作的永恒主题,他是大凉山风景的守望者。他为何如此心系大凉山?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如此痴迷风景题材的创作?他的风景创作与“伤痕美术”、“乡土绘画”又有着什么样的文脉关系?他的风景创作,以及他对大凉山背后的文化体验在三十多年的线性发展脉络中有着怎样的变化?希望通过此次访谈以及本次展览,呈现给观者一个完整而清晰的答案。
记者:此次展览“以心观境”与前不久的“情凝沃土”展有哪些不同?
侯宝川:在展览架构上两个展览差别很大。“情凝沃土”只是我的写生展,虽然写生对于绘画而言极为重要,但这也只是一种素材的积累。对作品技法、思想性的完整性的呈现来说,“情凝沃土”要比即将在成都举办的个展碎片化一些。写生展的作品有很多即兴表现的因素,是一种在场的有感而发。“以心观境”是我的一个中型回顾展,是这三十年来对我风景创作的一个脉络梳理。主要是通过此次展览能呈现给大家一个稍微完整作品面貌,让别人能够了解侯宝川是如何走过来的。此次展览还专门组织了学术研讨会,并全程录像、录音,我想我会花上数月的时间去认真琢磨批评家的意见,慢慢从批评家的角度去挖掘他们对我的作品的评价和对我后期的期望,我也希望能从中找出一条路子,因为接下来的作品在表现形式和语言上会有一些变化。
记者:作为四川美术学院的副院长,为何56岁才举办个展?
侯宝川:作为川美的副院长,按理来说56岁才办个展的确好像有些不可思议,因为现在许多青年艺术家二十几岁就已经办过个展或数次个展。但是我觉得人和人不一样,大众媒体前两天也是围绕这个问题采访过我,甚至直接将这个问题直接作为标题。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无所谓,因为这么多年以来,我始终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学生,觉得自己在各方面还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甚至这次个展对我而言,是一次艺术经历的梳理,也是一种自我鞭策,希望能从中发现自己的问题和不足。艺术家对艺术要有敬畏之心,要踏踏实实地去搞创作,爱艺术,就要耐得住寂寞,才能厚积薄发。再说,我这人的确很笨,就只能边学习边创作,办个展早一些晚一些并不是最重要的,当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办展览就成为自然。
记者:您是1986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那当时“伤痕美术”、“乡土绘画”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
侯宝川:我是1983年考进美院,考了五年才考进美院,因为当时考美院很难。1982年、1984年中国美术馆两次举办“四川美术学院油画赴京展”,当时罗中立的《春蚕》、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开始亮相,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共鸣。虽然他们的年龄比我大一些,但那个时代我们有共同的经历,我在上大学前也当过知识青年下过乡,当过工人,做过中学教师。我们都经历了“乡土绘画”、“伤痕美术”的过程,体验过那段历史,其实也不仅仅是艺术史的见证者。“乡土绘画”、“伤痕美术”的艺术史价值我们都无需赘言,但我们真的对这段历史是有比较深的感情在里面,甚至我们对那里的乡土本身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我们这代人的“乡土情结”特别明显,就是因为能在那里找到一种回归的感觉。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钟情于题材,我仍钟情于我的大凉山,虽然我也时常带学生到重庆周边的古镇写生,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大凉山。但在艺术创作方面为什么我没有选择人物题材,可能因为我的性格以及和大凉山的环境有关系,大凉山很苍凉、很贫瘠,那些少数民族非常能吃苦,我也深受他们的影响。我觉得是这片土地赋予了我们这种性格,所以我觉得风景可能对我而言是最好的一种创作载体。

记者:为什么对大凉山如此充满感情?
侯宝川:我虽然出生于成都,我不到一岁就到大凉山,在大凉山长大。我父亲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军人,恰巧的是,凉山剿匪之后,我父亲这个没有文化的人被安排管理文化部门,不过有幸地接触了很多画家。当时凉山艺术馆、凉山报社也有很多美院毕业生在那工作,因此我也有机会经常看他们画画,耳闻目染地我也就喜欢上画画。但真正喜欢上大凉山,是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加而慢慢体会到的,大凉山不仅有一种刚毅的精神实质在里边,凉山彝族人民的吃苦耐劳精神,骨子里的那种忍耐劲都深深地影响到了我。这不仅是因为我个人的成长环境、个人感情的结果,还有我迷恋上大凉山背后的人文精神。
记者:1985年之后,乡土题材、风景题材经历了从非主流向主流转换过程,开始寻找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整体特征。这时候,您对“风景”又是如何思考的?
侯宝川:其实这主要是一个和国际接轨的问题,风景或者乡土越来越承担了一种象征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使命,像尚扬早期作品《黄河船工》,丁方围绕西北乡村所创作的《城》系列都可以看到这些影子。当时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在风景所呈现出来的本土性因素做过调整。1986年的毕业创作带有明显的“乡土现实主义”特点,其中一张是表现彝族葬礼的油画《更生歌》,其实更生和凤凰涅盘性质相同,认为人死了以后只要通过火化便可获得到新生。彝族人对生和死都用一种歌颂的形式来表现,新生命的诞生他们很高兴,一个人离去的时候他们也不悲伤,我觉得是一种超然的境界。
留校以后,西方的艺术理论、艺术流派在国内已经广泛流传开,我也开始学习西方的艺术语言为己所用,但这仅仅是一种语言方法,如何真正地用来解决我们文化或艺术本身的问题,却仍然处于一种迷茫的探索之中。
记者:从艺术史来看,乡村题材逐渐从人们专注的视线中消失。为何你一直在坚持画大凉山的风景?
侯宝川:作为一个艺术家一定要清醒,不能去跟风,艺术家还是要有自己的主见。捕风捉影的结果,可能自己就稀里糊涂将最初的东西放弃了,把自己最熟悉,最喜欢的那部分消解掉了,用不熟悉的方式去表现你熟悉的东西是绝对不可取的。所以刚才提到,一些艺术家的风景题材,能够表现出所谓中华民族的磅礴气势,精神气质,那是他们的境界。我一直觉得,我只要立足西南,面向大凉山就已经足够了,不管大凉山是蛮荒还是狂野,我觉得这里是我的根,我深深的爱着这块土地。为什么钟情风景另一个原因,可能与我在学校的管理工作有关,由于学校的日常工作也比较繁琐,没有完整的时间去叫我仔细钻研人物画那种细腻的情感表现。所以,偶然面对自然,自己的心胸好像一下子就开阔了许多。工作上的压力,以及工作上所受的委屈和不理解完全都得到了释放,甚至在画画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根据自己主观意愿去自由呈现,有时候能完全体会到陶渊明那种寄情自然的快感。

记者:或许这就是你所说的一种回归。
侯宝川:我的风景创作从2010年开始出现“路”的形象,甚至围绕“路”展开一系列的创作尝试。在大凉山的确存在这样一条路,但作品中的“路”只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可以引发出各种对它的阐述和理解,它有很多的可能性,比如它可以代表着现代、科技和信息等新时代之路。另外这个“路”还有一个指向,过去大山的孩子总是盼望着出来,现在我的“路”都是往里走,因为我想进去。这或许和“围城”一样,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我在外面工作这么久后,我真的是很关注凉山里的发展,我发现彝族的文化脉络也慢慢出现断裂,现在彝族青年开始穿上了牛仔裤,擦起了口红。我的一些朋友在凉山做美术教师,他们宁肯去丽江、上里、重庆等地去写生,自己守着这么好的地方都不去画。而我们这些走出来的人,却拼命地反过来往回走。我为什么要回去,我觉得大凉山的文化是不能丢失的,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东西是很惨的。
记者:希望大凉山文化、凉山人能沿着你笔下的“路”回到本初,找回那份难得的简单和纯朴。
侯宝川:大凉山民风很纯朴,但是现在出现了吸毒、贩毒、艾滋病等现象,一些最民族、最本质的、最本分的,最善良的东西在逐渐丢失,这是非常可悲的。我自己创作的时候都在想凉山不能再变,再变民族性的因素就荡然无存了。大凉山经济很落后,因此他们向往发展,向往发达,但不能采用一种非常规的手段。
记者:相当于整个中国现代文明进程的一个缩影?
侯宝川:是这样的,现在那里的一些人已经不是靠勤劳致富,而是靠一些投机,一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取个人利益,这个过程丢失了纯朴的民风、道德层面的东西,也丢失了大凉山的精神。我每次回大凉山都是带着喜悦而去,又带着一种恋恋不舍的感情离开,看见我们的凉山在变,不管是城市化建设带来的变化,还是凉山人骨子里的气质,甚至都会带给我一种陌生感。虽然大凉山的风景还在,但它承载着彝族人的感情、民风却都在渐渐消失,最可怕的是大凉山最后只能成为一代人情感和文化上的记忆和想象。
过去,我是对着大凉山画大凉山,仅仅对大凉山风景的一种客观再现,后来我越来越加入一些主观表现,一种意象性的表现方式,因为那才是我想要的大凉山。艺术语言的变化和主观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密不可分的,在艺术语言的表现形式上我更倾向于语言的单纯化,更富有一些诗意的意境在画面中,至于那些表象的笔触、色彩我像越来越简化一些,但是隐藏在画面背后的思考却越来越多了。
记者:这是否就是此次展览“以心观境”的核心,也就是说你越来越重视通往风景的“心灵”通道,或者说风景的回归本身?
侯宝川:的确如此。过去对景物只是一种对形式构成的冲动在里边,现在更多的是从心灵深处看待这种景物,因此不一样。为什么我要坚持画写生,其实写生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与自然接触的那种感情,那种与自然接触中心里的微妙变化。通过积累,通过心理的思考,从而挖掘出不同于别人对大凉山风景表现,这条路还很漫长。
- >>相关新闻
- • “总统府”晴空万里:一幅油画背后的历史真相
- • “荷语—郝跃先个人作品展”在天津空港经济区开展
- • 当代中国历史画:我这样画你到底对不对?
- • 朝鲜油画市场升温 质优价廉备受青睐
- • 马克·夏加尔:他的画板只有爱的色彩
- • 第三届大学生(广州)艺术博览会将于12月开幕
- • 用笔触勾勒土地的质感——张绍杰个展将亮相798
- • “美丽家园”油画家申树斌个展亮相新加坡
- • 海派艺术巨头王元鼎陈巨源齐亮相LOHAS艺术博览节
- • 墨西哥国宝级艺术家迭戈·里维拉展亮相中国美术馆
- • 何多苓:重要的不是艺术,是感受
- • 光景常新:唐寅油画展北京798圣之空间展出
- • 古棕油画作品展纪念梅兰芳先生诞辰120周年
- • 第四届中国西部美术展油画年度展评选揭晓
- • 寂·谧——朱东升油画个展将亮相上海
- • 全国美展油画展何以出现八幅躺在沙发上的女性
- • 江苏省美术馆举办“大师展” 一天观众超五万破纪录
- • 油画中国化百年之争:中国油画天生色弱是否难弥补
- • “满园春色关不住—呼鸣油画展”在济南开幕
- • “大写艺”唐勇钢油画展在杭州大瀚画廊举办

- • “画说天津”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研讨会
- • 苍劲恬然凝重朴实—李克玉书画作品评析
- • 水墨计(肆)十二人展将启幕 天津美院薛明入展
- • 王书平:与潘基文谈画的“东方鹰王”
- • 《光环的背后:我与名人》首发签售会11月2日举行
- • 百年书香 艺术精品——《华世奎书法作品集》出版
- • 天津文化旅游周暨东方艺术展在东京开幕
- • 圣地·后素—姚景卿姚铸国画精品展寿光举行
- • 书画家梁旭华的艺术世界:以字入门缘定山水
- • 挖掘传统 借古开今—薛永年谈李毅峰的山水画艺术
- • “荷语—郝跃先个人作品展”在天津空港经济区开展
- • 韩必省书画作品展暨慈善捐赠活动在北京举行
- • 天津美院教授著名画家何延喆80年代山水画课徒稿
- • 天津艺术家张羽:毛笔皴擦掉了当代水墨精神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