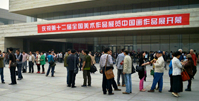-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画葵的艺术家许江:我们这代人三次被裹挟

许江1989年做了观念艺术作品《神之棋》。他思考过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的不同设定:“中国的士和帅是田字格里头出不去的,国际象棋的士和帅可以到对面去;中国的兵下到底线基本上没有战斗力,国际象棋的兵下到底之后,可以变成已不在棋盘上的任何一个子。”
“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天地本无心,此心就是核心价值观。”2014年10月15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许江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作这一番发言。天安门广场对面,国家博物馆的三个展厅里,正在展出他的个人作品展“东方葵”。
五十多幅大尺寸油画、百余幅水彩、一系列大型雕塑,描绘和塑造的对象只有一个:葵。这葵不是许江少年时在黑板报上画的向阳花——一个圈,圈里划成整齐的格子,格里点上籽,圈外边加上花瓣。这葵也不是某处风景的一部分,画面上除了葵,别无他物。许江的葵鲜见青葱的绿叶和灿烂的黄花,更多是铁一般的黑,铜一样的褐。苍凉原野里往往葵头低垂,葵叶凋萎,醒目的是成片葵杆依旧笔直挺立。
葵花向阳的比喻在中国古已有之。西晋文学家曹摅写“太阳移宿,葵藿倾心”,宋代词人詹无咎写“一寸草心迎永日,更把葵心自许”。而在新中国之后成长的几代人,自幼接触的葵花与太阳已有着更明确的指代。
“葵花向阳,没有比这个更能够表现那个时代我们国家的一种社会关系,这深深地烙在我们心上。”许江说,“我们都是向阳花,承受着阳光的沐浴。这个阳光是什么?可以是祖国,也可以是领袖。”
许江画的是老葵。2010年许江在浙江美术馆办“致葵园”画展,一位观众在留言簿上写道:“一支葵两支葵的残破,就是残破。一片葵的残破,那是一个季节,那是一代人。”
“东方葵将指向某个人群的历史性。这个人群正是中国‘文革’中长成的一代人。”许江在2014年元旦时一篇名为《东方葵》的短文中这样写道。
“它下雨,你要接受它”
许江留学时,在德国、奥地利的崇山峻岭当中,看过很多幸福的葵园。公路在山上崎岖盘旋,以为走到山穷水尽,突然一拐弯,阳光灿烂,一整个山垄的葵展现在面前,黄花灿烂。车赶紧停下,人奔到葵园里像是要拥抱它,“很疯狂,但也只是觉得美,不会自诩黄花”。
2003年8月,他在土耳其的马尔马拉海峡附近偶遇一片老葵,熟过而未收割,已是通体褐色,仿佛钢浇铁铸。午后的太阳已落到葵的身后,但葵还是朝向同一个地方,太阳曾经升起的地方。“真的像一批老兵站在那儿,等候最后一道军令。”再上车,走了一百多公里,竟是特洛伊古城遗址。大地之下,考古学家发现了分属9个时期的城市遗迹,层层叠叠。《荷马史诗》里的特洛伊战争时期是第七层,最久远的第一层城市,比它还要早一千多年。
刚看过一岁一枯荣的葵园和枯干的老葵,随即就是层积数千年的人类历史,许江再也忘不掉那一片老葵的景象。他在那葵上看到自己,咂摸着人生的短和历史的长。他找到了终生的绘画主题。从那开始他只画葵,研究葵,四处寻找葵,内蒙古、新疆、北海道……至今十余年。
中国美院的象山校园年年种葵,有时候整个校园都是葵,加起来有上百亩。有一年葵园成熟,正是毕业季,许江决定把毕业典礼放在葵园,让同学们穿过葵园来畅谈欢聚,来领毕业证。结果典礼当天一场雷雨,延续了一天。
那一年整个夏季雨来得特别多,眼看葵园就要腐烂,工人们赶紧收获。有200棵是专门留给许江的,连根拔了堆在教学楼外边,堆了两天,也快捂烂了。终于晴天,许江把这些葵杆倒悬着靠在栏杆上晒。有一瞬间,斜阳从背后打在倒悬的这个葵阵上,许江看到一面金色的瀑布,他画了倒悬“葵瀑”。
“那葵其实已经腐烂了,但是被阳光激活,让我感动。”许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腐朽与新生,凋谢与坚强之间,有时候冥冥之中真会给你一个不简单的答案。”
许江画横躺的葵。“葵的横呈,与直立相异,让人想到生者的倾覆。”
用在国博展览请柬上的作品是为展览新绘的《狂飙》,280×540厘米的巨幅油画。绘画从局部开始,葵株越来越密集,它们似乎自然生成了一个腾然向上的顺势,从边上又撞进来横斜的逆势,层叠、挤压、倾覆、挣扎。
“毛主席有诗词,‘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文革的时候有多少战报,都叫狂飙。我的《狂飙》像一个人的海洋,它被如此这般地组织起来,这是我这样一个葵花的真实感受。”
许江画葵,很少有大面积的绿和黄。即便名为《生如夏花》,也绝对不是鲜嫩的玻璃花一样的葵。“一定会有黄花在绿叶当中挤压出来的那种生命力,那种抗争的意思。这是我生命当中无法摆脱的,就是身不由己,必须这样。”许江说。
2012年,许江寻葵到了新疆。这里的葵一人半高,葵盘很大。农人拿着锋利的菜刀,抓住葵盘砍下来,再在葵杆离地面半米多的地方拦腰一刀,留下一个尖尖的桩,把葵盘戳在桩上。“没过多久你眼前的葵园,就像一片头颅插在它们的身躯上,我当时感觉这是一个屠场。这太残忍了。”
葵农眼里这再平常不过,就是晒葵罢了,葵盘晒干了一抖,葵花籽就掉下来。
“这可能是我们的幼稚,但也许这就是艺术家的一种很有趣的想象。”许江说,“什么叫荒寒,什么叫凋零,什么叫天地无情,万物刍狗……它不会因为你现在要举行毕业典礼我就不下雨了。它下雨,你要接受它。”
“我们这一代人被三趟火车裹挟”
“我们这一代人是被三趟火车裹挟的。”几个月前,许江在中国美院的毕业典礼上说。
第一趟车是1966年的“大串联”,数百万红卫兵涌向北京。许江只有11岁,也赶上了这股浪潮,独自从出生地福州坐火车到老家扬州,完成了人生第一次远游。“那时候风气很好,一路上多少人站着,为我能够躺下来睡觉。我走的时候,谢谢都没说一声。”许江回忆。
第二趟车是1967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许江从沙县一中毕业,17岁,去了沙县乡下当民办教师。他在一所完全小学教体育、音乐、英语,每星期三花三小时爬到山顶上只有两名老师的另一所完小,第二天早晨教两堂英语课:“Wish Chairman Mao a long long life(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下到半山,有所一个老师教四个年级的学校,再教两个小时的外语,再回到山下的学校。风雨无阻,将近两年。“有时候路上还画水彩,画云,老画不好,非常生气,又没有老师教。其实现在才知道云是最难画的。”
第三趟车,1978年,恢复高考招生。许江也赶上了,进入浙江美术学院读书,“很多人没有幸运坐上第三趟车。”
对自己的青年时代,许江记忆最深的是别无选择。“我们那个时代里没有东西可以选择,所以当你抓住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放的,你是拼命地去吮吸它。”
画作是匮乏的。“你可能发现一张图片,《狼牙山五壮士》,还不知道哪个人画的:哎呀,这辈子如果能画这个画可太好了!——这口奶是从这里过来的,后来才知道这是詹建俊先生的。今天呢,孩子可看的东西太多了,他却苦于选择,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不知道哪一口是他的奶。他那种彷徨可能比我们更充分,更难以解决。”
诗歌也是匮乏的。“《唐诗三百首》也都是封资修了。”许江读张永枚的《西沙之战》,读郭小川写伐木工人的《祝酒歌》,读贺敬之,读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那时候我们真以为,这条‘大堰河’是他的母亲河。”许江说,“那一代人的阅读非常有限,反而很集中,所以我说这代人群体性是太强了。今天的诗人,有一首诗多少人阅读这是很难的,网上能够有十万人点击你,已经了不得了。”
改革开放后,许江又赶上一回潮流:1988年,他去了德国汉堡美术学院研修,“洋插队”。学的是油画,他想现在可以在师傅面前舞舞大刀。结果人家说,别舞了,我们已经不舞这个大刀了。“我的教授就跟我讲,你画什么油画?我写书法怎么样?我说你那个书法太差了。那就是了,你的油画也够差。”
困惑中许江开始读书,外语还不够读书,只有跑中国书店。汉堡火车站边上一个香港人开的“天地书店”,现在已经不在了。有台湾的书,有香港的书,老板人很温和,允许他在那里乱翻书,从来不买。许江在德国开始阅读中国,很认真地读。“以前你读不到,”许江说,“中国的传统经典,本来应该是你手下心中的东西,但是由于文革,它变得很遥远。当你的故乡成为他乡的时候,你才会对它珍视起来。”
闲来跟外国同学下象棋,由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不同的设定、规则,许江思考起东西之间不同的文化、社会观念。“中国棋盘上有炮,这跟中国最早发明火药有关;中国的马是有马脚的,中国人说我可以别你的马脚,别死你。中国的士和帅是田字格里头出不去的,国际象棋的士和帅,可以到对面去;最有趣的是兵,中国的兵下到底线基本上没有战斗力,国际象棋的兵下到底之后,可以变成已不在棋盘上的任何一个子,这是否反映西方一种用人的体制呢?”
1989年许江做了观念艺术作品《神之棋》。用真人当棋子的巨大象棋,连下几天。回国之后,再下这样的棋,没有人看得懂,许江慢慢从观念艺术回到架上绘画。
世纪末逼近,全世界都处在对历史敏感的情绪里,他用大约几百年之后的目光,俯瞰北京、上海,艺术评论家巫鸿称他是“中国第一个画废墟的画家”。
发现葵园之后,许江回到大地。他在葵中发现了自我的况味,也看到了历史。“未来的历史画再也不是去画某一个场景,因为在媒体时代,这个场景已经被摄像机、照相机拍了无数次,不需要你再画。”许江说,“通过这个特殊的、沧桑的葵,我们看到了这一代人,看到了这一代人的历史性,这是历史画。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性是什么?回归东方。看起来我们始终向西,其实是归东。” (李宏宇0
- >>相关新闻
- • “花看半开”徐春丽个展798红鼎艺术开展
- • “玖零•光华”90级学生毕业二十年展开幕
- • “追求卓越:首届油画邀请展”举行新闻发布会
- • 无处可逃—当代油画艺术展在撃水艺术空间开展
- • “总统府”晴空万里:一幅油画背后的历史真相
- • 当代中国历史画:我这样画你到底对不对?
- • 朝鲜油画市场升温 质优价廉备受青睐
- • 侯宝川——大凉山的描绘者 凉山风景的守望者
- • 马克·夏加尔:他的画板只有爱的色彩
- • 第三届大学生(广州)艺术博览会将于12月开幕
- • 许江:关注视觉中国 弘扬核心价值
- • 中国美协副主席许江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 • 全国美展油画展何以出现八幅躺在沙发上的女性
- • 中国美术学院首次向入学新生赠送“文化礼物”
- • “三山”陈智安方勇徐钢山水画展将亮相今日美术馆
- • 许江:真正的葵园既在大地上又在人们心中
- • 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第一届甲骨文书法高研班
- • 油画作为艺术观和使命精神的核心思考
- • 东方葵—许江艺术展将亮相国家博物馆
- • 被唤醒的风景:焦小健作品展开幕

- • 敦煌壁画艺术精品展在天津美院美术馆开展
- • 丹青物语——黄雅丽庄雪阳国画作品联展开幕
- • 丹青缘—唐睿、何宁、杜小龙水墨三人展开展
- • “艺海清扬·近现代名家画展”在天津美术馆举行
- • 李军、路洪明赴美国参展“文墨儒风”
- • “画说天津”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研讨会
- • 苍劲恬然凝重朴实—李克玉书画作品评析
- • 水墨计(肆)十二人展将启幕 天津美院薛明入展
- • 王书平:与潘基文谈画的“东方鹰王”
- • 《光环的背后:我与名人》首发签售会11月2日举行
- • 百年书香 艺术精品——《华世奎书法作品集》出版
- • 天津文化旅游周暨东方艺术展在东京开幕
- • 圣地·后素—姚景卿姚铸国画精品展寿光举行
- • 书画家梁旭华的艺术世界:以字入门缘定山水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