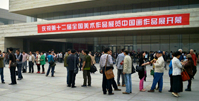-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20世纪中国美术钩沉:吕斯百大型艺术展侧记
然而对于大多数艺术爱好者而言,20世纪早期的中国油画,初看难免令人感到有些平淡,甚至乏味,吕斯百的作品尤其如此——几乎全部是平淡无奇的静物画与写生习作式的风景。既无刺激神经的图像、色彩,也无细腻逼真得令人惊叹的照相写实技法,甚至作品尺寸也那么不起眼,对于“身经百战”、“阅画无数”的当代观众来说,实在缺乏吸引眼球的因素——至少几位与笔者同行观展的朋友是如此反应,“这题材也太普通了,技法也没什么可突出的,水果、蔬菜这种静物写生画班学生也能画出来”,“这么保守,完全看不到30年代西方前卫艺术的影子”大家如是说。而展陈布置也并没有在美观的层面上为展览加分,本次展览仍保持炎黄艺术馆一直以来朴素且中规中矩的风格。展厅入口处依然是两面遥相呼应的文字墙,常来此看展的人可以熟稔地在此阅读展览前沿、艺术家生平等信息。作品基本是按照题材分类,再根据时间顺序排列,都规矩的挂在墙上,旁边贴着信息详实的展签,部分重要的或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附有成段的解读文字,从构图、风格、创作背景等多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然而不得不承认这样的陈列方式恰恰与早期中国油画气质相吻合,相对于一些华而不实的设计,更加纯粹,有助于观众获得欣赏艺术、沉浸于历史所需的宁静感。
几位已经不耐烦的朋友在笔者的劝说下仔细阅读了吕斯百的生平,了解他早期在法国的留学经历和四个主要创作阶段,之后在我陪同下重新观看了一遍展览。这一次我们不仅更加细致的观看画面,而且仔细阅读重要作品的分析说明——这些文字多来源于相关研究论文或知名学者对吕斯百的既有评价,显然展览策划者在学术史梳理方面颇为用心。虽然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难免会令观众产生先入为主的看法,影响对作品的自由感受和理解,但对于大多数观众,则有助于他们更充分的理解作品,且避免了与重要作品失之交臂。在观看期间,我们还在一些大家都认可和有争议的作品前交流和讨论,我们通过比较《读》(1929)和《人体》(1934),感受吕斯百在里昂和巴黎所接受训练的差别,以及他艺术上的成长;我们结合1942年吕斯百随中央大学迁移暂住柏溪农村的经历,体会他在《庭院》(1942)中流露出的与世无争的性格和对乡村的深厚感情;我们细读《野味》(1932)、《莴苣和蚕豆》(1942)等最具代表性的静物画,欣赏吕斯百简练而充满诗意的笔触,分析夏尔丹对他的影响。经过这一番品鉴,最初不以为然的朋友们都不得不承认,吕斯百的作品的确是需要细细玩味并且是经得起推敲的。而大家也都公认吕斯百的静物画和那些表现宁静田园或海滨景色的风景画,是最值得称道的,无愧于他“田园画家”的美誉。这样的结论不仅出自美术史家的定论,更是我们作为普通观者在深入了解艺术家生平和仔细观看原作后的真实感受。
视觉传达理论中广泛应用阿尔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视觉循环理论“了解越多,感觉到的就越多;感觉到的越多,选择的就越多;选择的越多,理解的就越多;理解的越多,记住的就越多;记住的越多,学到的就越多;学到点越多,了解的就越多。”对艺术作品的观看与理解莫不遵循这个规律,而吕斯百初看平淡的作品更是如此,唯有静下心来了解背景和细读原作,方能体会他笔触的轻松精妙、作品的高雅格调,更重要的是他赋予朴实的静物以情感生命的非凡才能。而且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不仅吕斯百的作品,许多20世纪早期的中国油画在今天看来都未免过于平淡与学院派,然而如果了解当时作为主流正统的法国学院与沙龙体系,就会由衷赞叹我们的前辈作为外国留学生在当时取得的巨大成就。
近年来对20世纪早期中国美术尤其是油画的关注逐渐成为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许多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一度被埋没、遮蔽的名字,重新被美术史研究者们钩沉出来并纳入美术史的书写,如赵兽、沙耆、决澜社、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包括这次的吕斯百,然而这仍然不够。例如今年8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孙宗慰个展,其实孙宗慰与吕斯百之间有诸多相似之处和关联——他们不仅是同代人与同乡,更重要的是同属于徐悲鸿写实主义教学体系,甚至后来被认为是孙宗慰创作转折点及高峰的敦煌写生,也正由于时任系主任的吕斯百向张大千推荐其为助手,才得以成行。假如研究者与策展人能对此前的学术成果与展览善加利用,巧妙借力,挖掘各艺术家、各体系之间的潜在联系,以及隐含在艺术背后的文化价值,为公众提供更多的背景知识,相信大家会更愿意主动去了解和欣赏20世纪早期中国油画,而不是在第二眼才提起兴趣甚至与精彩的艺术杰作失之交臂。20世纪中国美术的价值研究与推广依然任重道远。(陈琳 中国现当代美术文献研究中心(CCAD)研究员)
- >>相关新闻
- • "2014炎黄文化艺术节"——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 • 陈正雄:抽象画家要清楚自己在画什么
- • 少年行——彭建忠油画个展将在杭州开幕
- • “第四届中国西部美术展油画年度展”献上佳作
- • 东西方美术年展亮相卢浮宫 中国艺术大放异彩
- • 土豪青睐西方顶级油画:国外看印象国内重写实
- • 桥舍画廊将举办颜艺澄个展
- • 一面墙:黄丙寅作品展在圣东方画廊举办
- • 靳尚谊作品展在南昌市791美术馆开展
- • 许江:回到画布前 就会减少官僚气
- • 《凉灯:黄于纲的一件作品个展》开幕
- • 中国梦美丽中国:第二届大型国画展在京举行
- • “苍劲风华——尹默中国画作品展”亮相北京
- • 黄胄和他的时代大型文献展在炎黄艺术馆开幕
- • 美国前总统卡特来华参观“中国美术家眼中的美国”
- • “乡愁国”展示八个在中国的外国艺术家的艺术
- • “吕斯百旧藏”登陆匡时春拍 涵括徐悲鸿等画作
- • 2014第六届亚洲艺术博览会即将在北京举办
- • 生活之路:第三届黄胄师生作品展炎黄艺术馆开幕

- • 王承尧书法作品展将在天津图书馆举行
- • 组图:2014玉雕名家名作精品邀请展在滨海新区开展
- • 画家闫勇:写意不可“贫学” 先论功夫再谈格调
- • 悠悠天籁之鸣——天津著名画家史振岭的花鸟画
- • “澄怀观象”喻建十书画作品展及研讨会举
- • 天津市美术家协会山水画专业委员会成立
- • 孙伯翔书画艺术展开幕:碑学大家 八十抒怀
- • 章用秀:记天津老一辈篆刻家徐嘏龄
- • 姜维群:《八百遐龄》唱大风 又是一曲正气歌
- • 八旬书法大家“八十抒怀” 孙伯翔书画展九日开幕
- • 津门著名书画家严六符临文徵明《行书千字文》
- • 津门著名山水画家皮志刚创作巨幅画作《天下情山》
- • 津门画家李津:画最纯粹的“红烧肉”
- • 敦煌壁画艺术精品展在天津美院美术馆开展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