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潘世勋:画艺之初不用担心“喝牛奶会变成牛”

画家不是思想家,但为画画也要不停的思索。画家大都不是理论家,因此思索常是不连贯的碎片、偶然迸出的火花。思索过程有时会激发创作的灵感,画画过程也常中断思维的深入。而我经常是好读书但不求甚觧,好思索也不求甚解,有些问题与周围朋友交谈过,多数情况只是自言自语、自省自悟。自觉想通了便皆忘却,也有不少想不清楚在脑子里长期缠绕不去。好在画画也不一定要都想通了才画。



我冥想的时侯不多,“苦思”倒是经常的。画好了会想,画坏了更会想,更多的是一张画想的挺好,中途却画不下去的时侯,会想得茶饭无心,夜难成寐。别人看来活得毫不潇洒,挺不正常。但我觉得画家要是没什么可想,大概画也就没什么可画了。
古人说“画山情满于山”,“画水情满于水”,都是说画画先有有感情。虚情假意不行,一见鈡情一时冲动也靠不住。还需不断的培养和长期的维护。华君武先生很早前说过;画家创作有如恋爱,要先有感情才能结婚,结婚才能生孩子,讲得就更加生动而有哲理。我多次入藏出于绘画素材搜集的需要,也在无意中增进了对高原的感情。



我曾在在巴黎美院一个画室进修,导师推崇马蒂斯,我画写实风格他不太喜欢,画装饰风格也不太赞赏,他觧释说画家应是“狡猾和诡计多端的”,具体说就是尽量用剪贴、拓印、转移一类手段代替画笔的刷涂。试了试形式上确实颇增趣味,但造型当然也要偏离真实。我也曾想过这样画肯定会画得轻松、活得愉快,可以充分享受绘画的乐趣,但考虑再三还是没有这样画下去,做一个一味玩弄形式玩弄技巧的画家,有背我学画的初衷。我不承认我是艺术的保守主义者,我喜好古今中外多种艺术形式,在课上课下也是力求客观地介绍西方现代主义运动,並一直鼓励青年学生开阔视野大胆试验。但我个人斟酌再三,还是不想改弦更张,决心利用有限时光,继续走自已的现实主义之路。



画艺之始总须有所依傍,才寻得标准,觅到入处。我上初中时,学校两位美术老师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便盯上一位电影院的残疾画工,他每期电影海报一出便跑去看,总可学到不少东西。在部队仍没有老师,除靠拼命画速写提高造型能力外,手法上也不时借鉴黄冑与叶浅予。画揷图更离不开模仿,开头是前苏联的杜宾斯基和施玛林诺夫,后来是中国的任伟长,当然也不时向同辈人偷艺。中国画论讲“中法心源”,就包括学习借鉴前人的经验,当然第一要“取法乎上”,第二是“学法不为法障”。前些年去国外考察现代美术,才弄明白一切高唱“反传统”的前卫大师,也都是只反爸爸不反爷爷。因为要超越前人,不仅是自然科学家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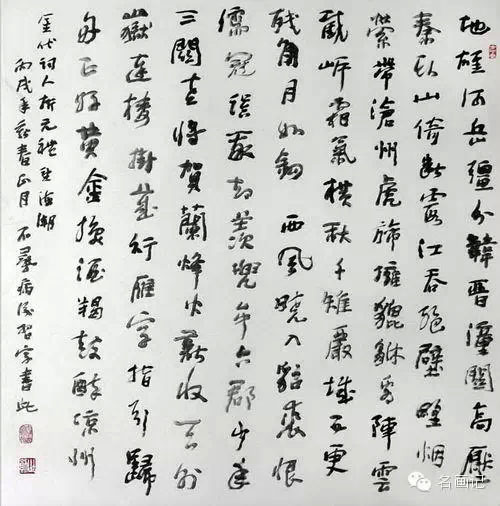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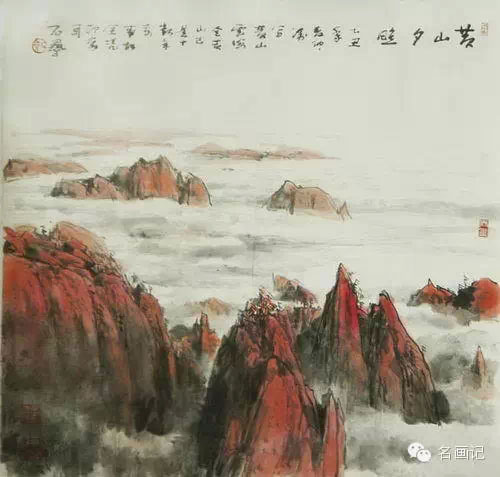
我画油画之初模仿过前苏联的画家,后来也模仿提香和林布朗,八十年代出国后又心仪于凡。艾克,包括过去不太喜欢的卢本斯,见过原作也刮目相看。近代和现代大师我也喜欢很多人,但学来学去还是谁也不像,就是因为学古人还是为了画自已想画的东西,合用的技巧才会拿来,不合用的只好舍弃。有自己想法的艺术家其实用不着担心“喝牛奶会变成牛”。我也没有喊过“民族化”口号,因为硬化毫无好处,我相信用中国人的眼光画中国的事物,最终总会有民族的特色。我研究绘画技法材料也是如此,我曾用很多精力与时间,致力于这一学科知识在中国的创立和推广,有人说见你对学生讲那么多,自已画上倒没看見用多少,其实出国前后不论画风与技法和材料我都有不小改变,但技巧的吸收和运用,总得相题行事,我至今还在画现实和具象的绘画,就是喜欢也无法硬搬毕加索立体主义时期的技法。





绘画的题材应是宽泛多样的,可以画身边的静物花草,可以画孩子老婆和自已的画室和卫生间,画好了都是好画。但我一直喜欢跑出去画,这只是与个性爱好有关。一辈子也画了一些画,其中有不少描写髙原的作品,但面对生活的多彩多姿,面对髙原的博大雄浑,又常自愧画的不够多,也不够好,心中总有一种负债感。几次在髙原的旅途中,都会遇到朝拜神山圣湖的善男信女,他们多是风雨无阻、目不旁视,一步一跪拜地向目标直去。我非宗教信徒,但献身艺术也须有这种进取精神,我一直记住“小车不倒自管推”这句话,只要余热尚存,尽管目的难达,也应奋力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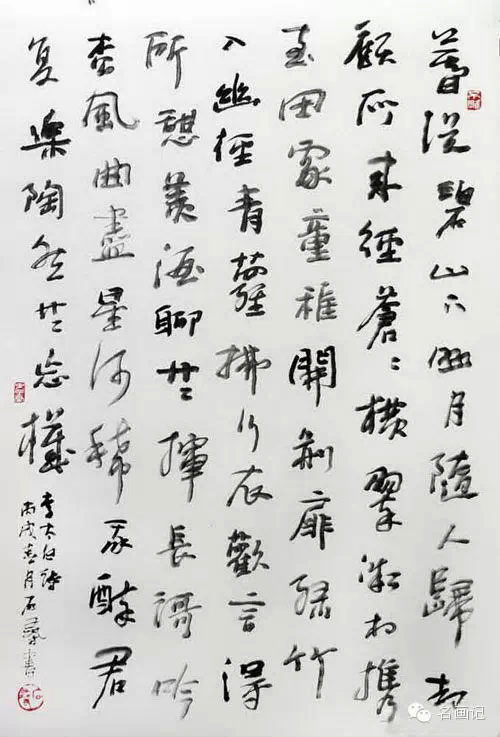

- •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记王印强和他的写意人物画
- • 组图:著名书画家尹沧海赴韩国首尔东国大学讲学
- • 孟昭丽、萧慧珠、李澜绘画小品精粹展
- • 孟昭丽 萧慧珠 李澜小品精粹羊年绘画展前言
- • 霍岩:中国画的笔墨之美
- • 国画名家八人展在宝坻举行 孟庆占吕大江参展
- • 水墨语境·书法国画十人展将在西洋美术馆开展
- • 向中林山水画展在“集真阁”开幕
- • 组图:庆“三·八”西青女书画家深入警营送书画
- • 尹默 李振华 王文元 杨建岭等书画家在沧州开展
- • 天津著名书法家刘光焱:读帖临池终有得
- • “翰墨传承 学院力量”中国当代书法展开幕
- • 姜维群:首创“蜀山嘉陵派”的山水画家向中林
- • 第七届“津门女书画家佳作邀请展”举行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