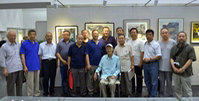-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从“徐冰:回顾展”看徐冰的艺术
徐冰(1955年生)回忆自己在幼年时期,母亲因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工作繁忙,经常将他“关”在书库里。或因此故,他日后走上艺术创作的道路,内容却一直与“书”有着不解之缘。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官方厉行文字改造,汉字简化成为运动。因此,徐冰的成长过程经历了“一批批新字的公布、旧字的废除,对新字的再更改和废除,对旧字的再恢复使用”。这一对待文字的特殊现象和概念,在徐冰心中种下了因子—也就是“文字是可以‘玩’的”。
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版画和教学时期,徐冰除了将版画视为绘画的表现,也从中国传统拓印和印刷术入手,摸索版画成为前卫和当代艺术媒介的可能。版画的模块性、过程性、复数性以及转印特质,成了徐冰实践观念艺术的基本法码。80年代后期的《五个复数系列》(1986-1987)、《天书》(1987-1991)、《鬼打墙》(1990-1991)三个计划,都是徐冰在旅美之前的重要代表作。1990年7月,徐冰赴美。他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艾维翰美术馆(ElvehjemMuseumofArt,现ChazenMuseumofArt)首度个展的就是这三件大作。借此,徐冰也奠定了他在美国艺坛发展,同时很快受到瞩目并肯定的重要基础。
可以确认的是,至少从《五个复数系列》开始,“过程”作为“观念”展现的一种形式,已经成为徐冰日后创作的思考常态。1987年他开始进行的《天书》(最初命名为《析世鉴—世纪末卷》),也在正式印制完成之后,随即通过海外的展览,让徐冰成功地在90年代的国际艺坛崛起,并引发西方学术界的热烈讨论。简单说,《天书》以中国语境为出发点,触及文字语言系统和文化、体制的关联以及相应而生的民族心理、传统与历史思维。看似什么都没说也不能读的《天书》,不但搅动观者对中国及其传统的反思,更让文史哲各界的国际学者为它写下许许多多的诠释和论述。
相较于《天书》由徐冰自己制版,《鬼打墙》以极具中国政治、军事和文化历史象征意义的“长城”作为拓印、转印之物,等于也把长城这一浩繁巨大的建筑量体,看成一个兼涵时间与空间双重性的物质文本。换个方式说,徐冰彷佛将长城视为另一本“书”,城墙的实体成了现成的版式。与《天书》无法让人读懂相比,长城混杂自然的风侵雨蚀和人为历史的构筑,经过拓印之后,虽然无字无语,只见时空抚摩过后的抽象痕迹,却未必不能阅读、感知或联想。曾经有人提出,《鬼打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幅版画;徐冰自己则说:“那时年青,野心大,做东西就大。”
旅美之后,对语言和文字敏感的徐冰,一度质问东西方文化是否可能经由语文的转译,达到真正的沟通。不少以中英文转译为题的作品在90年代前期完成,有些甚至影射中西文化交流的荒谬情境。《A,B,C…》(1991)、《MyBook》(1992)、《一个转换案例的研究》(1993-1994)、《文化动物》(1993-1994)、《转话》(1996-2006)都是这一时期之作。从难以沟通的冲突感,到交流接口的研究创作,徐冰也在90年代期间发展出《英文方块字书法》,不但设计了一套教学法,更将展场转换为教室。观众来到展厅,便进入了一个学习的场所。不管是华人或西方人,面对这些来自“英语文化的东方书法”,都是非常特殊且前所未有的经验。中国书法和英文在此邂逅交会,形成耐人寻味的对话。徐冰曾经坦承:“如果我一直生活在大陆,一定不会有这件作品的出现,因为文化的冲突不会那么直接……”他更写道:“当代艺术的新鲜血液经常是来自于艺术之外。《英文方块字》的实用性和在艺术之外的可繁殖性,是我很喜欢的部分。”就在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转换中,人们对文化的旧有概念受到挑战,从而打开更多思维的空间,借以找回认知的原点。美国著名的麦克阿瑟“天才奖”也因为看到徐冰的“原创性、创造力、个人方向,连同他对社会以及在书法和版画艺术上的贡献”,特别于1999年对他给予奖励。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徐冰更频繁地受邀在国际间展出,也有很多机会因应各机构的主题策划,结合其场域的文化或历史特殊性,进行与在地对话的创作。《文字写生》(1999迄今)、《烟草计划》(1999-2011)、《背后的故事》(2004迄今)、《魔毯》(2006-2009)、《芥子园山水卷》(2010)和《汉字的性格》(2012)都是因这类机缘而创作的作品。而徐冰在构思作品时,总不忘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与该地的语境或脉络互动,借此激荡新的艺术动能和讨论。
如前已见,针对在地特殊的文化氛围、环境,乃至于历史,据此创作出具备脉络意义和对话关系的新作,这一直是徐冰重要的创作模式。《背后的故事》也没有例外,他运用中国文人书画传统的“临”、“仿”概念进行了创造性的再诠释。针对此次台北市立美术馆的展览,徐冰特别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典藏,以晚明宗师董其昌(1555-1636)一卷与古人—北宋末期知名画家王诜(1036-约1093)—对话的《烟江迭嶂图》(约1604年),作为放大的蓝本,巧妙结合馆舍长二十米高五米落地窗的九连屏结构,发展成一件巨幅新作—这也是《背后的故事》的第十六号作品。
徐冰的创作素以符号、文字、语言为核心,《汉字的性格》意在揭露中国文字及其书写如何演变为一种深层或超稳定结构,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思维惯性,乃至于行为模式。西方现代以降的各种主义与思想,诸如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自由民主等等,看似已对中国社会产生明显影响,徐冰却认为,这些潮流并未对中国社会的本质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只是多了一种物质性的附加追求。也就是说,外来的西方价值还是“都被溶解在这个特别的,源自于汉字书写的‘文化范围’之中”。因此,或许可以看成是总结徐冰此次回顾展的近作《汉字的性格》动画片,最终想要表明的还在于:“中国文化的内核与能量,以及在未来人类新文明建设中的利弊与作用。”
面对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社会及其处境,徐冰也表达了富于普遍性的个人关怀。《何处惹尘埃?》以美国2001年“9·11”事件为楔子,向禅宗求借智慧之镜,反照当代世界景况。而创作已经长达十年,庞大且继续中的《地书》,则是反映了他对人类当代—甚至未来—语文发展新动向的持续观照,亦堪称徐冰个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巴别塔”(TowerofBabel)计划。
- >>相关新闻
- • “劳特雷克的巴黎:石版画与海报”MoMA展出
- • 在伦敦国家美术馆寻找色彩中的艺术史
- • 2014年“青年艺术100”启动展将亮相北京农展馆
- • 组图:“2014首届中国版画大展”正式启动
- • 深圳美术馆展出第十二届全国版画展作品
- • Artprice全球艺术市场大揭底:市场极度饥饿
- • 钟馗图:超越民族界限 承载普世价值
- • 刘永刚:艺术的线相与精神的尚立
- • 关山月美术馆年度计划聚焦当代水墨
- • 收藏家安德莉亚·狄比留斯倾心前卫艺术
- • 48年前焦裕禄木刻组画在中国美术馆找到
- • 陈丹青:文凭为了混饭跟艺术没关系
- • 浅析王铎的书法艺术及作品市场走向
- • 徐冰荣获第三十三届“城市之心”全球艺术大奖
- • 全国美术馆展出季——馆藏宁波籍版画作品展
- • “第5届安徽美术大展—版画展”在芜湖展出
- • 陈烟桥:现代著名版画家和教育家
- • “大师风采·国际版画名家原作展”开幕
- • 波兰克拉科夫版画展在南通举办
- • 鲁迅收藏的日本版画:数量众多 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