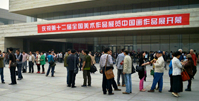-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身份,共同体,同胞:马莱内·杜马斯的艺术

马莱内·杜马斯(Marlene Dumas)的创作为当代绘画开拓着新的纬度,她将媒体图像政治性和当代绘画结合,挑战着人们对图像的阅读方式。对当下欧洲面临新的民族主义危机之时,她对身份的研究更加让人直面当下的问题。
人常说死亡让每个人变得平等,并不代表着当死亡从我们的双眼中夺走爱人的尊严时是仁慈的。麦克卢汉说“报纸卖的都是坏消息”,大众媒体中扑天盖地的死亡信息已经让人对此麻木不仁了,战争、灾难、车祸、死刑、犯罪、恐怖袭击,死亡的图像永远占据着大众媒体的主要版面,塑造着人们对恐怖的认知和经验,无论是经济利益的驱动,还是统治术的诱导,死者的尊严就这样被媒体剥夺。
1976年7月16日,德国《斯特恩(stern)》杂志刊登了一张摄影,图像中死亡的女性是德国左翼恐怖分子乌尔丽克·玛丽 ·梅茵霍芙(Ulrike Marie Meinhof),她于1970年建立了左翼恐怖组织红军派;在1972年,梅茵霍芙被捕,并被以谋杀罪和与犯罪组织有关起诉。定罪前,梅茵霍芙在狱中上吊自杀。梅茵霍芙是主流社会的公敌,又是左派组织的偶像。马莱内·杜马斯(Marlene Dumas)在2004年摄影图片为原型创作了梅茵霍芙肖像,130x110厘米的尺幅远远大于摄影的原始尺寸。作品的标题用的是杂志的名字——《斯特恩》,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的暗示,没有复仇的情绪,描绘的只是“睡着了”的人,只为提供给我们悲伤,只为恢复死者的美丽。纵然是全民公敌的肖像,这件作品中也没有“站在敌人尸首上欢歌”的不仁,只是对人类的悲剧的同情和深思。
这个作品属于杜马斯的“死亡系列”,在这个系列中,她描绘了一系列的非正常死亡的死者肖像,他们都来自媒体的死亡报道,有的是偷渡西班牙的非洲难民,有的是声名狼藉的罪犯,还有激进的恐怖分子和反恐士兵。展览中最为吸引人的那张刚刚死去的玛丽莲·梦露肖像,对杜马斯来说,那还是美国梦的死亡,还是作为自由和现代主义的代言模特的美国的死亡。那些死亡的形象也许我们都在媒体里见过,但当我们看到这些作品时,想到的是,她/他是一个妈妈,是一个爱侣、是一个父亲、一个朋友---媒体是政治的,从媒体中取材的杜马斯作品却消解了政治立场,没有提示” 3 “谁是侵略者?谁更值得同情?死于战争还是谋杀?”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强大的悲悯和恳求,不带丝毫偏见,审视着长眠之人,他们不再是个抽象的“他者”,而是人类共同体中的同胞。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参观纳粹办公室时留下的名言——“平庸之恶”。这句名言成了杜马斯1985年自画像的标题。她曾说:“有了一个南非的白人的身份,就没有什么更糟糕的事了”,带着白人的罪恶感,她研究了很多被掩盖的殖民史和政治史,特别是美国在刚果的掠夺,让她将政治、资源和罪恶关连起来,重新思考身份的意义。
这些思考在她的《人类肖像》系列完全体现了出来。这个史诗般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就是北非和中东男性的肖像画,还有巴勒斯坦自杀式炸弹携带者的肖像画,杜马斯移去了模特们所有的文化、民族、地域方面的特征,面孔被简化的只剩最后的结构线——嘴唇、发际线、眼线;这些最简洁的肖像都直视观众,神秘而忧郁,让人只能从中识别出男性的面孔的基本特征;不能辨认谁,谈何敌友呢?要回答“为什么是北非和中东一代的男性肖像?”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转向当下欧洲的政治语境中,穆斯林的移民浪潮刺激出了欧洲新一轮的种族歧视,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对恐怖分子的警惕,被明显地移植到了穆斯林的移民认知中,甚至是文化领域的歧视和排斥中。2002年到2005年,《人类系列》的诞生,正是以杜马斯为代表的欧洲知识分子是对当下欧洲文化环境的回应——以跨文化、跨种族的“人类肖像” 和博爱的情怀对抗种族划分和地域政治。MoMA的策展人柯妮莉亚-巴特勒(Cornelia Butler)评价道:“这件作品伟大、勇敢、直截了当地对当代文化、政治问题做出了回应。从我的第一感觉到最后的思考,都聚焦在那一个又一个漂亮而强有力的面孔”。这么多的肖像密集地并置在一起,营造了一个‘匿名的大众’的语境,又提供了一个中立的立场去观察人和人的图像。而当人不由自主地试图从区分种族的角度去阅读图像时,你又开始意识到“种族划分”这个顽固的问题,从而产生了严重的不安感,这正是这件作品的魅力和力量。杜马斯的创作取材自媒体,抽出意识形态的成分,将死亡和政治的图像变成普世的药方,那就是超越意识形态争斗,思考人类悲剧。
所以杜马斯挑战的,是大众对图像的解读的方式,她说过:“如果我们不知道希特勒、尼克松象征着什么,那么我们看他们的图像的时候,能读出什么呢?”。(Louis Hothothot)

- • 八旬书法大家“八十抒怀” 孙伯翔书画展九日开幕
- • 津门著名书画家严六符临文徵明《行书千字文》
- • 津门著名山水画家皮志刚创作巨幅画作《天下情山》
- • 津门画家李津:画最纯粹的“红烧肉”
- • 敦煌壁画艺术精品展在天津美院美术馆开展
- • 丹青物语——黄雅丽庄雪阳国画作品联展开幕
- • 丹青缘—唐睿、何宁、杜小龙水墨三人展开展
- • “艺海清扬·近现代名家画展”在天津美术馆举行
- • 李军、路洪明赴美国参展“文墨儒风”
- • “画说天津”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研讨会
- • 苍劲恬然凝重朴实—李克玉书画作品评析
- • 水墨计(肆)十二人展将启幕 天津美院薛明入展
- • 王书平:与潘基文谈画的“东方鹰王”
- • 《光环的背后:我与名人》首发签售会11月2日举行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