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夏展:高端垃圾场?
“他来了,开了一枪”
天津美术网讯 “夏展”(Summer Exhibition)一直是英国皇家学院每年挂历上的盛事,自1768年夏天开展至今,已连续举办248届。这是面对公众开放接收作品的最古老的展览之一。
夏展由Varnishing Day开始(Private View),画家们往往会在这一天来到皇家艺术学院的展厅里,审视一下别人都展了什么东西,给自己的作品添加最后几笔修改,迎接一周之后面向公众正式开放的日子。
1832年的Varnishing Day,有一次紧要的擦枪走火。 那一年的夏展焦点,是皇家学院两位院士:康斯特博(John Constable, 1776-1837)选择展出作品The Opening of Waterloo Bridge,对面挂着透纳[ 朱光潜在西南联大讲英国美术史,说:“在透纳之前,泰晤士河上不曾有雾”。](JMW Turner, 1775 – 1851)的Helvoetsluys。在V Day这一天,康斯特博早早来到皇家艺术学院依然伏在画布上,仔仔细细用他独特的“Constable Snow”的技法(一种反复、频繁点出的白色颜料,在观者离画作有一定距离的时候,可以用来模拟人看到的反光)来修饰新桥通车当天的盛景。

The Opening of Waterloo Bridge, John Constable, 1817。 Tate Britain, London
稍后不久,透纳也慢慢悠悠来到皇家学院的展馆。
后来的故事因为被电影《透纳先生》拍了出来而被大家所熟知,我在此复述一遍,因为关系到我们后面文章的展开:透纳进了展厅里,和康斯特博互相问好。趴在Helvoetsluys画布前,在一片阴云和风暴中,在海面点了一个鲜红的浮标。

JMW Turner putting on a finishing touch on Helvoetsluys, film clip

Helvoetsluys, JMW Turner, 1832。 Fuji Art Museum, Tokyo
透纳画完这一笔,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展厅[ 电影里他对众人不屑地唾了一口,很神气。我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献记录这个行为。],剩下康斯特博站在那里,笔掉在底地上,脸色惨白地站着发抖。听到声音的其他院士们纷纷赶来这间屋子,问康斯特博发生了什么事。
康斯特博指着透纳的画说:“他来了,开了一枪。”(He’s been here, and fired a gun)。康斯特博如此震惊的这“枪”打在哪里,我们可以猜测:一个浮标巧妙降低了整幅画的重心,让场景在观者眼里更为宏大(观者成为了仰视)。加重了风暴中渺小而摇曳的无力感,或者可能只是一个鲜艳的层次,让观者在宏大的叙事中有了一个可靠的抓手,一个安放视线的有效前景。
画家之间的竞争,在夏展尚未开幕就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 人们感兴趣的印象派画家,似乎却不存在这个问题,总是表面上一派和气,集体展出。可能也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对他们一并敌视,反而促进了他们之间的情谊。虽然莫奈和德加也并不愿意和其他人一起展览。康斯特博和透纳,彼此之间总是透着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敌视。印象派画家之间是没有的:他们都觉得自己是没有周瑜的诸葛亮。莫奈不喜欢和雷诺阿一起出去写生,觉得雷诺阿会抄他的作品。德加不喜欢和印象派一起展览,他觉得自己不是印象派。当然,这是后话。],似乎是贯穿二百年历史的核心主题。在今年皇家艺术学院的夏展中依然可见。作为全世界最古老的面向全社会接受展品的展览,今年皇家艺术学院的80位院士评委要从一万多幅来自社会各界的画作中挑出1250幅进行展览。皇家学院成立夏展的初衷,就是给当时没有办法展出自己的作品的社会画家们一个展览的舞台。直到今天,这一传统依然延续了下来。画家和雕刻者们,每年都背着自己的作品来到皇家艺术学院的门前,已经成名的院士和艺术家,带作品来展示自己的新思路和创作的新方向。而还没成名的年轻人,刚入门的艺术爱好者,则更希望能被人们记住,像康斯特博说的:“他来了,开了一枪。”
“Artistic Duos”
今年的夏展,由Richard Wilson院士策划,聚焦于以双人创作为主的艺术家群体(‘artistic duos’)。这一侧重点也让不少评论家伤透脑筋: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为什么两个人一起创作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那三个人呢?五个人呢?十个人呢?两人创作的主题也没有明确地体现在展览之中,毕竟最后展出来的展品,艺术家依然强调并注重了一定的和谐(coherence),在构思层面和执行层面,都看不出任何两人创作比之一人创作的独特之处。

今年的展品里,令人眼前一亮的是由Ian Ritchie和Louisa Hutton布展的Artchitecture Room。两位院士决定以蓝色刷墙,将整个空间压缩,并且让背景对视觉造成的疲劳减到最小(是一件必要的工作,考虑到展品的精细)。今年的主题是“Unbuilt”,布展突出了那些没有被实现的建筑构思和理念。
在介绍中,两人就直言太多年轻的建筑师发现在这个行业里立足已经越来越难,因为最终实现创作理念所需的资源和金钱投资都意味着只有相当小的一部分建筑理念会最终被实现。所以今年的建筑单元聚焦于那些“藏于草稿本和柜橱里被人遗忘”的设计。同时展出的,除了年轻建筑师没有实现的想法,还有其他一些成名建筑师的最终没能与世人见面的理想:有些是参加竞赛输掉了没有人投资,有些是因为经济环境改变,有一些则单纯超出了他们所在的时代太远。
六号展厅是此次展览的另一个亮点:探究艺术在对一个充满动荡和战争的世界所起到的愈合作用,以相片和雕塑为主要载体陈列出来。日本艺术家青野文昭的作品尤为引人注目。他使用在2011年3月日本海啸之后从废墟中寻找到的物品,将破碎的物品重新构建出完整的可认得艺术形式,体现了“愈合”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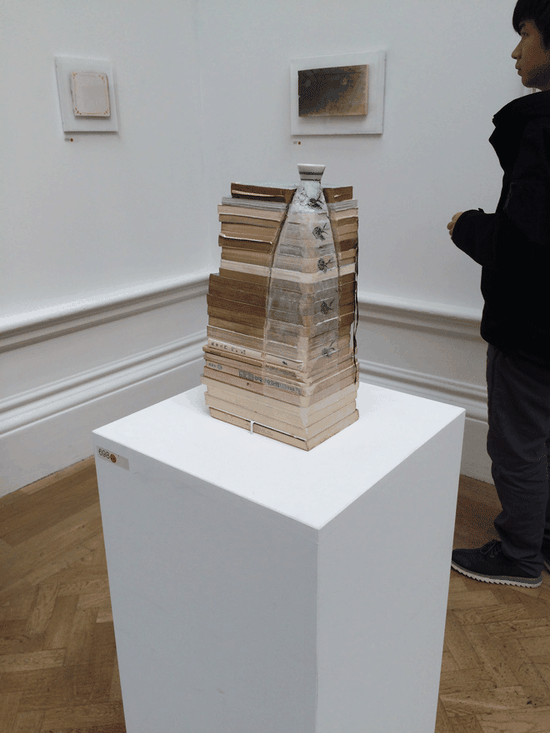
六号展厅的介绍中,突出了“创造”和“摧毁”这两个主题。巧的是,这似乎也是二十世纪最有价值的两条线索。从两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数个流派(解构主义、达达主义、存在主义),都是以“摧毁”为手段,以“创造”为目的。通过解构权威而实现自我。二十世纪随废墟诞生,创作似乎也过于痴迷于打破,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首先提出作者不是作品的最终解释,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提出人们不应该在作品中寻找熟悉的日常体验。人们在一百年间,把创作从“涵义”(meaning)中解放出来。然而解放出来之后,人们依旧在原地留守,要去哪里?似乎也是没有人可以确切地说出来。
似乎是“我与废墟缠斗过久,我也变为废墟。”
“天啊,一切都太复杂了”
夏展一直以“当代艺术”为主题,给先锋艺术创作一个发声空间。“当代艺术”作为一个定义宽泛的词,在这里的使用似乎十分不妥。在一个高度上理解,就是“所有活着的人创作的被活着的人嫌弃的艺术”的简称。自从印象派诞生以来,当代艺术“被嫌弃,兴起,被嫌弃,被接纳,被嫌弃”的轮回就是艺术史中的一个重要的生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嫌弃过当代艺术,似乎就没有参与过艺术史。早在19世纪,德加在看到他不喜欢的当代艺术被拍出高价的时候,也曾默默说了一句:“有些成功和恐慌并无二致(There is a kind of success that is indistinguishable from panic)”

A Private View at the Royal Academy, 1881, William Firth。 Royal Academy of Arts, London A Private View at the Royal Academy, 1881, William Firth。 Royal Academy of Arts, London
《每日电讯报》的诘问,反映出了艺术的发展的一个副作用:
也是因为夏展对先锋艺术的追求,历年来,人们给予夏展的评论,和人们给予当代艺术的评论并无不同。作家Stephen Fry在2010年夏展的晚宴上作为开幕嘉宾,曾经公开讲述类似的疑惑: “… 我们应该理解这些画吗?我们在看展时应该交谈吗?我们应该完全安静,站在画前面,瞪着它看,并不对人揭示我们的感受,还是我们应该偶尔非常大胆,说我们喜欢这个表达方式,那个形状,或者那些颜色?我们是否应该模仿那些站在另一边大声炫耀自己有许多知识,用着“morbidezza” “sfumato[晕涂法,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绘画技艺。]” “golden sections”这些词语的人?我们如果不喜欢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们太自大了?他明显在欣赏并享受这些画作,还与他的同伴带着热情和知识分享他的感受,这似乎没错?我们为什么假设他在炫耀?这假设,是不是揭露了我们自己的不安全感?我们是不是应该对我们面前这幅大师的杰作展示一些不喜,反而去喜欢那些没有名气的人的作品,来体现我们懂得如何鉴定作品的原创性和不被名声所欺骗?天啊,这一切都那么复杂(Oh dear, it is all so complicated)” 每一年的夏展,都会引来同样的争议,混乱和困惑。《每日电讯报》在2015年对夏展的评论尤其尖刻,说夏展是“高端垃圾场(high end junk shop)”
《每日电讯报》还引用1949年的夏展时皇家学院的主席Alfred Munnings说的一番话:“如果我在街上看到毕加索,一定会过去踢他一脚:‘看在上帝的份上,如果你画一棵树,就画的像一棵树吧’” 不可置疑的是,如今的皇家学院,从“那个画一棵树,就画的像一棵树”的理想里已经走了很远了[ 20世纪过后,人们把画什么像什么这个常识称为“自然主义”,“超写实主义”等等]。这也似乎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毕竟画一棵树,如果就像一棵树的话,很多艺术评论家也就要失业了。艺术评论家,自夏展开始之际就巧妙融入,把自己变成了夏展的一部分。 比如1881年,参加夏展开幕式的时候那些小姑娘们,都带着崇拜的表情等王尔德解释这些艺术品的来龙去脉[王尔德虽然给妹子们讲画,他自己却是反对art criticism:“What is the use of an art critic?。。。 Nowadays, there are so few mysteries left to us that we cannot afford to part with one of them” (The Critic as an Artist, Part I)]。 评判标准的消失。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百年,文学界和艺术界从废墟中成长起来,带着伤痕开始的一代人,开始像生活中被摧毁的一切看齐,在创作中摧毁权威。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画(Old Masters)的标准被认定不能再用了。突破意味着抛弃标准,而新的标准的建立却迟迟缺位。也不得不说是一个至今依然遗憾的事情。2014年,英国金融时报曾经刊文《当代艺术依赖金钱标准而非美学价值》[“Contemporary art is judged by its price tag, not aethestics” 金融时报2014年11月18日刊]讨论这一问题,文章中悲观地指出,我们已经集体失去了以美学标准判断艺术品的能力,而只能觉得“越贵越好”。我们看重潮流,价签,以及最流行的噱头,而不是艺术品本身。然而金融时报这篇痛彻心扉的文中,那位作者也不能免了自诘一句:哪个年代不是呢?
结语
我坐在RA旁边小咖啡馆的落地窗旁边,敲敲打打这篇评论。身边都是刚从夏展出来的人,看见我在敲打,大概也都猜到了我在做什么。对面有个姑娘,敲敲打打,是不是一样的事。
一百七十年前,波德莱尔给1846年的沙龙夏展写评论,他说: “评论者是幸运的,他没有朋友,这是他最大的优势,他也没有敌人。我真诚认为,最好的评论,是娱乐而带有诗意,而非冷冷的,分析性的评论。
分析性的评论自称解释了一切东西,其实是:没有了恨,没有了爱,刻意地掏空了一切情感。
既然一幅画是自然在艺术家心里的投影。那么我要说,一个最好的评论,是一幅画在一个智慧而敏感的心灵里的投影。对于一幅画最好的评论,甚至应该用十四行诗或者一首悲歌唱出。”
波德莱尔这话,桑塔格点头同意:不要用智识(intellect)压抑美(aesthetics)。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庄子,每一堂课都挤满了人,第一节课,先生对学生们说:“庄子呵,我是不懂的咯,也没有人懂”。
既然不懂,为什么还要撑着讲?大概因为心里存着波德莱尔说的:对其有爱,有恨,也有一首悲歌。

- • 笔底庄严·李寅虎个展7月6日在天津美术网艺术馆开展
- • 纪念穆仲芹、赵松涛 工艺美院60年代学生举办画展
- • 回归古典 高冬教授收藏英国水彩原作展在津开幕
- • 中国画八人精品展在津举行 刘家栋“大红袍”首发
- • “墨致文心”书法专场展在天津文化产权交易所开幕
- • 白狼书法走进国际大都市7月5日将在天津美术馆开幕
- • 第三届“滨海杯”国际设计大赛全面启动
- • 津门青年画家齐聚一堂创佳作 纪念建党95周年
- • “墨韵颂歌”书法作品展移展至天津未来科技城
- • 庆“七一”京津冀书画名家联谊展在河北文安开幕
- • 天津工艺美院60年代学生办展纪念穆仲芹、赵松涛
- • 天津美院曹敬钢现代撒拉族服饰设计作品亮相北京
- • 天津美院实验艺术学院综合基础绘画优秀作品展开展
- • 天津师大现代陶瓷艺术研究所成立 尹沧海任所长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