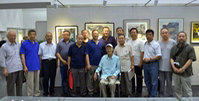-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第八届深圳雕塑双年展:雕塑在哪里?

“我们未曾参与”第八届深圳雕塑双年展在深圳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简称OCAT)展出,8月31日,展览结束。此次双年展共邀请到了33位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共34件作品陈列在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OCAT)的深圳馆的A和B展厅、北区的B10馆及周边的公共区域内。第八届深圳雕塑双年展从“社会雕塑”这一概念出发——“社会雕塑”最初由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提出——“像塑造雕像一样塑造社会”的观念拓展了雕塑的边界,使其不仅停留在物质形态,更侧重介入社会关系。“但是在流行后,原来博伊斯理论里一些积极主义的成分消失殆尽。”
今年的策展人马可·丹尼尔,现任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与泰特英国美术馆成人项目召集人,也是泰特现代美术馆公共项目策展人。马可·丹尼尔说,通过观赏等方式,我们发现有些艺术方式已经不再有原来的激进成分,看上去只是非常俗套的做法。对有些艺术家和机构来说,好像只要有人参与到艺术创作之中就够了,而完全忽视人在这个参与过程中到底做了什么,以及在参与过程中,从创作的角度来讲,究竟又提出了多少新的艺术主张?
“不参与也可以是一种重要的艺术声明、艺术态度。从观众来讲,不参与也是他们发出的一种很重要的艺术声音、艺术立场。”在马可·丹尼尔看来,我们现在正处以一个“后参与式”的大环境中。“后参与并不是说参与这个过程已经完全结束了。我觉得现在的参与只不过是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所运用的不同的艺术工具之中的其中一种而已。我们必须学会将它作为一种工具来介入到艺术创作之中”。
这一观念在希拉·佩佩的空间站装置《为了人民》中体现的细致且微妙。艺术家用织网、钩针、编织等技术在展厅中构建了一个五颜六色宽阔的活动空间,看起来像乐园,供人休息,同时这件作品也将为后续的展览讨论活动提供场地。就在我对这个颇有趣味的公共空间垂涎三尺并准备跃跃欲试的时候,我看见地毯与地面的接合处写着“请脱鞋进入”的告示——这当然是一种人人平等的参与权。可是我犹豫再三,最终因为自己的鞋子脱穿麻烦,裙子太短,而放弃了对于这个装置的体验,对于躺在舒适挂篮的人们唯有艳羡。

于是我的参与变成了一种自主的放弃,“请脱鞋进入”给了这种参与以提示。如马可·丹尼尔所设想的那样,展览中对于“参与”的探讨既是多元的,更多是隐性的甚至是虚拟的,所挑选的艺术家们多角度地描述和表达了由“参与”所构成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等景观,这种关系的构成,所谓“社会雕塑”的概念体现在每一件所选择的作品中,策展人的意图非常清晰明朗。
然而只有策展人清晰是远远不够的。如2号展厅里中国艺术家黄博志创作的《生产线》,由一位正在制作T恤的女工和四十个简易衣橱组成。女工会一直制作T恤,双年展闭幕后,衣服打包运到台北,在台北双年展展出并制作更多衣服,如此往复。马可·丹尼尔说,三十年前,台湾的纺织业非常发达,但之后工厂大多迁移到珠三角,而今天又有部分企业返回台湾。而艺术家欲通过模拟商业逻辑的迁移,来引起观众对全球生产系统的关注。这样的手法拙劣且难以自圆其说,就好像我们没有必要真的杀死一个人来以此表达“杀人是不好的”,同样,艺术家没有必要真的搬运一条生产线来模拟两地生产线的迁移。更何况,这个“生产线”没有自身的必然性:它的规模、人工数量、产品数量都是可变并且随意的(至少当我于早上11点踏入展厅时,那位工人还没有开始工作)。艺术家既然无法将哪怕是一个完整的工厂搬入展览(即便是这样,作品也是浅显的)那么这种探讨“全球生产系统”的方式就变成了“世界之窗”里的微缩景观——它永远代替不了实际存在之物的叹为观止。可以看出策展人的思路,将该作品与陈彧凡、陈彧君的室内空间景观(《滨文路388号》)和庄普的三角房子装置(《召唤神话》)置于同一展厅内的做法是不二之选,这让作品间产生了关联,增加了意义。

同样粗糙的作品还有李景湖的《海风》。
“在东莞的工业区里,李景湖从距离他工作室不远的废品市场购买和搜集用过的容器,主义是不锈钢餐具。这些容器盛满水后,被放置在一层画廊的场域内。这仿佛是在诗意地召唤临近却又缺失的大海,我们简直可以感觉到工厂似乎吹起了凉爽的海风。”于是艺术家认为,大部分没有见过大海的内地工人对海的憧憬成了他们争取美好生活的“隐喻”。显然艺术家的出发点是好的,既有诗意的浪漫,又有人性的关爱。二手的器皿隐含着种种的社会关系,失败在于“水”这个媒材的选择上——装生水、熟水、矿泉水、洗澡水还是海水,它直接关系着作品是否成立的问题。艺术家在这个选择上是不考究的,既然要引发观者对于海的联想,为什么不将这些器皿装上海水?如果展厅中还能隐隐约约闻见淡淡的腥,是不是更有诗意?作品的安置也不具有空间感,光线也错乱,其视觉的效果就是:放在地上一堆浩浩荡荡待洗的碗。
而过于精致的作品也是致命的。比如程然的《信》。将一种虚拟的、是男是女都不确定的、充满想象力和无限可能性的网络邮件过于具体化在一张国际明星的“大”脸上,作品变成了一段精美的刘嘉玲个人宣传片。他没有做到“虚构和现实更加模糊不清”,他只做到了他和刘嘉玲很熟。

只有在马可·丹尼尔设定的这个“社会雕塑”的展览语境里,宋拓的《公务员》作品才能够成立得如此彻底,如此的震撼人心。艺术家为某个县级市直属党政机关每一个在编的公务员写生,这些人物根据他们的行政部门和官方角色被分成不同的组,打印在黄色的A4复印纸上,弥漫了整一面墙。其背后所代表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源是不言而喻的。复印纸是办公室的必备之物,公务员的形象呈现在其之上的时候,复制的概念就变得更为立体,而其中所包含着的沉默的激进意识在作品的体量上被一览无遗:一个县级市姑且如此,一个国家又如何呢?你可以站在宋拓的作品前设想出若干的社会景观,比如邱志杰、宋振与店口居民共同完成的刻在15套桌椅上的村里官员对于民生问题的承诺,同样可以和这群公务员发生关联,遗憾的是这两件作品并没有被呈现在同一个空间里。而邱志杰的作品只有存在于一个合理化的展览语境中时,才显得没有那么的故弄玄虚。
可以看出,抛开对于作品自身实施过程中的技术与观念是否合一的考评不谈,策展人清晰地知道自己试图突显的是站在艺术家背后的社会关系群体的存在感——工人、农民、公职人员、特殊群体;工厂、学院、被拆迁被废止的建筑群,这种呈现与每一个到场的观众一同发生了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回应了博伊斯的“社会雕塑”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此次展览的疆域无限之大。

然而,当我们细细想来,将一个60年代始发于西方曾经流行的概念通过外国策展人的眼界展现在当下的中国艺术史进程中的时候,其价值意义又在哪里?很明显“不参与”、“反参与”概念的兴起伴随着西方反美术馆收藏/消费的热潮。而反美术馆的思潮也是建立在成熟的美术馆系统之中的,即:西方艺术博物馆的兴起将艺术品从原有的语境中抽离出来,进入美术馆意味这让它们成为孤儿。唐纳德·贾德注意到了二十世纪后期博物馆的发展趋势。在他看来,博物馆的主管和建筑师们破坏了雕塑作品的完整性和个人特征,对此他深恶痛绝。他说:“艺术仅仅是收藏艺术品的建筑存在的借口。这些建筑是新富阶层文化的真正象征,就像粉笔划过黑板时的尖锐声响一样清晰无误。”(《碰巧的杰作》【美】迈克尔·基默尔曼著李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场“不参与”的运动诞生的中最为极端的形式“大地艺术”可谓其一。对于这样一种基于地质和天体活动时间表的创作,参与其中,需要巨大的付出,它的义务就不在于让每一个人随时都能轻易欣赏到它。
成都艺术家张羽最近在其微信里传播着一个“孤独的公共性”的概念。如果说公共性必须是自由的、开放的、公民民主甚至是民粹的,那么它在有红线的现实情景中哪怕无人知晓,不能传播,它们的公共性也不会被改变,只会愈发孤独——在一个没有激进传统,不能也不敢迷恋激进的国度,艺术的激进性是不是一种必然?
而当我们将“社会雕塑”的概念从它诞生的土壤中抽离出来时,它变得放任四海皆准,而最真实最有力的场景在历史中只能出现一次。不管你是复制一个“参与”还是复制一个“不参与”,或者炮制一个“反参与”,它仅仅是一个展览的噱头,一个没有时效性的噱头。博伊斯在史册中已然是一片过眼烟云了,我们又如何能寄希望于一个永恒的方法论呢?理解是有条件、有语境和暂时的。

- >>相关新闻
- • 首届(天津)两岸名家艺术精品交流展开幕
- • 天津市河东区举办书画、印石、葫芦艺术名人精品展
- • 菱花馆艺文社同仁举办书画展纪念奇才曹大铁
- • “非洲罗丹”乌斯曼·索的雕塑人生
- • 走出去办画展 艺术展览的“海外镀金热”
- • “2014首届中国北京国际艺术臻品展”即将启动
- • 明心见性:王磊墨彩工笔画展于芳草地聚艺堂开幕
- • 米罗大型回顾展——"从大地到天空"诠释创作历程
- • 岩田小龙的波普绘画展在纽约229艺术区展出
- • 喻红的早期展览与新生代绘画的生成
- • 合肥一青年用纸做雕塑:一月始现一番天地
- • “1960”群展在北京泉空间开幕
- • 上海静安国际雕塑展9月20日开幕 汇集11国艺术家
- • 2014苏富比室外雕塑展“超越极限”于英国开幕
- • 山寨雕塑扎堆艺术园区 游客质疑缺少文化气息
- • "明:改变中国的50年"主题展将亮相大英博物馆
- • 无锡展出百只大熊猫雕塑 3只已被游客顺走
- • 博物馆塑像惹争议:清代书生握毛笔像执钢笔
- • 京城最大雕塑公园国庆落户当代MOMA
- • 霍夫曼英国首件委任作品大河马现身泰晤士河

- • 首届(天津)两岸名家艺术精品交流展开幕
- • 邵亮:孙其峰艺术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引发的思考
- • 天津市河东区举办书画、印石、葫芦艺术名人精品展
- • 天大学子坚持绘画19年:将儿时梦想变为年轻事业
- • 天津市河北区、河东区举办翰墨丹青中国梦书画展
- • 李雄风新书潇洒的智慧 把禅的艺术带回人间
- • 孙其峰:“包容”为师 重视创作能力
- • 张蒲生美术作品展亮相天津美院美术馆
- • 三远当代艺术中心首展拉开艺术长卷 倾听世界寓言
- • 视频:“境由心生·陈丙利山水画展”在天津开展
- • 陈丙利山水画新作在君合利景饭店展出
- • 王俊生大写意画展在天津群众艺术馆开展
- • 张福义、康国林、马孟杰三人书法展亮相
- • 津疆两地书画家作品联展在乌鲁木齐市举行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