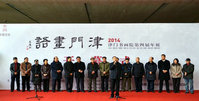柳新生
来自田园山水间,隐于清旷心原去
——著名水彩画家柳新生先生访谈录
初到柳新生先生的家,宛如来到欧洲湖光山色的乡间,一处静谧的林中小屋。暖气营造着绵绵的聊天气氛;暖色系的家具罗列简洁;大门和楼梯是厚重的实木;画具和各式工艺品呈现出亲密的姿态,随意地出现在偌大房间的任意角落;阁楼的尖顶高耸,舒适的层高和满溢的阳光,让阁楼成为迷人的工作场所。
工作台上散布着几十张碧天清漠的风光照片,我拿起细细端详——“噢,那是去年在新疆阿勒泰写生时候我拍的照片,喏,你看这张塔里木河边上的胡杨林,好看不好看?”先生挑出一张照片递过来。我注意到房间一侧,便有一幅先生已经完成的作品,正是这照片中的胡杨林,曲折,遒劲,寂静,不屈。去年新疆写生的作品先生已加工完成十幅有余,皆靠在房间角落的地板上,构图饱满,笔触简练,色彩清和,仙魅柔妙,使人恍惚得难分此境此刻幻与实。
工装背心,牛仔裤,灰白的长髯,一顶小小的毛线无檐帽。说话时总带着儒雅的笑,口音夹着浓重的吴侬腔。语速徐徐,思维敏捷,说到高兴处开怀大笑。我们在阁楼铺洒着冬日阳光的落地窗前坐下,向着如此的柳新生先生开始了我们的采访。
从艺渊源,源自幼时那抹绿
1937年,柳新生先生出生于常州武进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做木匠的父亲在上海工作,过年时会带回一些上海的年画,先生对年画很感兴趣:年画反映的内容有的是当时上海的跑马厅,赛马的景象栩栩如生,还有的反映的是戏曲人物,他只有七八岁,总是看得很入迷。“隔壁一个堂兄是我的偶像,他喜欢给书本插图涂上色彩,画得很好看。”
“农村那时候过年,邻里间的主妇会互相串门帮忙做糕点。我就跟着我母亲去邻居家玩。吃了一个米团后还想吃,不好意思再找邻居要,就用泥巴在人家的门上,画了个一模一样的米团,邻居看到后都笑了,说,呀,他还想吃!于是又得到了一个米团。那应该就是我的第一幅美术作品了(笑)”。
先生曾说:“我非常喜欢冬天树木优美而丰富的线条,以及许多攀附在树干上的藤类小生命,这些感受激起我对新的表现技法的追求。”这份对草木生息特殊的恋察与交悟,幼时已然成形。读书后,春假远足,别的同学都买吃的,先生只对图画本子感兴趣,树、莲藕、远山,只是简单的画面和物体,也爱不释手。“可能因为从小对农村的记忆吧,全是田园啊、树林啊、河流啊、竹林啊,自然景观的美对我审美趣味的塑造,影响很深。”熟悉先生作品的都知道,乡土和田园,先生画了一辈子。
十岁,先生全家迁去上海。“第一天到上海的景象,我到现在都记得,满街的霓虹灯和洋品牌的海报,五光十色、眼花缭乱,视觉冲击是非常强烈的,整个人都看呆了。”
来到上海的学校,文艺课程丰富起来,对艺术的兴趣随之阔然。秉承木匠父亲的天赋,先生手指灵巧,善于手工,“那种两手一搓,嗖——地一下飞出好远的竹蜻蜓,是我最擅长做的”。学校一位老师爱给学生在竹片上写励志语句,他便临摹老师的笔迹,在竹片上学刻“奋发图强”一类的字。山水国画也极感兴趣,弄堂有一户人家挂的山水画得极美,便常绕道去看,回家来自学自娱,毛竹画了一幅又一幅,家里挂得到处都是。在读书上,和意向思维相关的学科,作文、画画、手工,先生总是名列前茅;理科则很吃力,“数学啊、化学啊、物理啊,题目的答案叫我背也背不出来。”考高中时,因为理科实在太弱,先生落榜在家。
求学名师,汗水浇灌方茁壮
好在读书生涯行将终结之前,人生的转折已然出现。一次美术课,老师教授起西方绘画。把《蒙娜丽莎》一亮出来,十五岁的先生感到了异域美学对感官如潮地震撼:他分明看到画中被赋予神秘之笑的妇人,连交叠着的双手,都在静晦地微笑。老师的画作也私下看过,只是一只简单的香蕉,却连表皮黑色的斑点都栩栩如生。“完全走入西方绘画的世界中去了。”艺术的星火,就此在一个少年的内心莽原,簇燃不灭。
一日,父亲的友人在街上看到上海山河美术研究所招生广告,急急来告诉了他。山河美术研究所坐落在延安中路的洋房里,甫一进入,建筑里的分子都与外界迥异了。“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石膏像林立,维纳斯、大卫、拉奥孔……还有很多学生正在画人像。我站在那里愣了好半天,如痴如醉啊,我就晓得了,我是一定要走画画这条路了。”
进入研究所那年,他16岁。他成为研究所里进步最快的学生。一大早便骑着脚踏车去画室练素描,一抬头就是晌午了。老师们都回家吃饭了,偶然没带吃饭钱的先生,干脆就省了一顿饭,街边转悠两圈,守在研究所门口,成为下午开门第一个到的学生。“老师问,你中午吃饭了吗?我便答,吃过了,吃的面!”在研究所的张眉孙、方雪鸪、王挺琦三位老师的谆谆教导下,先生学了整整三年的素描、水彩、风景、静物、人像。“张眉孙老师当时已经60多岁了,有一天清早画了一幅雪景,急急地拿来研究所给我们看,大家一起赏一赏,他再去上班。有年严冬,张眉孙老师在田间画景,天气那个冷啊,傍晚时分身上都冻僵了似的。他带了调水彩颜料的酒,一边饮酒取暖,一边完成了写生。张老师曾说退休后,会云游全国去各地写生。这句话一直烙印在我的心里。”
彼时先生已进入水彩写生的学习中,经常跟着老师去野外写生,养成了这个好习惯。只要是上海有点滴自然气象之处,都被先生背着写生板跑了个遍。“一次去松江写生,几个同学同租了一间房子,后来人家告诉我们这屋里刚刚上吊死了人,之间点的蜡烛忽忽悠悠的,不停地摇啊摇,大家心里害怕得睡不好觉。”
先生一生坚持赴外写生,拉萨、海南、帕米尔高原、青海湖、西双版纳、吐鲁番和阿勒泰……无论寒暑病疾,直至今日。有一件关于写生的事,一直让先生颇为唏嘘:“我家住在中山公园不远,我几乎可以把中山公园的每棵树都背出来。母亲说,中山公园是你的娘家,你就在那里作画不要回来好了(笑)。时隔半个多世纪,弟弟陪我再去中山公园,居然找到我年轻时画过的几棵法国梧桐,已经变成了参天大树,记得当时画完它,王挺琦老师非常喜欢,说可以争取出版了,并起了个名字:《培植新生》。回到家,居然还翻出了这幅画。”
十年断层,世事玩笑自有解
1956年,先生19岁。来到了安徽,在《安徽文化报》做美术编辑。而他只知如何对着石膏画铅笔素描,如何对着乡野画水彩写生,对美术编辑工作一无所知。于是经常去请教各位画家,甚至去请徐子鹤大家为报纸指导插图。“上班8个小时,总觉得不习惯,就想写生,领导特批每周两个下午出去写生,所以常去逍遥津、包公祠公园等地方去写生。哪怕出差,也不会中断写生。”后来先生调到铜陵市工作,巧遇上海来的两位同学,他们曾为写意水彩大家冉熙先生的学生,在冉熙先生画风的影响下,先生对个人水彩风格已渐有雏感。一些评论家看了他的画,直言是“有新意的水彩画”,《安徽文学》编辑部特约先生两幅作品:《湖上》和《绿了田间》,在彩色中心页发表。“有一次去单位食堂买饭票,卖饭票的同志桌子上玻璃板下压了一幅剪下来的《湖上》,我一看,呀,是我画的呀!”
先生的“写意水彩”风格还在起步时,文革爆发了。
“十年文革,我当真是革命得很,觉得自己的西画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环境不允许你画,我也无心画了,把大部分画烧了。包括拎着水和画具辛苦爬上黄山天都峰的写生,也全都烧了。”还有一幅武汉长江大桥的写生作品,出于对构图美感的考虑,先生将过桥火车的喷气部分遮盖了桥面。作品被刊在《安徽日报》上。读者写信来,言辞激烈地直指这幅作品在“炮轰长江大桥”,让报社遭受了巨大的压力。“领导便通过组织问我,你这幅画还在吗,我说在啊,领导说,出了点问题,你把画交上来我们看一看。我就交上去了。至于交画的缘由,我是在文革结束才知道的。”文革带来的十年创作断层,终究是让最好的年华,成为一场世事的玩笑。
思想解读,随性随心享艺怡
郭玮:山河美术研究所的三位老师,带给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柳新生:三位老师的专业极好,为人却非常谦和。每一位都儒雅高洁。比如方雪鸪老师,晚年来到安徽艺校当老师,一言一行谦逊庄和,衣服永远整洁如新,品格深得师生的敬重。三位老师的做人风格,是对我影响非常重要的。
郭玮:您的作品中,有极其写意的,也有非常写实的,两者间的创作关系是怎样的?
柳新生:我的性格比较内向,年轻时更是性情严谨。张眉孙等老师是写实风格,这是给我影响最早的。后来冉熙先生的写意水彩我很喜欢;林风眠的国画,那种水墨意境我也很喜欢。写意是一种生来便喜欢的情结,可能是幼时家乡的山水培养了我这种喜好。喜欢作品讲究意境,笔墨简练,写意从构思到技法都渐渐有了自己的体系。至于写实和写意的安排,我倒没有刻意为之。
郭玮:您对色彩的运用也非常考究,同样描写乡土之情,有的色彩奔放绚烂,有的色彩素丽宁静。运用两种色调的规律是什么?
柳新生:这个是根据题材、对象和自己的追求来决定的,有的是事先已经想好,有的是作画过程中因为一些灵感即兴改变的。
郭玮:除了水彩之外,您有其它喜爱的美术形式吗?有相关创作经历和计划吗?
柳新生:有啊,速写啊(笑)。现在最喜欢钢笔速写,去年在欧洲待了40多天,画了七八十幅速写。这一阵又在修改写生油画,并突发奇想,画起了油画人物,你们看这个印度美髯公,是在印度时想画的题材,这次参考一本图册上的一张红胡子老人的照片,顿时起了油画灵感,就自己画起来了。(指给我看房间一角的成品:红髯瘦削的印度老者正在凝视远方。)另外还修改完成了在新疆阿勒泰牧场写生的雪景,目前产量不高,就自己兴趣使然慢慢画吧(笑)。
郭玮:您对书法艺术怎么看?
柳新生:喜欢啊,真心喜欢,前面说到了,从小就喜欢。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练习书法。现在总感觉时间不够用,因为又迷上了油画嘛(笑)!也没有勇气。我觉得书法的美,在于用线条来书写情感、表达思想,这是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财富。中国很多艺术都是符号性很强的,包括戏曲、中国画等。把客观对象抽象成一种特定的艺术语言。这多美啊。
有一年我和好友王涛先生在泾县,我们在宾馆,我就用王涛的笔墨画了古人国画,王涛一看,非常惊讶,要为此画题字(笑)。所以我也经常画些水墨画,真的非常喜欢。
郭玮:您对安徽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有什么期望?
柳新生:一些画家急于让自己的作品进入市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作为画画的人,不能被市场绑架。我不是科班出生的,不论是来自市场的压力,或评论界的压力,一路走来也是有很多的。但是最终还是决定走自己的风格,这是勇气,也是姿态。同时,我一直认为画画需要不断创新,重复、平庸、虚伪、炒作都是不行的,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多风格的尝试和转换,创作就会有激情。
正聊着,先生的手机和固定电话同时响起,先生矍铄地站起身,就那样左手手机、右手固话听筒地将电话接了来。一只电话是好友王涛先生的,一只是一位画山水画的好友的。电话里的两个人,都嚷着让先生互传问候。我笑得前仰后合,望着柳新生先生欢碌着讲电话的背影,沉心待着先生将那跃悦的友间笑语尽兴说完。(特约撰稿:郭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