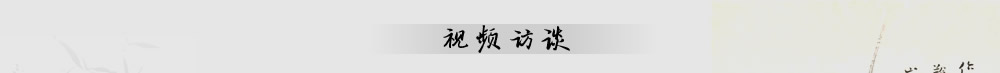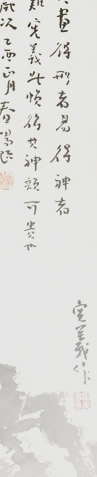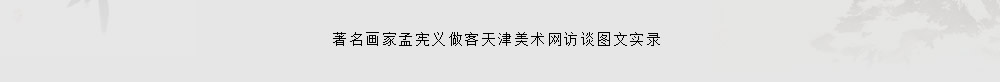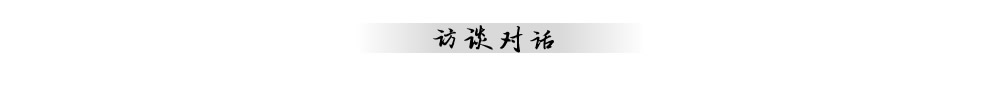|
|
|
[孟宪义]:我们不论学习什么路径一定要正确,他给我指导的方向是不对的,所以给我带入歧途。1972年碰到一位老先生,赵胜初先生。他当时才54岁,他是1955年毕业于中央美院,上过马克西莫夫训练班的。在天津的美术界画油画的只有两个人上过马训班,一位是秦征先生,一位就是赵胜初先生。赵胜初先生出身书香门第,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就到一个企业里面工作。我是在一个展览上遇到的赵胜初先生,他就给我讲了绘画的原理,这样我就对绘画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才算正式起步,一画画了十三年,到了70年代末的时候我自己就开始思考这样画方向对不对?画油画这样画下去行不行?因为油画毕竟不是本土文化的产物,本土文化和西洋...[详细内容] |
|
|
|
[孟宪义]:霍老师对花鸟画的认识符合于我们传统绘画理论的诉求,所谓文人画的思想,是追求思想的,所运用的题材只不过是一种载体而并不是目的。是利用花鸟来表述人文思想和绘画理念,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如果单纯的画花、画鸟,必然走向小巧一路,后来的学习证实了这个的观点。苏轼有一首论诗的诗说:“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从学习的角度、观赏的角度都不能以像为标准,比如画鹰、画花、画鸡、画马、画驴这都是像,如果以像为目的,就只是和儿童一样。所以霍老师从一开始我听他讲花鸟画的时候就不是从像这个角度思考和学习的,他更博大一些,内容更丰富和深刻一些,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必然形成...[详细内容] |
|
|
|
[孟宪义]: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才十几岁,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才12岁,就不上课了。我那个阶段小学五年级就停课了,所以读书对于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孩子来讲是很渴望的,同时也有非常大的难度,因为我们识字都是有限的。但是所有的人都有求知欲,只不过角度不同。那个阶段我可能是因为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喜欢政治类的东西,因为哲学的一部分属于政治,从马列主义这个角度看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对这些东西有兴趣,下了一些功夫。哲学的思想在马列主义中占有突出的地位。那个时候到图书馆看书,也没有太多其他的书供我们看,这一类的书籍是非常容易借到的,再加上我对哲学有一定的兴趣,我认为它很神秘。我带着一种...[详细内容] |
|
|
|
[孟宪义]:因为不管是孔子还是释迦牟尼他们生活的时代都是在公元前两千五百多年。可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不是啊,到公元前两千五百年的时候,也就是战国时期我们的文化正处在百家争鸣的时候,文化已经非常辉煌了,前面还有大段的时间,这部分的文化在《周易》里面。《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根,所以我在路边上看看到算卦的或者在网上一涉及《周易》都是算卦的,我觉得很伤心,我们这么伟大的文化,儒释道三家文化的根最候被大家知道和了解的就只剩下了算卦,这是不可以的。孔子时期,两千五百多年,上溯到周文王大约又早了八百多年,之前还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喾)、唐(尧)、虞(舜)之书...[详细内容] |
|
|
|
[孟宪义]:应该说没有特定的,只有约定俗成的,比如大家常画的梅兰竹菊,是一种历史的演变。为什么要画这些?从人文精神的角度来讲,它表现了一种君子之风。兰花的姿态并不妖艳,香味儿也不冲、颜色也不好看,但是他那种淡淡的香味沁人肺腑,号称王者之香,并且它不招摇,一定是在草丛里面、石头边上、山谷里面,“任是无人也自芳”,这样的一种君子品德。梅花的品德,“众方凋落独鲜艳”,所有的花都掉落了,只有梅花再开,就像是主席诗词“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这种气节。菊花,“人淡如菊”,竹子,“虚心直节”,这都是从人文的角度。从学术的角度看,我们的中国画是以线构成的,梅兰竹菊的用线可以称得上是我 ...[详细内容] |
|
|
|
[孟宪义]:当你了解了我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之后,你所谓的改变就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我们是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了,中国的书画是两千年的积累,单纯中国的绘画还有一千多年的积累。这说的都是完整的绘画,比如唐末五代出现的山水、花鸟的分类,在唐代只有人物画,北宋将山水画、花鸟画分离出来,确立文人画,无论哪一个阶段它的历史都是够长的,并且有这么多人积累。一个人的一生研究一百年的历史,但是我们不能研究上千年的历史,何况我们的一生不是没有很多的时间做这类的工作?我们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中国艺术的特征是学生和老师的心口相传,老师研究几十年的经典的东西能传授给学生,学生再研究几十年再传给学生...[详细内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