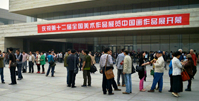-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组图:中国最早旅法画家常玉绘画作品欣赏

常玉作品

常玉作品
“我的生命中一无所有,我只是一个画家。
关于我的作品,我认为毋须赋予任何解释,当观赏我的作品时,应清楚了解我所要表达的……
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在巴黎的最初十年,常玉已经画了上千张人体临摹,在画室的破沙发上,落座过至少一二百个当得起美字的女人。如此锻炼出一双发现“美苗”的“淫眼”:“一半因为看多了缘故,女人肉的引诱在我差不多完全消灭在美的欣赏里面,结果在我这双‘淫眼’看来,一丝不挂的女人就同紫霞宫里翻出来的尸首穿得重重密密的摇不动我的性欲,反面说当真穿着得极整齐的女人,不论她在人堆里站着,在路上走着,只要我的眼到,她的衣服的障碍就无形地消灭,正如老练的矿师一瞥就认出矿苗,我这美术本能也是一瞥就认出‘美苗’,一百次里错不了一次;每回发现了可能的时候,我就非想法找到她剥光了她叫我看个满意不成,我记得有一次在戏院子看着了一个贵妇人,实在没法想(我当然试了)我那难受就不用提了,比发疟疾还难受—她那特长分明是在小腹与……”对于女人体的精通,使得常玉脱出了皮相上的情色。
他跟徐志摩描述了一位法国南部面包师夫人的身体,简直如梦似幻:“(她)够打倒你所有的丁托列托,所有的提香,所有的乔尔乔尼……她通体就看不出一根骨头的影子,全叫匀匀的肉给隐住的,圆的,润的,有一致节奏的,那妙是一百个戈蒂埃也形容不全的,尤其是她那腰以下的结构,真是奇迹!你从意大利来该见过西龙尼维纳斯的残像,就那也只能仿佛,你不知道那活的气息的神奇,什么大艺术天才都没法移植到画布上或是石塑上去的(因此我常常自己心里辩论究竟是艺术高出自然还是自然高出艺术,我怕上帝僭先的机会毕竟比凡人多些);不提别的,单就她站在那里你看,从小腹接上股那两条交汇的弧线起直往下贯到脚着地处止,那肉的浪纹就比是—实在是无可比—你梦里听着的音乐:不可信的轻柔,不可信的匀净,不可信的韵味—说粗一点,那两股相并处的一条线直贯到底,不漏一屑的破绽,你想通过一根发丝或是吹渡一丝风息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同时又决不是肥肉的黏着,那就呆了。真是梦!”

- • “人美·新生力量”第四届中大艺展美术展18日开展
- • 观者赞叹孙伯翔艺术造诣:字得清凉境 画得天趣美
- • 阮克敏、王全聚与梅葆玖在天津“梅府”以艺会友
- • 贾广健:让我们用浓墨重彩描绘时代画卷
- • 陈冬至等当代名画家罕见的文革时期写生作品
- • 天津画院建院35周年作品展将在津开幕
- • 天津画院召开学习贯彻习总书记讲话精神专题座谈会
- • 享受书法—王承尧书法作品展在天津图书馆开展
- • "中国天津当代著名画家作品展"在印尼东爪哇省开幕
- • 第七届亚洲联盟超越设计展在天津工大开幕
- • 孙伯翔书画展在天津美术馆开幕
- • 天津举行纪念希望工程25周年书画捐赠活动
- • 著名女画家梦玉近日赴美国作中国画讲学及作品展示
- • 姜维群:援手,为圆一位书家梦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