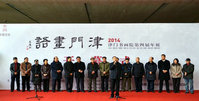小说家龙一 (包仲川 摄)
如果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气场,那么在我看来,龙一的气场是温厚、舒适、悠然自在的。
采访时,他的电话不时响起,其中两个是电视台邀约出镜做节目,皆被他谦卑委婉而态度坚定地回绝了。放下电话,龙一笑着说:“写小说我乐于让主人公历经困境、诱惑和考验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可是生活里,我可不想被名利彻底改变”。
两年前,龙一因《潜伏》而被大众熟知,也因为《潜伏》,他自言被“名利相逼”不知所措,只能逃避。而两年后,由《借枪》引发的关注和话题再次让龙一走入人们视野,但这一次对他而言,心境已经大为不同。他说因剧而火的“虚名”带来不少诱惑和干扰,现在他已经逐渐找回从前简单快乐的生活,继续在小说的世界里愉快“潜伏”。
追随自己趣味
1986年,机关干部李鹏正式转变为文人龙一。1997年,龙一听了朋友劝,改行写小说,将自己在历史研究中发现的“妙趣”,通过小说表达出来。
《借枪》激起了很多人对老天津的兴趣,而原作者龙一对天津历史文化的深厚情怀,我也早有耳闻,所以在见到这位同乡之前就先有了几分亲切和好奇。
老乡见到老乡,首先免不了攀谈“出处”,而攀谈之下我们都颇觉意外和有趣,从出生地和早年的居住地点来说,我们不仅同属于天津地域文化保存比较好的河北区,而且竟然住过同一条胡同,就读过同一所小学和初中!虽说时间上相差了近二十年光景,可空间上的轨迹几乎是交织重叠的。在往日记忆几乎随着那些胡同、平房院落的消失殆尽而渐渐模糊的时候,忽然巧遇一位老街坊、老邻居、老校友,这怎不叫人惊喜?
而龙一的兴致也仿佛被点燃了,“我们住的那片区域早年是袁世凯督直施行‘新政’开发的新区,所以有大量外来移民聚居,你知道吗,上学必经的那个铁道口早年是天津两派混混的楚河汉界……”听龙一津津有味地讲着老天津的故事,能感觉到那是一种流淌在血液中的文化情怀,这情怀滋养了他,也滋养了他笔下那些新意扑面的故事。“天津这座城市太丰富了,20个作家写一辈子也写不完。”龙一说。
自古漕运天津便是大码头,开埠百余年,中国社会发生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几乎都与它发生关联,因此天津的近代史给龙一的小说提供了很多灵感,《潜伏》、《借枪》、《暗火》的故事皆发生在天津。在转让天津题材小说的影视改编权时,龙一特别要求不能改变故事发生地,“很多人不了解天津,认为这样的故事只能发生在上海,其实一战后天津是远东最大的情报市场,很多职业间谍常驻于此。”
他在自己博客上专门开辟了“天津词典”专栏,以小说家的眼光解读的天津历史很有妙趣,比如《作一回青帮老头子》、《八大碗与张作霖》、《公馆里的赌局》……龙一说,真正的天津历史不单存在于政治中,还存在于生活细节中,比如时尚、生活趣味、人的思想。“天津文化有三块,租界文化、老城文化、移民文化,所以它吸收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地域性质造就人的性格,就是通权达变,不较真,喜欢舒适地达到目标,如果不成也会去拼。”
小说里的天津味儿在电视剧中被演绎得淋漓尽致,特别是熊阔海身上幽默、豁达、爱逗闷子的劲儿,而龙一本人也有着天津人特有的开朗幽默,当我说“最初看到‘龙一’这名字我想到的是坂本龙一”,他听了哈哈一笑:“‘龙一’还是我大学刚毕业时给自己起的,源自《周易》乾卦第一爻‘初九,潜龙勿用’。名字对人的生活有隐喻,这个名字几乎隐喻了我后面的生活和生活态度。简单说吧,老实待着,别轻举妄动!”
龙一本名李鹏,1984年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天津教卫委,那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可工作一年多后他主动请求调走,去了天津市作家协会“创研室”,龙一说这并非有心栽花,而是因为更加满足了他对职业的需求:少干活,多学习。那是1986年,机关干部李鹏正式转变为文人龙一。
但他似乎并不急于获得什么,在好友肖克凡的印象中,那时候常常看到龙一手里捏着一只宜兴紫砂壶,一派通达随和的平衡状态,相比身边一大群勤奋进取、想成名成家的业余作者,他的散淡形成鲜明对照。
他只醉心于自己的兴趣,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龙一钻研于中国古代生活史,似乎要走学者之路。他喜欢从字缝儿里寻找古人的生活轨迹,搜集、考证,甚至揣测、拼凑起一个人的生活史,他开玩笑说自己就是研究“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这十个行业,没有切实目的,只是因为有乐趣。他曾计划写一本《中国古代享乐史》,但那时人们对历史的态度很“严肃”,而他的选题又很“腐败”,所以未能如愿。但是这些研究让他攒了一肚子的学问。肖克凡曾见到龙一展示的一张唐朝长安城地图,坊间与坊间标得清清楚楚。而关于晚清与民国,他也说得头头是道,好像是前朝遗民。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文学创作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社会上的流行词是“下海”,曾有一个茶商惊叹于龙一对传统文化的知识,力邀他一起做茶叶生意,“结果赔了个精光,也把别人的钱赔了,这告诉我‘不是干这行的料’,还是回作协接着研究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吧。”龙一笑着回忆。
读书对龙一来说是件极大的乐事,而他的兴趣之广、读书之杂,在朋友中也是有名的,时常有人在写作文言片段时求助于他,他会说得一清二楚。作家林希就曾提到:“龙一读书可谓无所不读,上至高深哲学文学理论著作,下至杂七杂八琐碎文章。当年我写《蛐蛐四爷》,就曾经向龙一求证。他借我关于蛐蛐的‘专著’,果然市间难觅,让我很是卖了一阵关子。”
在古代生活史之后,他的兴趣转向了近代城市史,而其中“城市地下工作者”的生活又将他的兴趣引向了中国革命史。“追随自己趣味,很快乐,至少不委屈自己。”龙一说。
九十年代中期,在他正兴味盎然地研究城市史时,有一次,肖克凡很认真地对他说:“你积累了这么多东西,不写小说可惜了,写小说就是靠直接生活积累和间接生活积累。”而亦师亦友的林希也对他说:“将你这些闲趣知识写成小说一定好看。”终于,1997年,龙一听了朋友劝,改行写小说,将自己在历史研究中发现的“妙趣”,通过小说表达出来。
《借枪》隐喻生活
“把英雄塑造得无所不能、高大全,是个偷懒的办法。实际上,人本身都是很弱小的,没有谁能轻而易举克服困难,而且要付出代价。”
开始写小说时,龙一已经37岁,这时他发现此前研究的所有那些“偏门”都是在为小说做准备,那些闲趣知识、历史掌故都成了他故事中鲜活的形象和细节。同时,他把从历史中获得的对生活、对人性的观察都融进了小说。
读龙一的小说会发现,他的小说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有的都是身处困境,在信仰、使命和日常生活间挣扎的人们。《潜伏》里有洁癖的小知识分子余则成,被阴错阳差安排与鲁莽村妇翠平做假夫妻;《长征食谱》里一心想当英雄的药膳厨子,最后将他的铲子和大铜锅变成了最有利革命的武器;《在传说中等待的》主人公崔大少,在世人的误会与嘲笑中竭力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小说《借枪》里的荒诞和黑色幽默在电视剧中被演绎得更加淋漓尽致。
“其实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荒诞,只不过我们自己没意识到。研究历史我发现,生活是件非常荒唐的事情,人的需要和生活给他的往往有很大差距,这差距就是荒诞的原因。把英雄塑造得无所不能、高大全,是个偷懒的办法。实际上,人本身都是很弱小的,没有谁能轻而易举克服困难,而且要付出代价,物质的、情感尊严的、生命的乃至灵魂的代价,就像熊阔海为了完成使命,压上的风险代价越来越高。中国人说‘义所当为’,关键是应该到什么程度。熊阔海放弃妻女,在人性上就染上了缺点,付出类似于灵魂的代价。”龙一解释说。
他在研究历史中发现,五千年来生活的本质从来没有发生变化,今天的人面对一个事件、困难、诱惑时,思考方法、判断依据、人情事理和古人毫无差别,而变化的仅仅是生活细节。“熊阔海是刺客的一种。古代刺客很多,熊阔海很像古代的刺客聂政,他们体现的都是‘义’。忠孝节悌、礼义廉耻、仁爱,现代人的生活也到处弥漫着这种东西,只不过我们曾经把这些都砸烂了,现在需要慢慢恢复,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不可磨灭的。”
龙一认为,在小说里表现被历史遗忘、遮蔽的内容,还原他们的生活真相,这是新鲜感和趣味的来源,也让写作充满成就感,“许多人看《潜伏》,不相信有翠平这样的地下党人,是因为人们不熟悉那时的生活。”
熊阔海被逼到走投无路,最后舍命一击。在龙一看来,生活的本质就是这样,英雄是存在于一瞬间的,抛开那一瞬间回溯去看,英雄可能是各种各样的,生活中存在什么样的人,英雄就有什么样的人,或者说革命队伍里就有什么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英雄,关键是是否有成为英雄的机会。而小说和电视剧结局不同,熊阔海并没有牺牲,龙一说,不想把主人公写死是他个人的写作习惯。在用巨大代价赢得了一个目标后,熊阔海整个人在生活、精神上也不再是刚出场的人,这段人生经历彻底改变了他,讲故事的目的就达到了。
但龙一非常欣赏电视剧对人物的改造,《借枪》的编剧是福建才子林黎胜,龙一曾陪他一起在天津的书店里找资料,“买了足足有50斤资料,装车上拉回了北京。现在看,他不仅把50斤资料读完了,还阅读了大量东西。他是个福建人,连普通话都说不好,居然让这部电视剧充满了天津味,让小说的荒诞和诙谐在电视剧里得到加强和发挥,这令我惊叹。”
对于剧中熊阔海之死,龙一说:“这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够壮烈、才有戏剧感染力,另外,才避免续集嘛。所以熊被编剧写死了,我很赞成。”说完他自己先被这玩笑逗乐了。
讲故事的“闲人”
写《借枪》时,他专门跑到中国军事博物馆,围着歪把子枪琢磨了好长时间。因为日常生活很简单,他发明了一套另类体验办法——动手做实验。
自1998年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第一篇小说《我是一个马球手》开始,龙一至今写了300多万字的小说。由于对古代历史比较了解,他先是写了一批以唐代生活为背景的中篇小说,后来又转入清末民初,进一步赢得写作空间。因为研究近代城市史他写了《暗火》,研究中国革命史写了《潜伏》、《借枪》、《代号》等,故事大多发生在天津。另有三篇是关于长征的故事。而他早期的长篇小说《深谋》与《迷人草》集中体现了他的小说观念,只是没有引起文坛的充分注意,龙一对此并不介意,始终不慌不忙地写着。
“我的小说一直非主流,很边缘。现在有读者了,这是我最幸运的事,以前我知道的只有两个读者,一个是我太太,一个是我女儿。”龙一笑着说。
在2007年《潜伏》火爆之前,写小说对他来说几乎没什么收入,但是小说本身带给他无尽乐趣,他醉心于每一部小说,寻找前所未有的人物和结构,“我不是文学家,我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人,生活当中有无数有趣味的故事。”他把写故事当成一种自娱娱人的过程,常常在写到一半的时候先让太太和女儿看,如果她们觉得好、想继续看,他就会兴致勃勃地写下去。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只凭感觉写作,龙一对小说理论和技术也钻研得颇深。他在写作过程中,会不时把自己的心得体会记下来,他的博客专门开设了“小说技术”的专栏,里面有创作上的感悟,也有方法上的总结,“把自己的创作方法贴到博客里,一定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希望感兴趣的人会去看,如果有人从中学会如何写小说,我会觉得很开心。”
龙一对知识细节的追求也是出名的,2006年写《借枪》时,因为他对枪械的了解仅限于书面知识,为了把熊阔海借来的那挺歪把子枪写准确,他专门跑到中国军事博物馆,围着歪把子枪的展台拍照、琢磨了好长时间,乃至管理员都开始注意他的举动了。
因为日常生活很简单,所以他的小说细节更多来自间接生活、来自史料书籍,不过,他自己发明了一套另类体验办法——动手做实验。说其另类,是因为他的方法实在是让人跌眼镜。写《古风》之前,他发现不是所有地下党人都很有钱买炸药,一个没有钱的地下党人需要炸药怎么办?只能自己制造。他想求证一下,于是买来二斤氮肥在自家厨房提炼硝酸铵,幸好,在还没炒成固体时其味道就引得邻居们恶声四起了。在他获“中国作家百丽小说奖”的《长征食谱》里,写了一个有着几分药膳本领的炊事兵的故事,他为了把皮带皮鞋做成能下咽的菜,用上了自己做药膳时发熊掌的本事,还原了皮带和皮鞋的胶性。龙一为了证实这的确可行,剪碎了一条皮带和一只皮鞋,放在锅里煮,“不过我偷懒用了高压锅,做熟了尝了尝,的确可以下咽。”龙一露出自得其乐的笑。
“先把自己哄开心了”,这是龙一进入写作的方式,也是他的生活态度。他的写作生活通常是这样的:早上起来吃过早点,沏上茶,听听音乐,直到中午过后才打开电脑。因为颈椎不好,他一般是半躺在床上写东西,身边左茶壶、右水果伺候着,状态来了就多写点,没有状态就少写或是干脆不写。他很少交际,只是偶尔才和朋友见个面。遇到好天气,他会把车当作移动书房,从城北开到城南的一个小湖边,看一整天的书。
“龙一写作上慢慢悠悠,不像时下某些急功近利少年,抓着好行市,笔头子猛刷。龙一另有一种活法,小说不到非写不可的时候,绝不匆匆动笔。”林希在一篇文章中评价龙一“不骄不躁真性情”,他写道:“龙一自己一味写来,写到高兴时虽也颇觉得意,但最终也还是将写作当作是娱人娱己的快活事,从来不知将作品当做一种资本,以此招摇于市,为自己争点什么待遇。”
守护惯常生活
“看了那么多古代人的经验,看了那么多人在名利荣耀面前栽了跟头,觉得生活毁灭你太容易了。为了避免自己毁掉自己,所以我停了下来。”
2009年《潜伏》的走红打破了龙一惯常的生活,突如其来的名声像一颗巨石投入了平静的湖心,一度令他不知所措,许多影视公司找上门,有的要买他的作品改编权,有的要请他做编剧,有的要为他出书……而他的感受则是“被名利相逼”:“我是沾了电视剧的光,浪得虚名,现在,生活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不能假装没有这个东西。”
他干脆选择了向后退一步,搁笔休息,“如果积极应对这种冲击,拼命生产,生活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我很担心这种改变,因为思想上走偏了回不来。我看了那么多古代人的经验,看了那么多人在名利荣耀面前栽了跟头,觉得生活毁灭你太容易了。为了避免自己毁掉自己,所以我停了下来,这是生活的自觉嘛。否则,稍一动摇,可能就投入到火热的生活当中去了,我清楚地知道我肯定遍体鳞伤。干脆退一步,这也是胆小的标志吧。”龙一有些自嘲地说。
他始终觉得无论《借枪》还是《潜伏》,真正功劳最大的是导演姜伟。“我说自己在潜伏里作用非常小,也就是1%,这是实情,结果被认为过度谦虚。现在人们把真话当谦虚,这是非常滑稽的社会现象。”他打了个比方,原著类似于原料,而作家类似农民种出小麦,至于小麦用来做什么则是编剧导演的事,“我很幸运,《潜伏》和《借枪》这两个戏都做得很好,有的小说家就没这么幸运。”
搁笔两年,龙一希望自己重新回到从前的状态,然后继续在写作中“潜伏”。不过,真正回到从前的生活,并不容易,“好像鱼被钓出来了,得挣扎才能跳回从前的生活。”对他来说,最不容易的是回到过去的写作心态,“现在写作时需要忘掉或克服掉考虑观众、考虑导演编剧的这种心理,能把这个克服掉就能回到我以前的状态,但不容易,这是在克服名利的诱惑。”
为了稳定自己的状态,回到心无旁骛的写作生活,龙一与《潜伏》和《借枪》的制作人张宏震、张静夫妇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而他们对他写或不写、写什么,从没有任何要求,“这是他们对创作者的理解和体贴,让我在最舒适的状态下写最想写的东西,所以没有命题作文的压力,仍可以由着自己的趣味来写。”遇到这样不急功近利、志同道合的合作者,让他觉得非常幸运。
在写作之余,龙一很有闲趣,“读书写作莳草玩物之余,尚有调和鼎鼐之好”,每年他要学一门手艺,雕假山石、鉴定古玩等等无所不学,甚至曾跑去学做拉面。他喜欢书画、摄影,偶尔会向好友展示一下修炼多年的厨艺,每件事在他手里都能做得有滋有味。
在他家的墙上挂有一幅南宋画家梁楷《泼墨仙人图》的复制品,朋友们看了都说画中人物俨然是龙一的漫画,这让他听了很受用,专门与画中仙人合影,放在自己的博客上,并认真地写下自勉之言:“我自己照镜子比比,真的希望很像。我说的‘像’不是模样,而是想要浇开胸中垒块,放掉手里紧握的俗物,坦荡襟怀,舒展袍袖,赤足趿鞋,活出画中人物的那股子放达、洒脱的劲头儿。”
坦荡襟怀,舒展袍袖,赤足趿鞋,真是快乐的至高境界!聊天中,我注意到龙一有两次提到“最幸福的时光”,一次是提到二十年前和好友肖克凡常常跑去古籍书店寻觅典籍野史的时光,而另一次是提到《潜伏》成名前写小说的那些年,虽然不被关注,但是自得其乐每天都很开心,那是一种很纯粹很简单、与名利毫不相干的快乐。
是的,人生不仅仅为了成功,平淡中也有真乐趣,而趣味才是燃料和真正动力。
在这样一个浮躁、不甘寂寞的时代里,龙一始终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趣味和天性保存完好,不为浮名所累,不受外物所役,如同他笔名所言“潜龙勿用”的境界,无论外界环境如何改变,都能不受影响,保持自己独特的思想与处世之道。
我想,对于喜爱他的读者来说,如此的龙一是值得期待的。 文汇报驻京记者 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