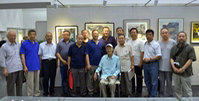-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天美教授郭雅希新著出版 解读当代艺术的天津样本

《个案与历史——与天津有关的中国当代艺术》,郭雅希著,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作为首都北京的“卫城”,天津在历史上似乎一直处于一个配角的位置。然而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天津孕育了极其重要的前卫艺术形态,如革命性的实验水墨,托古改新的新文人画,拯救传统的新工笔,奇绝鬼拔的表现性油画,等等。这些艺术形态的产生和形成与天津独特的地域性文化和历史经验息息相关,同时天津当代艺术家们的探索与奋斗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史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当代艺术群体运动的缩影,体现了自85新潮以来,中国艺术家们在传统遗产与现代语境,东方文化与西方冲击,本土特色与国际视野之间的抉择。因此,本书将天津当代艺术作为一个案例,从探讨天津地域性文化出发,揭示天津当代艺术与其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并见微知著地对与其相关的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史阐发思考。

郭雅希
作者简介:
郭雅希,1958年生于天津,现为天津美术学院西方美术史研究方向硕士生导师,美术史论系主任,天津美术家协会艺术理论委员会副主席、秘书长。出版专著《现实主义》,主编《韵律无声》《开放的中国实验水墨》(香港)、《天津油画史汇编》等。多次主持策划学术和展览活动,如“生存”与“表现”观摩展及学术研讨会(1999年,天津美院美术馆),“对话•1999”艺术展(1999年,北京国际艺苑美术馆),“表现主义大师——伊门道夫版画展”(2002年,天津艺术博物馆),“与你有关——当代影像装置展”(2002年,天津文化实验空间),“人·伦理·空间——实验建筑”艺术展及学术研讨会(2002年,天津文化实验空间),“墨与光色的对话——中德艺术家形上方式”艺术展(2004年,天津文化实验空间),“质性:实验水墨报告”展(2005年,北京红门画廊),“当代艺术史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天津美术学院)等。
简要目录:
第一章 作为天津文化的表征:表现性的艺术传统
一、天津的地缘文化特征
二、独具一格的“表现性”艺术
第二章 津门水墨:一种源自天津的后现代水墨现象
一、天津多元水墨现象分析
二、天津当代水墨人物“三剑客”
三、现代水墨的实验者们
第三章 在朦胧中前行:天津当代艺术的探索
一、当代性的建构
二、并非仅关涉语言的抽象
三、仿像、符号、图像:后现代的景观
四、对话:文化协商
五、走向更新的一代
第四章 当代艺术与学院教育
一、学院的前卫
二、当代艺术教育:一块缺失的阵地
三、当代艺术与学院教育
并非迸发的当代(结论)
本书前言
赫伊津哈在他的论文《文化史的任务》中曾如此说道:“如果我们看不到生活在其中的人,怎么能形成对那个时代的想法呢?假如只能给出一些概括的描述,我们只不过造就了一片荒漠并把它叫做历史而已。”这段话几乎可以被视为文化史研究乃至整个微观史学的箴言,同时也恰如其分地道出了个案与历史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
对于历史的书写,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延续着一种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叙述模式,而这种宏大叙事的集大成者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历史书写传统。但是随着后现代学者们对元叙事的不断质疑,以及对宏大叙事的不断攻击和反思,利奥塔曾经在他的那本惊世骇俗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我认为‘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就合法化元叙述机制的不合时宜而言,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形而上哲学和建基于其上的学院制度本身也出现了危机。叙事功能已经失去其功效,因为能够产生原动力的伟大英雄,巨大灾难,伟大航行和崇高目标都已烟消云散。”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便逐步瓦解,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学界之内风起云涌,从女性主义对男权的颠覆,到后殖民主义对西方强权的挑战,从文化史对经济决定论的质疑,到微观史学的全面兴起,仅就学界内部而言,层出不穷的理论学说对传统的历史书写方式不断地发起挑战,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历史研究的时代。而这些新学说的共同倾向都是旨在反拨现代主义以来所建立起来的话语体系,将以往受到压制或忽略的范畴如感性、身体、个体、意识等解放出来,个人的言说开始取代抽象的权威,个体的经验开始消解英雄的群像,历史叙事的统一性和普遍性被打破了。
从布克哈特开始,历史的书写便逐渐朝着微观与细节化的方向发展,他的扛鼎之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着重强调了“个人的发展”而非历史的必然规律,他津津乐道且事无巨细地描写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生活和文化,并突出了其中所体现的个人主义与自我意识,将具体的个案不断汇集成为大写的人文主义。其后的瓦尔堡、帕诺夫斯基、赫伊津哈等文化史家纷纷从细节入手,来审视和研究历史。对于个体的关注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催生出一大批颇具影响的学术著作,埃曼纽•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1975)记录了12至13世纪法国南部的一个小乡村的方方面面,作者以“显微镜”式的研究手法将一个“小题材”做得有声有色,为我们展示了蒙塔尤村民们的日常生活、家庭关系、婚姻、工作、生老病死以及宗教价值观;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元老之一爱德华•汤普森(E. P. Thompson)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中另辟蹊径,通过对18世纪英国工人和农民的实际生活的考察,指出了共有的文化环境与生活习惯对于阶级意识形成的重要性,打破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克利福德•格尔茨的(Clifford Geertz)的经典篇章《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收录在他的《文化的解释》一书中,1973)则采取了一个更为独特的角度,在对于斗鸡这一看似庸俗而平凡的娱乐活动中,他发现了这一游戏中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民族、礼仪的深层意义,从斗鸡这一节点延展至整个有关巴厘岛的文化网络,形成了一部深刻而精彩的民族志。此外,还有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虫:一个17世纪磨坊主的世界》(1976),娜塔莉•戴维斯(Natalia Davis)的《马丁•盖尔归来》(1983),林•亨特(Lynn Hunt)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1993),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制作路易十四》(1992),丹尼尔•罗什(Daniel Roche)的《启蒙运动中的法国》(1993),杰克•古迪(Jack Goody)的《烹饪、菜肴和阶级:比较社会学研究》(1982),丹尼尔•罗什的《服装的文化:‘古王朝’的装束与时尚》(1989)等诸多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史著作。这些著作无不是以个案为基础,来探究处于某一特殊历史环境之中的具体个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打破了“自上而下”的历史叙事体系。在丰富多彩的个案研究与个体叙述之中,历史被拉近到读者面前,有血有肉,呼之欲出。
作为文化史、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论美国的民主》(1835,1840)和《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尤其是后者,几乎已经成为了近代以来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必读书籍。经历了七月革命、二月革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的托克维尔近距离地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回顾和审视,发掘出了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以一位亲历者的身份细致地描述了当时的教会、贵族、农民和第三等级的生活状况,首次将宏大的历史问题化为最为具体的细节叙述,条分缕析地剥离出了历史的真相。在中国,个案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也涌现出了许多颇具影响的著作。吴文藻、费孝通等都是运用这一方法论的先驱,尤其是后者的《江村经济》对于国内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意义重大。个案研究的优越性显而易见,正如风笑天所指出的:“个案研究是对一个个人、一件事件、一个社会集团,或一个社区所进行的深入全面的研究。它的特点是焦点特别集中,对现象的了解特别深入、详细。”近年来,四川学者岱峻有关“消失的学术城”李庄的一系列研究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他以如今已不为人知的古镇李庄为节点,深入到了抗战时期的民国学术史之中,展现了这个曾经聚集了一国之精英的文化中心在那个特殊时代的历史故事与人文景观,填补了一段由于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学术空白。
由此可见,无论中西,个体化的叙事模式越来越成为一种更加行之有效地接近历史和文化的手段。学界对个案研究、口述史、文化史、微观、局部、碎片式论述予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因为个体正是构成历史文脉和公共意识的最基本细胞,而且也最能体现文化的鲜活与特定性。如今,个体化的叙述已经被广泛引入了文学、电影和历史研究等各个领域,然而在国内,以个案为基础的艺术史著作并不多见,尤其是针对某一地区的当代艺术史写作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将个案研究引入当代艺术和艺术史的书写,不仅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特定时期或地域的艺术现象,也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尝试。
正是以上原因使笔者决定以个案研究的方法来探查与天津地区有关的当代艺术发展状况。选择天津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作为首都北京的“卫城”,天津在历史上似乎一直处于一个配角的位置,无论是政治经济地位,还是文化发展都逊于前者。尤其是在当代艺术领域,天津更是由于毗邻当代艺术的前沿阵地而被遮没了光芒,难以受到足够的重视与正视。但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天津,孕育了极其重要的前卫艺术形态,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艺术家,例如实验水墨的领军人物张羽,新工笔的集大成者何家英,表现性水墨画家李孝萱、李津、阎秉会,此外还有汲成、广军、张胜、孙建平、王公懿、苏新平、邓国源、宋永平、周世麟、樊海忠、景育民、李志强、刘庆和、魏青吉、孔千、祁海平、马元、曲建雄、张利语、张浩、忻东旺、蔡锦、彭薇、张方白、马树青、江海、袁文彬、刘军、马轲、管勇、王爱君,等等,他们或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或是在这里接受过长期的艺术教育,或是移居此处从事艺术创作,他们的探索与奋斗是中国当代艺术史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群体运动的缩影。无论是革命性的实验水墨,还是托古改新的表现性水墨,无论是拯救传统的新工笔,还是奇绝鬼拔、独具特色的表现性油画,抑或各种形态、异彩纷呈的水墨实验,都体现了自85新潮以来,中国艺术家们在传统遗产与现代语境,东方文化与西方冲击,本土特色与国际视野之间的抉择,他们曾经彷徨,焦虑,无奈,困惑,也曾经激越,亢奋,愤怒,豪情万丈。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他们曾经的纠结、探索与突围,不仅仅代表作为个体的艺术家的经历,也不仅仅代表某一地域的艺术创作,而是整个中国当代艺术所共有的经验和回忆。因此,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中,除了北京、上海、杭州等人所共知的前卫艺术中心,天津亦是一方不可或缺的阵地。对于天津艺术史与文化史的研究亦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艺术流派,同时也能够以另一角度来窥探中国当代艺术运行的轨迹。
其次,天津当代艺术的价值不仅在于纵向的历史观照,更在于它是天津这一地域的文化表征。上文所提到的艺术家们,无论他们以何种方式与天津发生联系,其作品中都浸染了这一方水土所特有的文化底蕴。从历史上来看,天津虽然并不能称之为古城,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它在列强纷争的近代迅速成为一座世界瞩目的城市。人们常说“近代百年看天津”,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天津的近代史也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作为重要的海港与漕运中心,天津在西方殖民狂潮中首当其冲,曾经被英、法、德、意、美、日、俄、奥、比九国先后划分租界,一个城市之中,九国租界林立,这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然而,天津在承受奇耻大辱的同时,也在被迫开放的过程中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城市之一。电信公司、自来水厂、公立医院纷纷落户天津,电灯、电话、电车、电影、西餐、教堂出现在天津市民的生活之中,先进的科学技术、全新的城市规划、精英的文化理念,深刻改变着这座城市。西方殖民者梦想着在这个东方港口重现他们在欧洲的故乡,这反而从侧面推动了天津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旗号之下,天津也成为洋务运动的阵地,中国第一条电信线路,第一条公交线路,第一条铁路,第一艘潜水艇,都诞生在这里。由于天津便利的生活条件与相对和平的租界,吸引了大批学者和知识分子精英来此聚集,梁启超、严复等人的先进思想正是从海河的两岸传播到全国。在这样求新开放的文化环境中,天津出现了早期的现代美术教育,最早将“西洋画”和西画教育引进中国的先驱之一就是当时的天津学子李叔同。之后,又有陈之驷、严智开、汪洋洋、刘啸岩、潘元牧、李骆公等画家纷纷留学海外,将现代艺术的形式与观念带回中国,带到天津,培养了一批具有表现主义风范的艺术家;现代教育先驱严修之子严智开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天津创建的市立美术馆,向人们展现塞尚、马蒂斯等现代主义艺术风格,对当时的中国艺术产生了巨大的撼动。这也是导致天津自近代以来就形成注重表现性艺术传统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不仅体现在李文珍、汲成、广军、刘秉江、王公懿、孙建平、孔谦等人的创作和教学之中,也蕴含在85新潮中“鸣社”群体的创作和李孝萱、李津、阎秉会等水墨画家雄奇恣肆的作品之中。
然而,天津并没有成为另一个上海,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小资情调仅限于身份高贵的寓公和租界区文化阶层,而几个世纪积累下来的古老传统和浓厚的市民文化气息依然占据着租界之外的世界。老城区里的老街、老巷、老字号,是天津传统文化生活的象征。租界内有美国好莱坞的20世纪福克斯分公司、意大利的回力球大赌场和德国的起士林西餐厅、英国的赛马场和利顺德饭店,人头攒动、生意兴旺;租界外的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贴饽饽熬小鱼、煎饼馃子、锅巴菜,以及各个相声茶楼同样生意红火。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的上流人士注重礼仪和优雅的风度,土生土长的老天津市民则讲究“老例儿”,家庭生活依据祖宗章法,穿衣戴帽要有“台面儿”,行事做人要讲义气。作为漕运中心和军事重地,渔民、脚夫、军曹是天津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性情豪爽、行事仗义,但又不免具有浓厚的江湖习气,好勇斗狠,尤其是在租界与租界之间的“三不管”区域,三教九流云集之处,更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兵痞”“混混儿”文化,与租界之内的绅士淑女形成鲜明对比。然而正是这些普通甚至庸俗的人们构成了天津最为鲜活生动的另一面。老作家林希曾在《北京时间》里将天津文化比喻为草根文化,将天津城市比喻为平民城市准确地概括出了天津本土文化的豪放自然、“接地气儿”的特点。画家李津笔下的饮食男女,李孝萱作品中无所事事的城市青年,都是天津市民文化的体现。
因此,正如埃曼纽•拉杜里在《蒙塔尤》的前言中所说:“在无数雷同的水滴中,一滴水显不出有何特点。然而,假如是出于幸运或是出于科学,这滴特定的水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如果它不是纯净的,便会显现出种种纤毛虫、微生物和细菌,一下子引人入胜起来。”如果鸟瞰中国历史或者中国当代艺术史,天津以及它的文化艺术不过是这浩瀚长河中的一个支流,然而如果我们采用细度或者深描的方式来进行近距离的考察,则会发现其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与充满了矛盾性的文化景观,及其艺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然,选择天津作为研究对象,也有一部分是出自笔者个人的原因。笔者是一名地道的天津人,同时在天津美术学院从事了多年的艺术史教学工作,切身感受到了85新潮等重大艺术运动对于天津的影响,也亲自组织和参与过天津当代艺术的实践,因此更能以一名亲历者的身份来讲述和还原天津的当代艺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笔者深入考察了天津的地域文化,并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许多天津艺术家和教育家,其中也融入了自己对于故土文化的独特理解,对于天津当代艺术的评述以及对于艺术教育的反思。因此,本书建立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具体个案为主体,力求能够真实再现天津当代艺术的脉络与面貌;同时,也将作为个体的天津艺术家们和艺术团体放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群体运动和思潮之中加以审视,以求使读者更清晰地了解天津当代艺术的历史价值。
依据以上思路,本书正文部分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介绍天津文化的地域性特点以及在此特殊的文化和历史氛围中所形成的表现性艺术传统,并将其与近现代以来的天津艺术史联系起来。第二章是对于水墨实验的具体窥探。这是由于天津是一个水墨重镇,这里涌现出了许多以水墨实验为主要创作方式的艺术家,其中既有以张羽为代表的实验水墨运动,也有以李津为代表的“新文人画”,还有以阎秉会为代表的“自由水墨”。可以说,中国水墨艺术的现代化转型离不开天津艺术家们的不懈探索,而这样的探索又是与天津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的。第三章则是对于其他各种面貌的当代艺术形态的审视,其中涉及大量在天津出生、工作和定居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中国都市文化以及当代艺术发展的脉动。第四章所探讨的则是当代艺术发展的推动力之一——学院教育。当代艺术与学院教育是一对相辅相成又常常相互龃龉的矛盾体:一方面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大多数都来自于学院,但另一方面,当代艺术在试图进入学院教学的过程中又举步维艰。这种现象是中国所特有的,它所反映的问题引起过学界的广泛讨论,学者们莫衷一是。那么,天津的学院教育在其中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在当代艺术与学院教育相互融合与冲击的过程中,天津的艺术家与教育者们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和思索,就是这一章所要探讨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虽然主要以天津艺术为研究对象,但却并不完全局限于天津本地的艺术家,其中既有受到天津艺术家感召的其他地区的艺术家们,例如由张羽组织和带动起来的实验水墨大军和典型的水墨实验者;也有与天津艺术形成呼应的其他地域的艺术创作和教育实践,例如中央美术学院四画室在当代艺术教育方面的探索。笔者如此安排,只为使本书呈现出一种更为开放的视角,将天津当代艺术置于与其他地区艺术探索的关联网络之中。
正如胡塞尔所说:“只有亲身投入到特殊性中,才能从中发现恒定性。”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之所以意义重大,就在于它使我们“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马林诺夫斯基语)。而艺术史的写作也是如此,我们在探究某一类作品、某一群艺术家、某一个年代或某一个地域的艺术现象之时,既要对其内部进行精细而深入的考察,又要发现它与整个社会、时代乃至历史的关联,既摆脱机械决定论的套路,又要避免个案分析走向极端和孤立,以达到“以微明宏,以个别例证一般”的目的。因此,个体叙述和个案研究并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由此而指向的一个更为宏大的文化景观,使读者在与具体而生动的个体案例的亲密接触中,体察到其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与共有倾向,从而引发对于当代艺术乃至整个艺术史的深刻思考。由此看来,作为个案的天津当代艺术史正是笔者的一次以微明宏、见微知著的尝试。
- >>相关新闻
- • 徐江:伟大的观念艺术
- • 中国首个专注于艺术影像的国际博览会上海闭幕
- • 艺术8奖得主苏菲兰的中国之旅——出神·入画
- • Jeffery Shaw:新媒体艺术旧的、新的与未来
- • 2014横滨三年展——审视艺术和作为文献的艺术
- • 天津美术学院召开庆祝教师节三十周年大会
- • 尤伦斯夫妇抛售亿元当代艺术品 或致多米诺效应
- • 珍珠:何迟个展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举办
- • 南风北舞——国画大师陈少梅艺术研讨会举行
- • 著名实力派画家马兆琳:我希望给我的画面注入什么
- • 艺术不一定得喜闻乐见:但要确保真善美
- • "祼视时空的绘画:实验非辨别性的心与眼"开幕
- • 今日换帅一周年观察:高鹏与今日美术馆的性格之变
- • 长卷:世界寓言当代艺术展将在天津举办
- • 从神圣到情色:西方艺术史中的浴女图像
- • 马拉之死:艺术史上最残忍的杰作
- • 廖廖:西方战争史背后的艺术史
- • 自画像800年:“这就是我,我为此自豪”
- • 在伦敦国家美术馆寻找色彩中的艺术史
- • 新任天津画院院长贾广健:古雅花鸟寓真情

- • 陈之海山水小品展在天津图书大厦开展
- • 韩必省:笔墨当属时代 画作雅俗共赏
- • 姜金军、陈丙利等博士画家走进滨海画美景
- • 视频:王俊生大写意画展亮相天津群艺馆
- • 孙其峰艺术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津举行
- • 尤里·博罗罗维茨基版画藏书票展在滨海新区开幕
- • 陈少梅国画艺术研讨会在津举办
- • 全国楹联大赛优秀作品联墨展在津开幕
- • 境由心生:陈丙利山水画展将在天津开幕
- • 天津:创意产业蓬勃兴起 做好文化这篇文章
- • 一墨一世界 一笔一乾坤—走进写意人物画家田娟
- • 中国楹联书画院实践基地—问津阁在古文化街亮相
- • 长卷:世界寓言当代艺术展将在天津举办
- • 别有黛色·张福义 康国林 马孟杰三人书法展将举行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