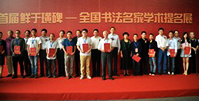-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艺术力量正在介入古村落活化与营造

大旗头村。锅耳墙是广府古村落中传统的建筑样式。
天津美术网讯 11月21至22日,由佛山市艺术创作院与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广府文化论坛,在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孔家村南天圣裔祠隆重举行。省内外古建筑保护、社会学、人类学、岭南传统文化艺术研究等相关领域专家50余人走访了佛山市特色古村落宜居示范与活化升级百村方案中的代表大旗头村、烟桥村、长岐村和松塘村,就古村落活化保护、文化传承、价值挖掘等各个方面展开讨论与建言。论坛上,专家们除了关注古建保护与利用、民俗挖掘与传承等问题外,特别指出当代艺术的介入对古村落活化与营造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从采风到艺术产业集群,艺术产业与古村落全方位结合
随着全球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城镇与乡村的面貌正急剧改变,文化身份的认同困境也在不断逼近我们。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曾大兴表示:“一方面,我们需要借现代化的方式快速融入世界现代文明体系,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保持自己的文化个性。”
“其实广东省拥有的古村落资源并不少,共有126处,在全国排第五位,这些古村落类型丰富多彩,大概可分为粤中地区、潮汕沿海和客家地区,另外我们还有少数民族村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劲告诉记者,这些古村落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衰败,原因众多。古村落活化工作需要政府支持、社会力量与村民主体的合力,近年来,当代艺术力量的介入也在古村落活化与保护中起到了越来越可观的作用。
“广州小洲艺术村是一个广州市民比较熟悉的案例,”曹劲首先介绍了由于大学城的建设,从艺术家租借村民闲置房屋作为工作室开始,十年来这个水乡古村发生的巨大变化,它充分证明了艺术的力量可以为古村落注入新的活力,在不过度商业化旅游化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另一个脍炙人口的案例是深圳观澜版画村。这个依山傍水而建的客家古村落,排屋形制,水塘、古井、宗祠、碉楼古色古香,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者、著名版画家、美术理论家陈烟桥的故乡,在官方规划了版画村之后,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入驻其中进行创作,产业发展与村落保护两不误,相关产业发展迅速,现在已形成重要的产业集群,不仅在古村落活化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而且成为了全国版画界的重要基地。
当大批艺术家来到同一个地点采风、创作时,山光水色极好的村落便逐渐成为艺术驻留基地,这也是一种古村落活化的方式。例如郁南县连滩镇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兰寨村,村中明清古建筑众多,文物古迹不计其数;甚至还有元朝末年间瑶族先民遗留下的古大屋、古围墙等。目前,兰寨村是“中国兰寨艺术创作基地”的主要创作场地,立足两广,面向全国,以写生、采风、创作为重点,以与著名高校实践课题紧密合作为手段,开展艺术写生、笔会、展览、展销等多种形式的艺术交流活动,努力打造成为艺术家、书画家通向市场的桥梁、代言人和经纪人的艺术创作基地。曹劲介绍说,最初建立中国高等美术院校写生基地时,村民们的态度漠然,但当他们看到这一计划为当地带来的就业机会与传播效应之后,都积极投入到相关工作中来,如今,村民们在进行合龙舞技艺培训,希望与美术学院的架上与影像创作者一起,将这一传统民俗传承下去。
如果说兰寨村的活化过程是政府与高校合力的结果,那么东莞万江下坝村的活化,则完全是由民间力量自发进行的。曹劲告诉我们,这里原本只是一座保存较为完整的历史文化村,在东莞文艺青年们自发的营造下,逐渐成为了一个集创意、设计、休闲、艺术于一体的生活街区,如今俨然已经成为了东莞的798,文艺青年的新蒲点。
与会专家探讨了这些案例之后得出结论:“乡村遗产是活着的遗产,它是持续的过程,包括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必要的改变,对古村落的活化,应承认其随着时间推移产生变化的部分,对文物建筑的保护标准与普通非公共乡土建筑的保护标准应有不同的规定;古村落活化成功的案例没有一定的模式,古村落保护和活化需因地制宜;在新增建筑中应坚持乡土性、文化性,避免景观性、同质化现象。”
影像不只是为即将消失的情境留影,也在重塑村落家园自觉
日前,仓东村因实行乡村文化遗产保育为目的的“仓东计划”而走上了国际舞台,荣获“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优秀奖)”。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到“仓东计划的自频道”的相关影像记录。第三届广府文化论坛与会专家中最年轻者、佛山市艺术创作院助理专职研究员罗祎英告诉记者,在互联网时代,社区(古村落)营造中的影像参与正在助力于在居民与社区环境、居民之间建立紧密的社会和心理联系,从而涉及到长期流转的共同生活印记与彼此认同的文化记忆,这是一种不同于官方话语的“家园遗产”。
“影像参与”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工作方法,说起来也不算什么新生事物,从二战之后就在许多国家有过成功应用,在我国也曾以不同的名称在西部地区的乡村、城镇社区中应用,它与异域情调式的风景摄录相区别,在技术上往往显得比较粗糙,与纪录片相比,又回避主题性的拍摄。在近年的当代艺术展、文献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类似作品与计划。罗祎英举例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金门籍导演董振良对家乡的拍摄,可以看做典型的案例。
这种工作方式产生的早期,艺术家们来到村落里,与村民同吃同住,赢得村民们基本的信任,然后用照相机或摄影机进行拍摄,将镜头对准日常化的场景,同时不断应对村民“为什么拍这些不够美的照片?别人看了会不会给我们村抹黑?”的疑问。随着国外观念的引进,近年来艺术家们的工作流程是建立一个工作项目,对村民进行简单的技术培训,把摄影机交给村民,让他们自由拍摄他们所感兴趣的与村落有关的内容。
“这里有一个角色的转换:艺术家始终是外来人,他再怎样努力贴近村民视角,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外来者的观察角度,预设一个拍摄目的。而让村民来拍摄自己,他们就不再是被摄的对象,一个被捕捉的客体,一个内源性的东西产生了,从他的视角来看他的家园,他真正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们拍摄的村民传统议会程序,记录村庄的公共生活,和外来者的拍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这种工作方式是一种培育,不是短暂的项目行为,而是长期的、内源的、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所有的影片都将成为文献,成为村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罗祎英解释说。
她介绍说,社区影像这种方式,在云南、贵州、四川地区已经运用得很成熟,广州地区目前还不明显,只有一些当代艺术家在尝试,例如徐坦和他的“社会植物学”——在珠三角的土地中寻找未知,发现城市化对自然环境和本土居民生活方式的干预。“徐坦的工作更偏实验性一些,我们所强调的影像参与是更广泛的参与,引入互联网情境,让村落被看见。古村落保护中最严重的问题是人员的流散,年轻人都离开去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村子几乎空了,他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失语。而互联网与影像结合,增强了传播效力,一方面让人们超越物理空间‘看到’他们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让离散了的村落原住民以及他们的第二第三代,通过这个媒介能够连接与交互。村庄共同体的意识不能只局限于现在。”(记者 冯钰)
- >>相关新闻
- • 钱海峰《绿皮火车》获第十一届连州摄影年展大奖
- • “芒:女性艺术家五人联展”亮相大韵堂
- • 相生:第四届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作品展闭幕
- • 徐锦江画展张丰毅黄秋生到场祝贺 传一幅画卖80万
- • 当代篆刻发展的新趋向以及展示方式的当代转型
- • 2015上海城市艺术博览会亮点汇聚即将起航
- • 展望“图像的命运”第四届国际新媒体论坛开幕
- • 钱海峰《绿皮火车》获第十一届连州摄影年展大奖
- • 首届全国青少年美术素养大赛决赛开幕
- • 2015年中央美术学院“国培计划”正式启动
- • 西湖艺术博览会迎来第18届 全山石等艺术家参展
- • 宝马集团助力艺术 中国艺术家黄建成实现跨界融合
- • “2015中国北京国际艺术珍品保税展”在京启动
- • 佛缘四友艺术展在无锡冯其庸学术馆举办
- • 大型跨界艺术展览“色·界”秋艺大展上海开幕
- • 意大利当代画展南京开展 七位艺术家将驻宁创作
- • 打开安迪·沃霍尔的旅行包 来自1982的北京旧物
- • 凡尔赛宫展出安尼施·卡普尔艺术作品再遭破坏
- • 关山月:把素描看作一切造型的基础是错误的
- • “辉煌与悲惨:1850-1910年妓女群像”巴黎展出

- • 组图:天津书画家赴大别山地区进行采风写生
- • 张善军书法作品展11月28日在中国书法展览馆开展
- • “劳作”马树青个展将于11月28日在798艺术区开展
- • 天地成经纬 水墨筑“大家”—我所了解的庞黎明
- • 溪山流韵-天津山水画南京邀请展12月13日开展
- • 范敏版画作品展12月5日在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
- • 飒韵叠翠-陆福林个展将于11月28日亮相乾庄书画院
- • “丹青映和”肖映梅中国画展在扬州八怪纪念馆举行
- • 张志连丙申年台历欣赏:月月嗅花香 日日闻啼鸟
- • 第九届和平·枫叶杯全国连环画创作大赛评选揭晓
- • 天津南阳友谊长青—天津百中国画院赴南阳采风侧记
- • 组图:悠悠的心灵牧歌——观高建章油画有感
- • 盛世芳华—民进成立70周年书画摄影展开幕
- • 刘玉社小幅水墨新疆山水画作品展在津开幕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